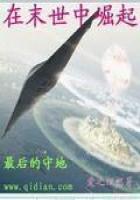秋兰一点头,“对。是我家小小姐,大名叫吴素兰,小名叫妞子。刚才睡觉来着,这会儿大概是睡醒了。这孩子胆儿特别小,有个风声草动地就哭。”想了下,秋兰又补了一句,“让她奶和她爸吓的,他俩动不动就吓唬孩子。”眨了眨眼,秋兰觉得意犹未尽,“她爸有时候还打她——掐屁股,掐大腿里子。”
“你去把孩子抱过来。”白胜仙交待秋兰。
秋兰应了一声,去东厢房里把妞子抱了出来,然后和白胜仙一前一后地进了西厢房。
“妞子,这是你三姨姥。三姨姥来救咱们了。”往西厢房走的几步道上,秋兰指着白胜仙,颠着妞子说。
妞子偎在秋兰的怀里,抽抽嗒嗒地眨着泪眼,畏惧地看了看这位陌生的姨姥姥,又扭着小身子去看她爸和她奶。她爸被人打翻在地,满地乱滚乱叫。她奶倒是没人打,哼哼呀呀躺在地上,勾偻着身子。
白胜仙迈步进了西厢房。一进房,她的气就不打一处来。房里又阴又暗又潮又冷。这哪是产妇该呆的地方。白胜仙扭头朝院里喊了一嗓子,“给我狠狠地打!”
她这一嗓子喊出去,吴包子的惨叫声更大了。
几步走到炕着,白胜仙探下身,去看床上之人。这是佩芝吗?她惊呆了。记忆里,佩芝白白胖胖,小脸有红是白的。哪像炕上的这个人,一张脸白里透青,两个腮帮子都塌下去了。
“佩芝?”白胜仙唤了江佩芝一声,声音不大,但是口型挺夸张。江佩芝虽然听不见,但是会看口型。用现在的话讲,她懂唇语。
两颗大大的眼泪,自炕上的病女人眼中滚了出来,“三姨。”
白胜仙愣了,不对啊,自家外甥女不会说话。
秋兰颠着妞子在一边解释,“我家小姐血崩之后醒过来,就能说话了,开始把我也吓了一跳。”
“佩芝,你真能说话了?”白胜仙还是不大相信。
“嗯,”林俐点了点头,“能说话了。”
白胜仙又像笑又像哭地一捂嘴,掉了两串眼泪。过了一会儿,她一吸鼻子放下手,抹了抹脸,感叹道,“老天开眼了。佩芝,你别怕。三姨接你走,那对畜牲再也欺负不着你了。”
“三姨……”林俐颤微微地叫了声三姨,像个要大人抱的小孩子似地伸出了双手。这动作,一半是她在表演在煽情,一半出于真情实感。只不过这真情实感不是她的,是残留在这副身体里的原主的残魂的。
白胜仙探身,小心翼翼地把林俐搂在怀里,“佩芝……”只叫了一声,白胜仙就哽咽了。
秋兰在一旁看着,不住地抽鼻子抹眼泪。妞子一看三个大人都哭,她也受了感染,瘪着小嘴,跟着吧嗒吧嗒地掉眼泪。
秋兰先是一抹自己的眼泪,然后又给妞子擦眼泪。一边擦,她一边颠着妞子,“妞子,不哭。以后再没人掐你了。乖,不哭。等会儿,姨给你买糖吃。”
一听吃糖,妞子不哭了。
“把孩子给我吧,”过了一会儿,白胜仙放开林俐,让秋兰把妞子给自己,“你去给你们小姐和小小姐找几件厚衣服厚裤子,再拿两床厚被褥。待会儿坐马车冷,你自己也多穿上点儿。”
“知道了。”秋兰转身刚要往外走,林俐叫住了她。林俐让她把江佩芝昨天生的男婴抱来。其实,林俐心里明白,那个婴儿要不已经死了,要不就是快死了。小说里,那孩子在江佩芝过世后的第二天,也就是今天,夭折了。
果然,在她说完这句话后,她看见秋兰的脸上露出了悲戚之色。
“小姐,小少爷今天早上没了。吴包子已经把小少爷拿出去埋了。”秋兰难过地说。
江佩芝血崩,许氏和吴包子又不肯带孩子,所以,那个男婴只能由她来带。今早天刚蒙蒙亮时,她起来给婴儿冲米糊,发现孩子已经绝命。可能是半夜时走的,她发现时,孩子小小的身体已经硬了。
她去跟吴包子和许氏说,许氏让吴包子找张席子把孩子裹上,拿到村外的荒地里,挖个坑埋了。她亲眼看着吴包子提着张破席子进了她的屋,把那孩子往席子里一放,卷吧卷吧拿根麻绳捆上,拎了出去。她追出去看,就见吴包子一手拎着席子卷,一手拎着铁锹出了门。
她怕小姐难过,所以没跟小姐说。如今小姐问到头上了,她没法再隐瞒。
林俐其实一点儿也不难过。她不难过,可是“江佩芝”必须难过。所以,听了秋兰的话后,林俐以手掩面,抽抽嗒嗒地掉起了眼泪。念大学时,她是学院话剧社的骨干成员,演了不少角色。同学一致夸她演技好,演什么像什么,说她没考中央戏剧学院真是白瞎了。
白胜仙接过妞子,一边拍哄妞子一边劝林俐,“佩芝,别哭。坐月子千万不能哭,该把眼睛哭坏了。秋兰,你赶紧去收拾吧。收拾完了,咱们马上走。”
不大工夫,秋兰拿着两套大人小孩的棉衣棉裤回来了,她自己已经换上了一套厚衣裤。白胜仙帮着秋兰,给林俐和妞子换上了厚衣厚裤。换好衣裤后,秋兰搀着林俐,白胜仙抱着妞子走出了西厢。
几个人来在院子里的时候,那两个当兵的还打呢。吴包子鼻青脸肿地在士兵的大头鞋和枪托间,翻滚哀号。
“行了!别打了!”白胜仙喝了一声。
两个大兵当即住了手。
“去!你们上屋里把被褥抱出来,放到车上。”白胜仙用空着的手一指东厢。
“是!”四个大兵,齐刷刷地又敬了个礼,快步进了东厢把秋兰准备出来的两床被褥抱了出来。
“走吧。”轻蔑地瞟了眼倒地不起的吴包子母子,白胜仙冷冷一哼,带着四个随从,三个弱女,威风凛凛地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