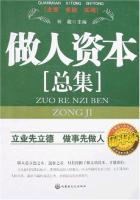当日下午,赵期昌来到朱高城工地。
他不在的这段时间里,工程就没怎么进行,卫里调拨来四千徭役在这段时间里也就完成了居住问题,并将原先烧好的青砖、红砖搬运分散码放,为后续工作提供便利。
卫里人做事最方便的一点就是有组织度,赵期昌不需要重新划分组织关系选拔头目什么的。他一抵达,近百余的卫里赋闲军官就列队迎接。
卫里军官编制编满,也只有三分之一人有实际差事可干,另外三分之二有世职有编制的,却没有实职可干。所以冗杂现象严重,好处也就是有充足的后备军官可用。
军官不是你一提拔那就是军官,一个合格的军官除了自身素质外,最重要的就是威信。赋闲的军官那也是有世职的军官,带领卫里军余做事情,天然有统御力。
赵期昌虽然与张祖娥之间有了历史性的进展,可这只是早晚罢了。让他心情不好的是这次出军造成的牲畜损失,尤其是拉车的牛,回到中所后大面积病倒,患有消化问题。处置不好,极有可能导致数十头牛的损失。
朱高城中,赵期昌翻开厚厚的花名册先将在场诸人认识了一遍,这才开口:“修筑朱高城,是省里心里惦记的事情。修好这座城,受益的非是我赵期昌一人。诸位,今后卫里就不止一个备倭城操守官的位置,还会多出一个朱高城守备官位置。三年一转任,就算卫里人能占据一半的机会,那每十年最少有两人能转升守备、游击。旁的也就不说了,且都用心想上一想。”
见有人不为所动,赵期昌便说:“或许一些世职百户、总旗人家不以为意,那本将就这么说,卫里上头人都通过备倭城、朱高城外调他地,空出的位置还不是由你们这些百户、总旗及子弟来填补?”
“其实,本将也无须说这些,本将以军法治众,也不怕尔等生事情。安心听令,事后自有酬谢。若有欺上瞒下,渎职者,本将也事前言明,卫里做事那就是军事,一切都以军法为准。将爷今日要杀你,你便看不到第二日的太阳!”
好话硬话说罢,赵期昌看一眼选拔出来的十余名头目,一帮人跟着他离去。
登上城墙,随行的庆童从竹筒里取出筑城图纸,铺开后,赵期昌指着城中道:“城中目前已完成排水暗渠铺彻,卫里此次出丁役做事,主要围绕两样。第一是修筑房屋,一切房屋规格想来尔等也都知道了,地基工程也已完成,需要做的就是打好墙基,先修第一层建筑。”
城中规划好后,不会有一处平房,都是二层建筑。赵期昌阐述自己的建设方案,先不建造二层这类耗时耗力的工作,先建造一楼。
只要临街房屋建好,再修二楼就简单不少,只要在一头垒土做斜坡,一切建筑材料就能运过去。再说一楼建筑以砖石为主,二楼以木质建筑为主。
赶在冬季前,能完成城中所有一楼建筑,并完善道路铺石工作,以及城墙包砖工作,一共三件事能完成,那就行了。
登州城,捕倭军开始游街夸功。
吴知府五十多岁,也骑着高达头大马跟在张茂、王文泽身侧,对着围观民众招手,甚是得意、享受这种排场。
赵家酒楼,赵凤翼端着酒杯摇头轻晃,听着音律。
那位落脚赵家酒楼的白衣女子这段时间以来,每日日落前,就会在楼中弹拨琵琶,房租照交,也不收钱,赵家酒楼生意渐好。
军队解散后,赵家子弟都涌向赵家酒楼。待酒客稀少后,赵凤翼见二楼广厅多是自家子弟,披甲提刀,这才起身走向白衣女子,拱手:“在下赵凤翼,算是此处少东家。姑娘日日抚曲,可是在等人?”
赵凤翼总觉得这女子是一个麻烦,他即将赶赴北京回吏部销假,赵期昌、赵鼎明都会赶过来送他。而这女子,来的太过突然,美丽的也是那么的离奇,赵凤翼担心这女子对家中安全造成隐患。
看一眼赵凤翼,这女子将琵琶收入布囊中,微微欠身,细语低声:“确是在等人,为报恩。”
赵凤翼笑道:“登州游人众多,本府人口过百万,姑娘等人,何不去德胜楼?”
这女子微笑着摇头:“妾身乃罪官之女,姓陈,湖州人氏。来此等一位将军。”
短短一句话,赵凤翼已经得到了很多信息,他努嘴:“陈姑娘与戚家娘子认识?”
点头,陈姓少女道:“王家姐姐与妾自幼相熟,情同姐妹。家父曾为曹州守备,年前下狱论死。妾与母亲充入教坊司,母亲为守名节追随先父而去。蒙王家伯父搭救,妾才得以脱身教坊司。王家伯父指点妾身,说能报先父仇者,便在此处。”
周围赵家子弟相互看着,赵凤翼心中暗道,果然是个麻烦。便问:“既然陈姑娘与戚家嫂子情同姐妹,何不找戚将军?”
陈姓女子摇头:“戚家兄长呀……他不敢为妾身报仇。”
赵凤翼皱眉:“那姑娘又是如何断定,我家叔父愿为姑娘报仇?”
这女子露笑,指指自己:“报妾身仇者,妾身唯有以身报恩。而王家姐姐那里,断不会允许戚家兄长出力。而戚家兄长,爱惜羽毛,自不会出力。”
想到那位的醋坛子本性,陈禾也是无奈,共侍一夫也不算什么大事情。可偏偏,那位世交姐姐,根本不愿意与人分享戚继光。
不满轻哼一声,赵凤翼双手负在背后,道:“我家叔父非是为美色所能动者,恐怕陈姑娘一番心意,要落空了。”
“不,妾身这里有小赵将军想要的消息,光这个消息,赵将军便会出力,为妾身报仇。”
“为何?”
压低声音,陈禾道:“妾身之仇,与赵将军相仿,皆是不共戴天之仇。”
赵期昌有什么仇?赵凤翼一想就知道,深深看一眼这陈姓女子,警告道:“望姑娘莫要作茧自缚,此言若真自是一番好事,若是虚言,我赵氏一族绝不姑息。”
陈禾微笑着欠身施礼,抱着包好的琵琶,领着小侍女回自己的客房。
一帮赵家子弟大眼看小眼,赵凤祥瞅着那背影身段儿心里痒痒,道:“兄长,这女子看上了叔父大人?”
赵凤翼皱眉:“希望不是,且不管他。说说昨夜情况,到底怎么个事?”
昨夜家中都备好家宴,偏偏赵期昌被新任知府给气跑了,这让赵凤翼很生气。他进士身份再有水份,也是进士。一个小小的拔贡监生当到知府也就到头了,竟然还如此放肆。
真要收拾吴知府,赵凤翼有信心熬个十年,就能折腾姓吴的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赵凤翼不是简单的进士,他家中有两名地方重将,他混军功是非常轻松的。就算职位不适合,也可以辞职跟着赵鼎明或赵期昌以幕僚身份参赞军机,混到军功屡历中添上重重一笔,那升官速度不要太快。
做知县、拔御史,再去兵部做员外郎,进而当道御史或六科官,就是他对自己的规划,以后在兵部、法司系统混,已经是一种定局。
反正朝廷那么多的位置,作为新兴将门子弟,赵凤翼除了吏部不能去外,其他地方都无问题,其中又以法司中的都察院、兵部最为合适。
而他赵氏一族猝然兴盛,他本人又无婚约在身,娶一个高门女子做妻,拉丈人的人脉也是今后水到渠成的事情。说真的,细细统计自己所有的资源后,赵凤翼心中心气大涨,自然看不上一个小小的拔贡监生。
知府?一个进士官员混到当知府,说明前半辈子白混了!
另一端,王文泽直接拒绝吴知府的私宴邀请,而张茂带着儿子赴宴。
宴中,吴知府端着酒杯赔罪道:“本官赴任以前,就听臬司副使东阳公、大名知府张公、登莱道朱公提点,说是小赵将军非凡人,万不可以寻常军将视之。”
张茂出于礼仪端着酒杯,微微颔首聆听着。
吴知府摇着头一脸苦色:“本官也是卫所出身,自然理解卫所子弟之苦。登州卫能有此气象,殊为难得。本官也无心思与小赵将军生别扭,可省里见不得本官与小赵将军和睦。还请张操守转述一二,务必告知小赵将军,本官绝无与登州卫生龌龊的心思,昨夜之事,只是做给省里看的。”
又是轻叹一声,一副有嘴难言的模样,吴知府端起酒杯仰头饮下。
张茂问:“省里?谁看我捕倭军不顺眼?”
吴知府摇着头,道:“卫所官本就与省里没什么关联,可如今的捕倭军还是寻常兵马?前任巡抚因妖僧惠金、金平而跌落,彭公从北京来巡抚山东,自然要竖立一番威名。而此时山东,各军疲敝,中军标营也被王参将带去广东备倭。眼前呀,唯一能打的就是登州卫捕倭军。彭公就任巡抚已快二月,而小赵将军、大赵将军迟迟不去拜谒,未免说不过去了。”
张茂恍然,端起酒杯一饮而尽,什么巡抚彭黯要建立军功缺打手,这话张茂是不信的。彭黯真要搞事情,何必一来就将王道成所部的标营尽数打发到广东去?
打发原有标营后,彭黯也没有组建自己的嫡系标营,更没有什么军事方面的动作,连各军整饬工作都没搞,说明人家根本不关心这类事情。
人家不重视军事,赵期昌等人自然也没道理贴上去看冷脸。再说没有必要赵期昌去历城拜见巡抚彭黯,在程序上就是一种错误。
现在倒好,借吴知府的口来传话,责备捕倭军不会做人,这到底怪谁?
登州卫这边根本没人去琢磨新巡抚彭黯的心思,彭黯将原有标营一脚提到广东,哪有标营空缺的说法?他只是将标营编制空出来,等着捕倭军自己去投靠,然后全员改建为标营中军。
各军看出来彭黯心思的机灵人也就没凑上去讨没趣,没看出来的也就过自己的小日子。反倒是捕倭军,一直没表示。
弄得彭黯心急,这才借吴知府之口来提点一下这帮只会干仗,不懂做人的粗汉。
实际上贾应春、朱应奎、钱知府都看出彭黯的心思,钱知府是懒得搅合。贾应春、朱应奎都不愿意捕倭军被彭黯连骨头啃下去,自然不会提点赵期昌。他们还都希望捕倭军待在登州卫静悄悄藏着,等他们需要时拉走,一起干大买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