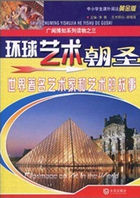把父亲从医院接出来之后,他经常在傍晚时,推着父亲的轮椅去附近的小公园看一看湖泊,不时停下来替父亲擦擦嘴边的涎,温言细语:“冷不冷?要不要喝水?”天气渐渐冷起来,湖上的黑鸭子一只一只飞走,父亲指着鸭子激动地啊啊叫,他耐心地和着:“嗯,鸭子鸭子,鸭子飞了。”
来探病的朋友吃了一惊:“你像一夜之间长大了。”
他也没想过会这样。他在家里赖到二十八九岁,日子过得生机勃勃:也恋爱也上班也交友,夏夜是小龙虾,世界杯是啤酒。动不动和父母吵架——不吵不行呀。父亲节俭,保鲜袋用过再用,一揭开,西瓜上全是鱼腥气;又天真,看到电视上“只要888元”的广告,就打算打电话,被他一顿臭骂,讪讪地又咳嗽又揉鼻子;这么老大,父亲仍然会没事翻他的抽屉杂物,他没好气地吼过去:“翻什么翻?非翻出安全套才甘心呀?”他恶作剧地想:不如放几张gay界的海报,吓吓他们?
是正吃着饭,突然间,父亲的筷子直抖,上面的菜哗哗撒了半桌子。他抬头不耐烦,看见父亲口角歪斜,脸有死色,缓缓倒下去。
天崩地裂。日子一下子变成:ICU、缴费单、陪床……还要挣扎着去上班。
由不得他想什么,要给父亲擦身要洗大小便。开始是买成人失禁品,眼看要生褥疮,于是家里的旧床单全成了尿布。每天带回家洗,洗衣机轰轰不休,他倒头就着;洗衣机一停,他霍地站起来晾尿布,挂出去好几十米,迎风招展。洁癖不治而愈,曾经文艺青年的小矫情,不知几时会卷土重来,但至少现在,他是一个在任何环境下都能狼吞虎咽、见任何床就能呼呼睡着的人。
父亲逐渐醒了,却没法理解自己为什么被困在一张陌生的床上,认定这是一场阴谋,忍不住要对周围的假想敌们拳打脚踢。他笑嘻嘻地打不还手、好言好语。人一堕地,就是不会言语,全靠哭泣和身体语言;人之将亡,也是一样的路程。他认了。这是一笔古老的、二十多年的债务,他得还。
突然没有拖延症了。以前到公司,先开QQ、淘宝、微博……再开Word,现在他对领导千恩万谢:这年头,都是资本家,能容下一个家里有病号的年轻人频频请假,容易吗?就在病房的走廊上,他全心工作,不时看一眼吊瓶。难得入睡的父亲像枚戒牌,强迫他静心。曾经天天抱怨“没有整块时间”,现在时间零散到以分钟计,他倒觉得绰绰有余。
也不再是暴躁的愣头青了。医护人员有时说话很冲:“你懂你上呀。”“医学不是万能的。”他恨得握紧拳头,一意识到,惊出一身汗,赶紧一根手指一根手指轻轻地放松:热血青年的不管不顾,是要由长辈来买单的。他能为了一时之勇带父亲转投另一家ICU?更何况,他明白医生说得并没错。他的愤怒,不针对任何人,只缘于自己的无能为力,只缘于那种叫天不应叫地不语的烦躁。
父亲一场病,拖了一年多,他始终身兼多职,还偷空狠狠见过几个天使投资人,谈他多年的创业梦。父亲状态平稳后,他去递辞职信——再不开始,梦便永远是梦。他不想“子欲养而亲不在”,也不想“徒有梦而身不由己”。前上司拍拍他的肩膀:“我看好你,孝顺的人,无事不成。”
“孝顺”这个词,又熟悉又古怪,第一次放在他身上,他很不好意思,于是认认真真想:什么是孝顺。
原来孝顺不仅仅是儿女对父母的爱、依赖与安全感,是把爱化为具体,像把银行里的定期存折兑成现金;是不论多疲倦还是站直,让老去的父母有个依靠;是不计前因后果的付出,不能回避不能逃避的责任。不能大喊一声“老子不干了”就卸挑子,你做的每个决定,都是父母晚年的一滴水一粒米,也是你的毕生心安。
这还是一种人力的无可奈何:无论做了多少,到最后,一定是一场空。父母只会越来越老,步入死亡,所有的钱、时间、心力,都是扔到黑洞里去。但这是写在血里的承诺,是人类世代相传的根基。
而他说:也许,我得到的更多。
他学会忍耐:不对身边人指指点点,缘分终将有尽,何必给出伤害;学会“色易”:什么都做不了,给个永远在笑的好脸色总是可以的;学会感恩:谁也不欠你,谁看着你不容易给你行个方便都值得感谢;学会当机立断、学会临事不慌……他就这样,藉由孝道学会了爱与生存。总之,是值得的。
不必计算得失,连父母都不爱的人,岂能爱全世界?而如果连对父母的爱也只能停在嘴边、埋在心底,还有什么爱与梦想,会真正化为行动?
孝是教的根基,爱之修为,从对父母之爱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