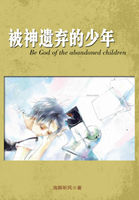铭——深刻于石头,有永远的意思。上帝似乎总想置我与我的愿望背道而驰,让我的庄铭时代那么短暂,而且知晓的人寥寥无几。但是,当铭记一页页篇章积成一本厚书的时候,关于庄铭的记忆却比任何一个时代都血性浓烈,趋近并超过了我的愿望。这要归功于南苑那次白刃战,白刃战彻底将我以前身上纠缠不清的两种东西分裂开来,将我变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人。一个是残留着白刃战中抡棍子时的癫狂、勇敢而好冲动的人;一个是保持着以前惯性的优柔懦弱的人。这两个人有时会面对面地搏斗,前者总是战胜后者,甚至能听到前者灵魂发出的报仇雪恨的尖叫。这尖叫让我激动,让我发狂,让我头脑发昏,做出了幼稚、极端的事来,包括杀汉奸解玉桂,包括一个人徒步找抗日队伍。
先说杀汉奸这件事,明显带有癫狂的特征。
齐老爷在失去两个儿子的当天夜里,带着庄上的男丁出去拣了大量的武器,在庄上成立了地方抗日武装。齐老爷足智多谋,让三儿子齐占山带着青壮男丁在高粱地里练兵备战,让五儿子齐占河在距齐家庄三里多路的草堂镇开了药材铺子,收集情报,他自己在家坐镇,穿针引线,制定战略。
草堂镇是一个以进行药材交易出名的镇子,空气整日里弥漫着药材辛辣的气味和骡马粪便的臭气。齐老爷给我派的活是躲在店铺后院的屋里,接待由五少爷验明正身后领进来的线人,问清楚记录好,然后根据情报的估计价值给来人赏钱。有几次鬼子在回兵营的半路上遭到伏击,均是这里提供的情报。可以说,我的特工生涯从这个时候就开始了。齐老爷说我细心、冷静,对分析情报有天赋,但我知道齐老爷让我干这个的主要原因是认为我胆小,我不敢向敌人冲去,他的两个儿子死了,而我好好地活着就说明了这一点。齐老爷不知道我已分裂成了两个人,他看不到那个癫狂的人正潜伏在懦弱的人之中,瞪着眼睛等机会要为懦弱的人雪耻。
这一天来了一个陌生人,来人说,“如果我给你带来的是二十九军惨败的内幕和你家四少爷齐占田的消息,你给多少赏钱?”我毫不犹豫地从钱箱子里拿出十块大洋放在来人面前。来人说,“太少,再加五块。”我又毫不犹豫地拿出五块。来人要讲的消息实在太诱人了,如果他要一百大洋,我可能手都不会软,我也相信齐老爷和我想的一样。
来人一笑,“你不怕我拿假消息骗钱?”我说,“没人敢,谁敢在打日本鬼子的事上糊弄我们,我们会杀他全家。”来人认真地端详了我一会儿,我坚决的表情好像让他很满意,他有些疼爱地用手捋了我头顶一下,“小孩子家家的,够毒的。我先说哪一个?”我说,“四少爷的。”
“齐占田在二十八日撤退的路上,遭到了日军的埋伏,战死了。”
“向哪儿撤了?都撤退了,怎么还会中埋伏?”
“向西。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个事情,有汉奸出卖。本来二十九军主力四个师的部署宛若一把巨大的三叉戟,西侧,是张家口的刘汝明第一四三师;东侧,是天津的张自忠第三十八师;中央,包括北平和北平以南直到保定,是冯治安的第三十七师,这是三叉戟的三个刃,前面还有一个独立第三十九旅作为屏障。三叉戟的柄,则是河间、大名一带担任预备队的赵登禹第一三二师。军长宋哲元颇通兵法,这个布局中央相对较弱,两翼较强,后方也有强力的预备队。如果日军先取中央冯治安部,则可能遭到两翼和后方刘、张、赵三路夹击,若是先取两翼,其威胁对宋部核心的北平地区又鞭长莫及。外围还有其他北方军阀万福麟、冯占海等部,一旦开战也可期待获得他们的策应。”
来人怕眼前这个“小孩子家家的”听不懂,一边讲一边蘸着茶碗里的水在桌上画着宋军长的三叉戟。
三叉戟是一种古代冷兵器,我这个“小孩子家家的”是知道的。四少爷从军队回来,喜欢把兄弟和家丁们叫在一起讲军事课。四少爷说,长城之战的胜利说明了我们擅长的冷兵器是敌人的软肋,我们的作战方略是要想办法避开敌人占有优势的火炮,诱敌深入或钻进敌人的肚子里用冷兵器打击他们。四少爷喜欢研究战略和冷兵器,他让家里的铁匠按古战书上画的兵器打了样品,有锏、钺,还有三叉戟,我和两个哥哥每样都拿出来比划过。但是,我听不大明白宋军长的这个三叉戟,也不想弄明白,甚至有些轻蔑,三叉戟再好也败了,现在谈这个有什么意思呢?
来人还在絮叨,“这样好的一个三叉戟被解玉桂出卖给日本人了,结果呢?日军的增援部队源源不断,川岸二十师团,关东军的两个旅团对三叉戟形成了战略的切割包围,而日军的眼光瞄在了三叉戟戟头与戟杆相连接的地方——南苑。”
南苑?我的心被刀子扎了,急切地问,“解玉桂是个什么人?他怎么知道三叉戟?”
“解玉桂书画皆佳,人称才子,是有名的亲日派,为何能接触二十九军最上层的机密呢?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很复杂。总之,解玉桂是一个在日军与宋军长之间穿梭说和的人,宋军长对解玉桂信任不疑,认为解玉桂亲日的目的是不想让百姓有伤亡,和是为了二十九军不要伤亡,所以,在机密问题上,宋军长相信解玉桂无论如何不会出卖二十九军。而解玉桂出卖了三叉戟还不够,南苑遭到袭击,宋哲元料守军难以支撑,当日上午下令赵登禹率部撤离。但是,由于南苑通讯系统都被日军摧毁,命令通过最近的三十八师部队派员冒死送达南苑,已经是下午一点。而此时,这一命令的内容,包括赵部的撤退路线,早已被解玉桂以最快的速度转给了日军,日军立即下令萱岛联队转而前往大红门方向,伏击撤退中的赵登禹部。下午四时,南苑撤退下来的守军落入日军伏击圈,遭到机枪和迫击炮的猛烈攻击,日军飞机也于此时投入轰炸。由于缺乏遮蔽,战斗很快演变成了单方面的屠杀,赵登禹师长、佟麟阁副军长都牺牲了。四少爷就死在这里。”
来人又一口气讲了这么多。
我仰起头,打量着来人,嘴动了动,却什么也没问。一般来讲,话到了这里,应该对这个来历不明的人提出一些疑问,比如,你怎么会知道这些呢?又为什么对我说这些呢?但是我没有,也许十七岁的少年头脑还没有长出会盘旋的细胞,也许在感情上我更倾向于二十九军战败是被人出卖而不是无力抵抗的缘故,更重要的是这个陌生人给我带来了报仇的具体目标,这是一个比杀一百个鬼子都解恨的目标,是最能报仇的目标。虽然齐老爷和三少爷一直教导我,我现在所做的事情就是报仇,但我只是承认这跟报仇只是有那么一点曲里拐弯的关系,让我太不满意了。
我将桌上的大洋向来人推了推,“我想知道解玉桂长啥样,家住哪儿。”
来人把大洋推回来,看着我,微微笑了。他的笑,让我颇费猜测,浅浅的、线条清晰的嘴唇抿着,似笑非笑的。还有他的眼睛,眯成细长,在笑意里闪出稍纵即逝的凛冽的光芒。
“解玉桂的家住哪儿你不必知道。长啥样?过两天,解玉桂要上齐府去替日本人进行亲善游说,你见了就知道了,很有儒雅风度的一个人,能把死人说活的一个人。”
来人把口袋搭在肩上说,“有了准信给你送来,到时候我再拿走大洋。”说完,对我挥挥手,走了。
我们家乡对送密信的人不问出处,更不问姓名。我跟少爷进北平读过书,是见过世面的,这个人尽管穿着一身农民衣服,肩上还搭着一个口袋,一副卖药材的农民打扮,但是还是没有掩盖住他的大家出身的风范,这种风范是一种气味,在大宅院里生活却是用人孩子的我,对这种气味特别敏感。这个人绝不是来挣大洋的。他的讲述又是那么的清晰、轻车熟路,他是宋军长身边还是解玉桂身边的?他为什么要出卖解玉桂?他怎么知道这里?疑问一个个冒出来,但很快被我不做任何答案地压下去了,那个时候我毕竟涉世未深,觉得关于那个人的一切疑问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人带来的消息。
当我出去要将这个人带来的消息告诉五少爷的时候,我突然觉得全身发生了一种几乎不可理喻的震动。我想最好把这种变化比作血液中起了一阵风暴吧,它立刻袭击了我的全身,我的动脉跳得非常激烈,我不仅感觉到跳动,甚至还听到了它跳动的声音,那个癫狂的我就要从懦弱的我中跳出来了。
我只告诉五少爷那人是来报丧的,四哥早死了,跟八哥九哥是一天,在大红门那边的路上,撤退的时候遭到了鬼子的伏击。五少爷含着眼泪说,这个事不要回去给我爹他们说了,权当四哥还活着在杀鬼子。解玉桂的事,我瞒下来了,我想一个人亲手杀死解玉桂。这天晚上,齐家大院的人都安睡了,癫狂的那个我跳出了懦弱的我,提着一盏马灯溜到农具房,挑了一把铁镐和一把铁锨,出了后门。
当时癫狂的我非常的激动和感谢老天爷,老天爷给了我这样一个一下能杀到根上的报仇雪恨的机会,我甚至认为,老天让这个人找到药材铺,找到我面前,就是让我去亲手杀掉这个汉奸的。
夜空是晴朗的,月亮像正在融化的冰片,白白的、薄薄的,那么脆弱地把似水非水的融化物淅淅沥沥洒下来,将路变成了一条白白的小河。高粱长得如原始森林一样茂密,路在其间忽隐忽现地绵延着。解玉桂要到齐老爷家,这是必经的一条路,伏击点设在哪里呢?那时候我对这种事情一点经验都没有,选在了距墓地最近的地方,我想让同学们和二十九军官兵听到我为他们复仇的枪声。报仇的激情此刻让我变成了一个诗人,付出了选错地点的代价。
我把马灯放在路边,开始用镐挖路。自从落入日本人的铁掌之后,老百姓没有人赶夜路了,这里高粱深深,日本鬼子也不敢晚上路过,高粱地里随便飞出几颗子弹,他们就是有飞机大炮又能怎样?
这路虽是土路,却硬得跟石头一样,被人踩了有几百年几千年也说不准,不一会儿我就大汗淋漓了。我抹了一把汗,把小褂和长裤脱了,想了想,干脆也把裤衩脱了,赤条条地干起来舒坦。马灯照着我,给我高粱秆一样纤弱的裸体涂上了一片铜黄,我从来没有注意看过自己的躯体,却在某个我举起镐头的瞬间深剜了一眼自己的躯体,不知是怜悯还是怎么了,一阵从来就没有过的令我心悸的感伤,电流一样窜过我全身,使我扔下镐头,四脚朝天躺在路面上,痛哭起来。高粱地里有虫子鸣叫,还有麻雀的梦呓。月亮很圆,但中心透了蓝,好像快要从中心被天空熔化了。八哥九哥的面孔出现在月亮里,若有若无。如果没有战争,现在他们在干什么?很可能在北平我们住的屋子里围着诗转呢。八哥自从喜欢上了一个叫李小亚的女同学后开始学写诗,一写就写到深夜,但还是没有九哥随意啊呀两句的好,八哥努力到最后,送给李小亚的诗还是九哥写的。八哥说九哥有诗人天赋,以后会成为诗人的,九哥说:我的目标是戴望舒那样的大诗人。我认为九哥不是吹牛,他会成为戴望舒那样的大诗人的。我记得九哥帮八哥写的诗里有这么几句:“李小亚,你不是丁香花,却比丁香花芬芳!李小亚,你没有走在雨巷,我却看见你撑着油纸伞,从雨巷里向我走来。”八哥不好意思把诗当面交给李小亚,让我当通讯员。李小亚很漂亮,长着一对酒窝,一笑很甜蜜,她嘴边酒窝中有一颗芝麻粒大的黑痣,笑的时候,黑痣跳动起来,更加迷人。每次我给她送完诗要走的时候,她都要亲昵地捏一下我的鼻尖说,“瞧,你长了这么高的一个鼻子,真英俊,等姐姐身边有漂亮女孩的时候,给你捉一个。”李小亚以此表示对我跑腿辛苦的感谢。我感到九少爷的这首诗与李小亚南辕北辙,李小亚是一个看上去性格畅朗的女孩,没有雨巷里的那种惆怅的味道。如果没有战争,八哥和李小亚是不是成双成对了?李小亚说给我介绍个女孩子是玩笑话,但我还是盼望着再给李小亚送诗,并希望她身边站着一个有酒窝的女孩。可战争来了,我们都参加了二十九军的学兵团,李小亚后来怎么样就不知道了。想到这些,我明白了令我心悸的悲伤是爱情。我就要死了,还没尝过爱情的滋味。那个时候我认定我会死在这个自己挖的沟渠边,我知道这是一个再笨不过的办法,但是我又想不出来一个好办法,如果八哥九哥中有一个活着,我们会想出好办法来,两人加在一起的力量也会大些。
仇恨又一次燃烧起来,我抹干了眼泪,起身继续干起来。我挖完了一层硬土,扔下镐,用双手把挖下来的土块扒到一边,接着再用镐挖第二层。
我挖好沟后,跨步试了试,估计足以把车头栽下去,就又用土把沟填上了。当我扛着镐,提着马灯往回走的时候,又兴奋起来,好像已经把大汉奸埋在了刚才挖的沟渠里。
三天后,药材部的门缝里塞进了一张纸条:桂皮明天到货。五少爷以为是谁把送货的通知送错了门,我心里很明白,这是那个人给我送的情报。从此我就把解玉桂叫桂皮。
桂皮第二天真的来了,由齐老爷的一个远房表哥引见。是这个表哥没有跟桂皮说过日本鬼子一天杀了齐老爷两个儿子,还有一个下落不明;还是这桂皮想给日本人卖力想傻了,想让齐老爷跟日本人亲善?这不是做梦吗?
桂皮穿着大褂,戴一副小片茶色眼镜,谈笑间所展现出的儒雅风度超过了我的想象。齐老爷虽然一头雾水,还是很客气地接待了这位不速之客。
我接过丫环的茶盘端上去,我想仔细看清那张脸。
桂皮亲善地问,“上过学吗?”
我说,“没上过。”
桂皮说,“这么一个大眼睛的俊小伙,睁眼瞎,真是可惜了。不过,还来得及,日本人要多多地办学堂了,不收钱的,贫富不分,孩子都可以上学。”
齐老爷说,“日本人都快把孩子杀光了。”
桂皮说,“齐老爷,今天到府上冒昧造访,就是想沟通一下对目前局势的一些观点。我不瞒你说,我跟宋哲元是朋友,我是中国人,也不想让日本人占领这里。可是,二十九军的武器早已经落后了,什么年代了,还用大刀,这简直是对我们这发明火药的文明古国的羞辱。日军是什么?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坦克大炮,我劝他不要鸡蛋跟石头碰,要爱惜士兵的生命,不要让老百姓受战争之苦,不听,这下好,死了多少人?打胜了吗?如果是谈和还有个立足之地,这下好,全部沦陷。还搞了个学兵团,不劝学生回去好好念书,而是拿起大刀,这些傻孩子,死得真不值啊!还有,日本人打前给宋哲元是发过通知的,谁见过打仗还有给对方下通知的?日本人不想打,想把宋哲元吓退算了,可我这老兄,立即调兵遣将,要跟日本人决一死战,非要让大家跟上他送死。我跟日军周旋,是真心为二十九军谋一条出路。你看看,现在的局势,国民党政权对北方鞭长莫及,阎锡山封建落后,都不是二十九军和民众可以依靠的支柱,唯一出路就是和日军合作,可免生灵涂炭。而且,日本文明开化,如果合作起来共谋和平发展,我们这里将变成没有军阀、政治开明的地方,还可以为整个中国的开化建立楷模……”
这样的扰乱抗日民心的人该碎尸万段!我听不下去了,在齐老爷藏枪的地方找出一支长枪,枪口架在窗棱上。齐老爷与桂皮坐在院中的石桌前,正好背对着我,我瞄准了他的后脑勺,以我打乌鸦的经验,只要我开枪,就一定能打中,但是就在开枪的那一刻,我手发抖了,我深呼吸镇定自己,但手还是抖得厉害,更糟糕的是我眼前模糊了,我想到这样做是会给齐老爷惹麻烦的,手一软,放弃了。在以后的回忆里,我不知道是那个癫狂的我在开枪前的那一瞬间理智了,还是懦弱的那个我占了上风,也许两者都有。后来,李简的死让我非常后悔这一次的放弃,李简那只身闯入狼窝、直面开枪的英雄之举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在这一刻的懦弱龌龊。也许,我不是懦弱龌龊,但我就是这么给自己下定义的,用以惩罚自己,让自己的心灵在受这种折磨的同时,得到坚强又果断的成长。
李简?我后面会讲到的。
接下来的回忆能给我一种安慰,我还是勇敢的。我又找出来一把大刀,我把枪和大刀装在一个粗帆布口袋里,背起口袋出了门。
门外,停着桂皮的黑色小汽车,司机和两个保镖坐在树荫下歇凉。我不由站住看那俩保镖腰间的盒子枪。“看什么看?”一个保镖对我嚷。我说,“如果谁突然向你们开枪,你那枪能从盒子里取出来吗?”保镖说,“哟,小熊孩子吃咸萝卜操淡心,解先生一出来,我们自然会把枪握在手里。”
我走了。走远后回头看了看齐家大院,我想,我死了,齐老爷和少爷们不会亏待母亲和妹妹的。
茂密的高粱像墙一样夹住那条土路,没有风,阳光如水,白晃晃从两墙中间泻下来,打在我身上。我对自己说:这下你没有手软的理由了,下一次瞄准了一定要开枪。我的脚板把坚实的路面拍得吧唧吧唧响,坚定不移地走向伏击点。
找到伏击点,我钻进高粱地,把带来的大刀和枪从口袋里取出来,准备随时用,然后拿起藏在高粱地里的铁锨起那沟里的土,必须在桂皮车到之前把土起出来,沟才能拦住汽车。土还虚着,一会儿工夫就起完了。估计桂皮的车等一会儿才能过来,我开始把土一锨一锨往高粱地里运,我想让车发现沟的时候来不及刹,栽到沟里去,这样一来可以分散他们的注意力,二来车栽到了沟里,他们还击不方便,也许车门都无法打开,当他们在忙于把车往上弄的时候,我开枪了。我就是这么设想的。我还生出一种幻想,如果把他们都杀了,而我还活着,我就把他们埋到这沟里,让他们永世都被踩在骡马的两瓣蹄子、狗的梅花蹄子和人的长着五个指头的臭脚丫下。
土全部运到了高粱地里,我又对路面进行了一番伪装处理,然后躲进高粱地,端起枪试了试,感觉是很有把握的。这些天来,我跟三少爷学过用这步枪打高粱穗子,一打一个准,三少爷说这跟我自小用鸟枪打乌鸦有关。可是,在我觉得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时候,问题来了:高粱地好躲藏,但没有视野,只能看见正前方,如果看见车了再瞄准就很仓促了,没办法,只好在路边装着拔草,等看见车老远过来,再跑进去端起枪等着。可还有问题,前面不远有一个弯道,车转过弯才能看见,而这段距离并不长,也就是说,车在拐弯处一露头,我必须赶紧跳进高粱地里端起枪准备射击,来不及怎么瞄准。这个伏击点选错了。我懊恼得直拍脑瓜,总想让同学们听到我的枪声,告诉同学们我多么勇敢,我为什么没有想到,同学们并不想看到我血沃高粱地,而出卖他们的汉奸却毫发无损?但绝不能因为这点问题而放弃,能瞄个什么程度算个什么程度,只要车停下来,他们在明处,我在暗处,我还是能多打几枪的,如果他们没有立即还击,我就扑过去使大刀。我带大刀的目的就是在用枪不顺手的时候用的,准备得还是比较充足的。
决战的时刻终于来了。我最先看到的是那只弯道外侧的车灯,车灯反射着夕阳橘黄色的光辉,带着几分诡秘从高粱丛里射出来,接着是车头,如一个独眼的黑色巨蛙,警觉地屏住呼吸,缓缓地探出身子……
我急忙跳进了高粱地,端起枪,迅速估计了一下车窗的高低,将枪头抬高了一点。
然而,车没有出现在我眼前。高粱地密不透风,汗水将我的头发和衣裳都浸透了,干枯的高粱花粉落在我湿润的睫毛上形成了霜花。
西斜落日的紫红色光辉铺满了弯道那儿的天空,一缕粗一缕细的蓝色光线从高粱秆中透出来,将路面铺成蓝色。成群的麻雀在高粱穗子上面飞舞,如迷恋花园的黑色蝴蝶。没有那车的一丝踪影,难道那独眼的黑色巨蛙是幻影?
悲惨的是我一直等到天黑,那车也没开过来。可怜我在回去的路上,还密切关注着前方,只要那辆车能迎面过来,我豁出去了,直接从口袋里拿出枪射击,我实在接受不了这只有伏没有击的现实。
无论我接受不接受,事情就这样结束了。我想不明白那车哪儿去了?除了这条路,桂皮没有其他路可走啊!
我眼前漂浮着一层云翳,无精打采地坐在药材铺的后院,我对任何情报都没有了兴趣,偷袭几个鬼子跟杀死桂皮比起来,实在没有多大意思。我盼望着那个人再来。我相信只要桂皮还活着,我们这边有机会出手,他还是会来的。
果然,没过几天,那个人又来了,还是上一次的打扮。那人严肃地问我,“齐老爷为什么不动手?”
我低垂着眼皮说,“我没跟齐老爷说,我想一个人干。”
那人生气地说,“你杀了吗?连一枪都没放?有你这样设埋伏的吗?见到车,像受惊的兔子跳进了高粱地,人家能不怀疑有埋伏了吗?桂皮脑袋过人!”
“那车跑哪儿去了?”
“人家哪里都没去,倒进了高粱地,等你呢。看见你背个口袋垂头丧气地走过去了。”
“那咋不杀我?”
“当场杀个孩子就不是桂皮了。桂皮把你当笑话说给大家听呢:一个熊孩子还想杀我?这熊孩子有意思。”
这个狗汉奸,这样嘲笑我?我气得血直往脑门上冲。
那人用手捋了一下我的头顶,笑了笑说,“熊孩子,不要再高估自己了。桂皮明天早上到刘村看他老师,你一定要告诉齐老爷,再误了可能就没机会了。”
那人一走,我就像吃足了奶的牛犊,连蹦带跳地去了刘村,刘村距小镇不远,跟齐家庄方向相反。我本来是打算先看好地形,形成一个战斗方案,再跟齐老爷禀报。当看到去刘村的路笔直、两边也是高粱地,更重要的是路边的高粱地里有几棵白杨树时,我改变了主意,我还是回到了要执意一个人杀死桂皮的癫狂中。
故伎重演,当晚就在距白杨树较近的地方挖了沟,这次我决定让桂皮在看到他老师之前就毙命,所以,没有用土把沟填上。第二天,我一大早就爬上了白杨树,这下视野好宽阔啊!高粱地泛着浅红,像海洋一样翻滚着波浪奔向远方,桂皮的必经之路虽然深陷在这片海洋里,但我趴在树上对一切能一目了然,哪怕从遥远的路那头过来只小狗,都逃不过我的眼睛。
路上有零星的行人经过,走到沟前都骂骂咧咧。一辆马拉的轿车远远过来了,这轿车看样子是个阔气人家的,车大,三匹大马拉着。走到沟前,那车夫下车看了看,从车上拿下两块板,架到沟上,把车赶过去了。跟提前知道这里有沟似的,从容不迫,也没有骂骂咧咧。
一个推地轱辘车的过来,把车弄过去后进了高粱地,两手扒拉着高粱棵子,走到树下,掏出家伙,准备撒尿的时候,看见了靠在树上的大刀,哆哆嗦嗦地仰头往树上看。我将枪口对着那人说,“我是抗日游击队,在这儿等鬼子,你敢去报告,我会杀了你。”那个人说,“你干你的,跟我没关系。”这个人尿没撒就跑了。
快到吃午饭的时间了,桂皮的车还没有出现。一般走亲访友都是在饭前,不然,主家会不高兴,认为你看不起人家,嫌人家的饭不好。我忽然想到,桂皮会不会坐着那辆马拉的轿车过去了?我赶紧下了树,把枪和刀装进口袋,背着进了刘村。
刘村是一个比较富裕的村子,村子也很大,前后分了三条街。在一个挂着“厚德载物”大匾的高门楼前的一棵大皂角树下,我看到了那辆轿车,我见过的桂皮的两个保镖在树下玩方格棋,车夫端着一个木斗,给马喂料。
啊呀呀,桂皮不但换了车,连他可能会遇到一条沟都想到了,这个老狐狸眼睛就像长在我背后啊!我如果再蹲在高粱地里守株待兔,又恐怕连根兔子毛都见不着了,必须改变方案。
我观察了一下,这高门楼对面人家门前有棵大槐树,既可以隐身设埋伏,又能居高临下。正是吃饭的时候,村路上没有人。槐树近旁有个草垛,我躲在草垛后面,把枪取出来背在肩上,把口袋藏好,然后三两下蹿上了大槐树。
我用枪对着那高门楼的时候,高兴极了,这是一个极好的射击位置,不说打一枪,就是打十枪,他们还找不到北呢!再一个居高临下,这射击面宽,可以追着射击。天助我也,老天爷给我准备了一个草垛藏家伙,又给我准备了一棵大槐树藏身。
午饭过后,那“厚德载物”下的大门开了,桂皮拱着手一步三回头地走了出来,我屏住呼吸,集中目力,瞄准了桂皮。可是,一眨眼,那两个保镖又挡住了桂皮,接着,门里拥出了一群送行的人。我紧张起来,怎么打?弄不好会打死了无辜的人,放跑了桂皮。可是,不能再放掉杀死桂皮的机会了。
我开枪了,那边倒下去一个人,是送客的一个男人,送客的一群人立即拖着那个人,退回到了大门里,关起了门。
这下好了,我的枪口追着桂皮连续开枪,但没有一枪打中,那两个保镖护着桂皮,桂皮一点也没有慌张,从容不迫地上了轿车,走了。我想象中的桂皮方面的还击没有出现,高门楼里也寂静无声,这是一个只有我一个人打响的战斗,没有人理我,真是奇怪了。我急忙滑下树,背起口袋,追赶那轿车。我不能容忍桂皮这样一枪不还地离开,我对那个沟还寄予了希望,轿车总是走到那儿要停下来放木板的,我可以追上去使大刀,对于枪我不敢再抱希望。这个时候我仿佛追求的不是要把桂皮打死,而是强迫他还击,我不能让他再发出嘲笑我的声音,“这个熊孩子,真有意思!”
但到底,还是被他嘲笑了,我看到那轿车到白杨树那儿根本没停,如履平地过去了。我跑到跟前一看,那沟已经被人填得结结实实。
我钻进高粱地,将头磕在那棵白杨树上,我想大哭一场,我不明白,桂皮和高门楼里的人为什么不还击?桂皮那么从容,仿佛知道我的枪打不中他似的。这桂皮到底是人还是鬼?
我等待着第三次机会,我告诉自己,无论如何,再不能一个人单干了,一定要告知齐老爷。可那个人再没有来。
有一天,我收到了李村人来报的情报,十多个鬼子去了李村,正跟村长商量要在李村办学校的事。估计路上打伏击还来得及,我急忙回来报齐老爷,却看见桂皮那辆黑色巨蛙停在齐家门前。
我从后门溜了进去,看到确实是桂皮在跟齐老爷说话。只见桂皮摇着头叹息地说,“我和他父亲是老交情啊,正因为这样,我才把他放到身边当我孩子一样培养。这样一个书香门第的文人,竟去刺杀一木清直那样的武将,你说现在的孩子是不是疯了?我是在保护他们啊,他们反倒要杀我!如果他们能杀了我,我早死八百回了。”
我听后一惊,这是说谁呢?但我来不及听下去,两次刺杀的失败,使我认识到那个人说得对,自己一个人是无法杀死桂皮的。我赶紧去高粱地找三少爷。三少爷立即带人埋伏到桂皮回去的必经之路上了。但最后也没有等到桂皮的车过来。桂皮的车在我跑到高粱地找三少爷的时候就过去了,他的眼睛不是长在我背后,而是长在我脑袋里。
我预感不好,我担心桂皮说的那个人是给我送情报的那个人,我问齐老爷,齐老爷说就是。那个人叫吕直,桂皮发现后,让吕直父亲把吕直领回去了。可是吕直想趁日本人知道之前进日军兵营把一木清直杀了。日军兵营的鬼子认识吕直,吕直谎称送桂皮的秘密文件,鬼子就让吕直进了一木清直的办公室,手枪就藏在公文包里,他一见一木清直就拿出了枪,结果一木清直未损毫毛,吕直当场被击毙。
桂皮来不但送来了这样一个消息,还下了一个让我在冀中平原消失的通知,通知充满一个长辈对年轻人的关怀:现在这些熊孩子不知好歹,都中了魔怔,别让这魔怔要了孩子的命,什么时候清醒了再回来。
皓月当空,树影婆娑,我躺在床上,流着泪思念吕直。显然,吕直是因为给我送情报被桂皮发现了,我的癫狂,也可以说,是我的自私让吕直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的一时冲动怎么就带来了这么残酷的后果呢?
齐老爷尽管对桂皮恨之入骨,还是听了桂皮的劝告,赶我去山西浑源县用柿子做老陈醋的朋友那里当伙计。齐老爷说,浑源县在五岳之一的恒山中,安宁,把你那魔怔劲过了再说打鬼子的事,你这孩子中魔了。
我也想离开,因为我预感到了,吕直的死会让我更加癫狂,我不敢肯定,如果有了什么机会,我能不能控制住自己的癫狂?我的魔怔会不会让更多的人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