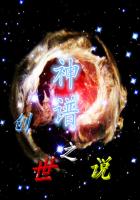当时留美学生在《中国学生》月报(3月)热烈讨论“中日交涉”问题,大家主张对日作战,并主张“对日本立刻开战”。胡适对此十分焦虑,3月19日他写了一封公开信,对全体同学进行劝告,他说:“从上期《中国留美学生月报》上表现的(抗日)情绪来看,我恐怕我们都已完全昏了头,简直是发疯了。有一个同学会竟然主张‘对日作战!必要的话就战至亡国灭种!’纵使是W.K.钟君(译音)这样有成熟思想的基督徒,也火辣辣地说:‘纵使对日作战不幸战败而至于亡国——纵使这是命中注定不可避免的后果,我们也只有对日作战,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可循……让我们对日抗战,作比利时第二!’纵使是本刊的总编……也认为‘中国人如今只有对日作战(毫不迟疑的对日作战),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从这段文字,可看出当时留学生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爱国情绪是多么高涨。然而胡适对此却无动于衷,他在信中劝告大家说:“这些在我看来简直是不折不扣的疯癫。我们都情感冲动,神经紧张——不是的,简直是发了‘爱国癫’!弟兄们,在这种紧要的关头,冲动是毫无用处的。……在我个人看来,我辈留学生如今与祖国远隔重洋;值此时机,我们的当务之急,实在应该是保持冷静。让我们各就本份,尽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的责任便是读书学习。我们不要让报章上所传的纠纷,耽误了我们神圣的任务。我们要严肃、冷静、不惊、不慌的继续我们的学业。充实自己,为祖国力争上游。……”这些便是胡适的态度。至于不能战的理由,他说:“让我们正视现实:我们至多只有12万部队可以称为‘训练有素’,但是装备则甚为窳劣。我们压根儿没有海军。我们最大的兵船只是一艘排水不过4300吨的第三级的巡洋舰,再看我们有多少军火罢?!我们拿什么来作战呢?所以出诸至诚和报国之心,我要说对日用兵论是胡说和愚昧。我们在战争中将毫无所获,剩下的只是一连串的毁灭、毁灭和再毁灭。……”在信的末尾他说:“最后的真正解决之道应另有法门——它较吾人所想像者当更为深奥。但其解决之道究在何处,我个人亦无从深索;我只是知道其不在该处罢了。让我们再为它深思熟虑,从长计议罢!”胡适在国难当头的时候,竟发出如此奇谈怪论。不惜与群众为敌;而且自己也提不出什么有效的“法门”来,说服不了人,自然要受到留学生们的批评。此文发表后,引起群众公愤。5月《中国留美学生月报》主笔邝煦堃指责他是“木石心肠,不爱国”;《战报》主笔谌湛溪写信批评他说:“大著结论盘马弯弓故不发,将军之巧,不过中日合并耳。足下果敢倡此论乎?东亚大帝国之侯封可羡,目前爱国者之暴行又可畏,作个半推半就,毕竟也甚大不妥。”诸如此类之批评,不甚枚举。胡适自己也说:“我为这封信受了各方面的严厉攻击,且屡被斥为卖国贼。”可见胡适所持之“不争主义”,对他是有害无益,但他仍不觉悟,还说什么,我不禁想起老子的名言:“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等等。之后,他又由“不争主义”走向“新的和平主义”,接受了英国经济学家,诺曼·安吉尔(Norman Angell)的新和平主义理论。(安氏于1933年获诺贝尔和平奖)安氏认为:“一个人如强迫别人接受他一己的意志,就会招致反抗。这样的强迫与反抗的对立,就会使双方力量抵消而至于亳无结果或浪费。纵使一方胜利了,仍然要创造出两种奴役——失败者为胜利者所奴役;胜利者为维持他的主宰权,又要随时准备对付这被奴役的对方,这样便形成了一种在经济上浪费亦如在道德上破产一样的关系。……如果双方息争合作,共同为人类的生命和人民的生计向大自然奋斗,则双方皆得其解放,双方都会发现这种和衷合作实在是最经济的办法。……”统而言之,两个力量如发生冲突,最后必然是相互抵消而形成浪费和无结果。这便是“新和平主义”的简明宗旨。这年6月15日在康奈尔大学举行了一个校际学生组织的“国际政治学会”讨论国际关系问题。安吉尔便是该次为时两周会议的主讲人,其他还有一些信仰和平主义的学者被邀参加。胡适出席了这次会议,并约安氏至寓所品茶交谈。会议结束,他在日记里写道:“此会告终矣,吾于此15日中得益不少,结友无数,吾和平之望益坚。”与此同时,胡适开始读杜威的一些哲学著作;对其论《力量、暴力与法律》与《力量与强迫》这两篇文章,十分佩服。他自己说是有“毕生难忘的影响”(见其口述自传)。杜氏认为,力或能是公正无私,甚或是个值得颂扬的名词。力如从可颂扬的意义上去看便是能。能便是能做工,能完成一些使命的力。能如不用来执行或达成它所负的正当使命;相反的,它却背叛了或阻挠了这一使命之实现;那末能就变成暴力了。他举了一个例子说:“炸药如果不是为了建设之用去爆破岩石;相反的,却被用去轰炸杀人,其结果是浪费而不是生产;是毁灭而不是建设;我们就不叫它能或力;我们叫它暴力。”但如何防止浪费、避免相互冲突呢?杜威提出用法律来解决,他说:“法律便是把那些在无组织状态下,可以招致冲突和浪费的能源组织起来的各种条件的一种说明书。……所谓法律……它总是……可以被看成是陈述一种能使力量发生效果的,经济有效而极少浪费的法则。”从这一观念出发,他们倡议建立一个国际间的联盟之类的组织,来处理各国之间的纠纷,维护和平。综上所述,可见杜威与安吉尔的思想是相通的,他们几乎用同样的语言来说明两个力量如何因冲突而抵消的原委。胡适在留学期间,毫无取舍,完全接受了他们的观点,而且很牢固地形成一种调和观念,这对他后来影响很大。
胡适在此次中日“二十一条”交涉过程中,所持的和平主义态度,受到同学们的批判,但他不悔改,仍坚持己见,在日记中他写道:“此次交涉,余未尝不痛心切齿,然余之乐观主义终未尽销。”又说:“不苟同于流俗,不随波逐流,不人言亦言。非吾心所谓是,虽斧斤在颈,不谓之是。行吾心所安,虽举世非之而不顾。”可见其顽固的立场。他不主张武力抗日,但对国内抵制日货的运动,则甚表赞同,他说:“东京及祖国书来、皆言抵制日货颇见实行,此亦可喜。抵制日货,乃最适宜之抗拒,吾所谓道义的抗拒之一种也。不得已而求其次,其在此乎?”首要者是什么呢?他认为:“上策为积极进行,人人努力为将来计,为百世计,所谓求三年之艾者是也。”在这次反日侵略的爱国运动中,胡适虽然受到了留美学生的严厉批判,但事件结束后,同学们对他还是友好和信任的。不久大家选举他担任《中国留美学生月报》的编辑委员;又选他任中国学生会所主办的《中国留美学生季报》(中文版)的主编。后来胡适回忆往事时,说道:“他们都是在我主张不抵抗以及反对对日作战之时,强烈反对和批判过我的。可是在我居住纽约的两年期间,他们对我都十分友好;有许多到现在还是我很好的朋友。所以我认为一个人在公开场合采取坚定的立场,择善而固执之,总是值得的。”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人民及南方护国军的声讨和打击下忧愤而死。次日消息传到美国,旅居海外华人奔走相告,拍手称快!胡适很兴奋,认为此真可谓“千夫所指,无病自死”者矣,并历数袁之罪责称:“袁氏出卖康(有为)梁(启超)其罪不可胜诛,20年来之精神、财力、人才都消耗于互相打消之内讧,皆戊戌之失败以致之也。”
其后,有人问他,今日国事大势如何?他回答说:“很有希望,因为此次革命的中坚人物,不在激烈派,而在稳健派,即从前的守旧派。”又说:我国今日现状,顽固官僚派和极端激烈派同时失败(新如黄兴,旧如袁世凯),所靠者全在稳健派的人物,如梁启超、张謇之派,名誉尚好,有此中坚,将来势力扩充,大有可为。最后他说:“将来的希望,要有一个开明强硬的在野党做这稳健党的监督,要使今日的稳健不致变成明日的顽固——如此,然后可望有一个统一共和的中国。”从以上谈话中,很明显地可以看出,胡适的政治思想正是新和平主义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他既反对封建复古,又反对暴力革命,而把希望寄托在中间改良派上,走资产阶级两党政治的道路,具体说来就是美国式的民主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