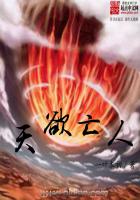苏佾见底下的众人一副惶恐不安的模样,脸上的忧色一收,泛起一抹微笑来:“大人不必惊慌,大人的招待面面俱圆且用心良苦,今日也算是宾主尽欢。虽然现在大雪突降扫了兴,但我未来恐要长居于此,要叨扰大人的地方还很多,大人万万不要拘礼,不然反而不美!”
县令见苏佾果然不怪罪的模样,听出话里有离去的意思,再想他席上心不在焉的应付,怕是有什么急事缠身扰心。如此,他确实不好再强自留人,倒不如顺水推舟成人之美,就像苏佾所说,来日方长机会还有,不需要心急。
县令想通关键,眼睛一眯,哈哈一笑,“世子所言极是,这大雪不留人,地滑风大,诸位不如早些回家,咱们来日方长,有机会再聚!有机会再聚!”
在座也有很多有家室的,毕竟聚在这里的在和城也算有头有脸,这地方远离上京,天高皇帝远管不着,就一律俗称这些人地头蛇。出门外行,家里的妻主到哪里都是羁绊,别看他们外面风光威风,回府还不都是抖不清的烂摊子。
妻在,夫不得远行。
这世上可是真的有祝英台这样兰心蕙性、忠贞不二的女子吗?或许他们还不知道什么叫巾帼不让须眉,所以理智在嗤笑,嗤笑戏本的荒唐荒谬,女子本就该养在小楼里,像温室的花朵,暖风吹都担心伤了,本就该有三夫四侍郎,说的什么一生一世一双人。
可是,感性又在一面隐含羡慕,是不是真有这样痴心的女子,或许不如祝英台才情横溢,只是若能得这一句情话,方死又有何惧!
只怕,只是痴人说梦罢了…
此时街上已无多余的行人,就这一会儿,车轮走过去都能压出来印儿,可见风雪之大。只是俗语说得好,‘冬天麦盖三层被,来年枕着馒头睡’,这雪下来,最欢喜的是农人。
马车里的阿左突然问:“公子,您读的书多,可知道这世上可真有如祝英台一样的女子?”
阿右也淡淡的看过去。
苏佾眼里本毫无波动,闻言笑了笑,心里叹这些痴儿,既然是戏本,就只当戏一看也罢。他想了想,轻声道:“天下四国,当女为宝,出生就养在小楼里,数人伺候,百人听命。那书院寂苦,且不说能否承受,单说多人同食同住,女子到底娇柔,且多有不便,怎么避人耳目?”
阿左眼神一暗,不由自嘲一笑,“阿左魔怔了,这终归戏本只能是戏本!当不得真!”就连当今天子,表面上是夫妻恩爱,背地里皇后娘娘不知养多少眷宠,历代如此,早已见怪不怪。
阿右移开视线,不言不语。
“也不知秦富怎么样了?”阿左不着痕迹的岔开话题,伸手掀开帘子瞧了一眼,只见天地灰暗,不过晚上七八点的模样,前面却一片明亮。
是被新雪映的!
这话说的苏佾眉心微皱,心里幽幽一叹,他那学生骨瘦如柴,弱小无力,如今大雪倾盆,怕是要遭罪的。又想起秦富黑黝黝的双眼,骨碌碌一转就尽是灵动之色,整个人都鲜活起来了。
“小奴,将车再赶快些!”苏佾掩下眼里的担忧,语气略微急促的对赶车的小奴嘱咐。
车缘上的小奴一听,扬声应一句,嘴里“驾!”的一声,也不用鞭子吓唬抽打,那马儿就甩着四个蹄子,踩着“哒哒哒…”的沉闷声,稳稳朝前奔去。
洁白的马路上压下去两道车痕,直直的朝前延伸,然后消失在前方的拐角处,而后面的痕迹也被覆盖,再不留一点走过的迹象。
秦富也没想到这雪说下就下,任性成这样也是没谁了,说实话如果不吹这如刀刮的西北风,她也不至于如此狼狈。当然秦富也不会傻到真的在原地一动不动,只是不能进屋,她就在外面蹦蹦跳跳,不是高抬腿就是蛙跳,最后觉得不管用,就躲在了那个倒霉的小奴身后。
小奴还奇怪秦富这般作态,一直盯着看,可转眼人就蹲在了自己身后,才知她是怕冷。虽然小奴皮糙肉厚可也有血有肉,见院子里就自己跟秦富,终于忍耐不住,将宽大的扫把往前面一挡,总算能稍微挡去冷风。
苏府本就秦伯一个看门的,拖着瘸腿日复一日在府里扫来扫去,好几天才能从东边扫到西边。秦富还在他面前骂苏家人太抠门,连洒扫的下人都没有,一个老人家当几个用。
不料这苏佾才来不到一个月,这府里陆陆续续就住进来好些人,都是从来没见过的生面孔,之前秦富凑上去打探这些人的来历,问了才知身家清白的外乡人,和城本地人很少。
莫诗戳戳他的小腿问:“你叫什么名字?你是哪里人?”
“我家在青州,南边,时逢洪涝,人活不下去,爹带着我来这里讨生活!我叫宁全。”小奴唯唯诺诺,知道秦富得公子看中,不得不说。
讨生活从南边的青州讨到这里的小城,也是不容易,秦富眼睛一转,又问:“你爹在哪里当值?”
“我爹在院子的后门处当值。”宁全有问必答,他性子软和,后面的话都快要哭出来了,沮丧着脸,“现在都这么晚了,我爹肯定到处找我呢,他可就我这么一个儿子!”
秦富也觉得他可怜,无缘无故看热闹还被牵连,她大气的在后面拍拍宁全的肩膀,义正言辞道:“宁全你放心,既然你是因为我才遭罪,我自然不能做那无情无义之徒,待会儿老师回来我替你求情!保你无事!”
宁全眉头拧在一起,虽然他知道自己笨,可明显秦富已经自身难保了,真的可以替自己求情吗?但他心里还是感动的无以复加,应了一声,努力伸展肩膀,尽大可能给身后的秦富挡风!
因为说话要张嘴总是吃冷风,所以,两人也就不再聊来聊去了,默默等待着苏佾回来。
苏佾戌时快尽才回来,等步履匆匆来到主院,一眼就看到正蹲在地上的秦富和那个小奴,雪花飘飘,都快将两个人盖成雪人了。
“子君!”
上下牙齿打架的秦富一听这话就激动了,哆哆嗦嗦喊道:“老师!学生知错了!”
宁全有模学样,也哆哆嗦嗦喊:“公子,小奴知错了!”
阿左阿右忍笑。
苏佾赶紧走过去,低头一看,秦富正可怜兮兮的缩成一团,头上身上都是雪花,黑瘦的脸也冻得青紫,雪花落在上面也不消,就随着秦富的抖动滑落。
一看她这样,苏佾心里再大的火气也灭了,面上却没有软半分,只问她:“错在哪里?”
“错在不该阳奉阴违欺瞒老师,还没大没小戏弄阿右!”因为每次苏佾问起来秦富的礼仪绣工,她总是信誓旦旦说进步神速。
阿左不爱搬弄是非,阿右自诩正人君子,不屑于做打小报告这种小人行径,所以每次都睁眼看着秦富说瞎话!
至于戏弄阿右,可不仅仅是今天这样,更是因为这个正人君子的帽子是秦富给他扣上去的,所以说句戏弄也不为过。
苏佾盯着她明亮的双眸,再问:“还有呢?”
“学生顽劣不堪,对礼仪绣工心浮气躁应付了事,这些日子并无多大进展,辜负老师期望……”秦富低头,视线里闪现苏佾的白色衣摆,随风飞扬,比这洁白的雪花更洁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