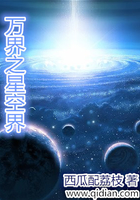翌日破晓,二明王早早传令归州招讨使何下廖及校尉哈麻、乌贵等诸将,齐集城南小校场上,又宣读了讨伐霸山草贼檄。数声炮响之后,三千兵马启动,一路枪戈如林,战旗飘翻,径出了归州城。
大军迅疾而行,于次日清晨,业已兵至霸山脚下。三军稳住,排开一字长蛇阵,旗幡卷空,兵威甚猛。
二明王坐在大红幢帐马车内,四周幢帐罩得铁紧,毕竟也有些惧怕那天阳之光哩。他掀开幢帐一角,对招讨使何下廖道:“听说何招讨身怀道术,擅放烟雾,此次务必尽早拿下这些草贼,本大人自可记你大功一件,上报朝廷,封官加禄。若遇到反抗,一律格杀勿论!”
原来这何下廖少学道术,修练了一口黄葫芦,能放三才烟气,虽只放得三番,常人却不是对手,便叫他在乱世里头谋得了一个归州城招讨使的职务。他道行极浅,自然识不出来州府大人的庐山真面目,只当剿匪,尽忠朝庭。
当际,何下廖拱揖高声道:“卑职虽然道术不高,擒拿这伙蟊贼,也有九成的把握。大人尽管放心!不叫半刻,必献于帐下。”
何下廖只当霸山众人都是一群乌合之众,又仗有左术才发下这般大话!说罢,他双脚一磕乌烟驹,提紧缰索,冲到阵前传令。
副将哈麻早就想立个头功,请过令,一促花斑马冲出阵来,把春秋大刀迎空展开,寒光闪闪,冲着霸山西寨头上大喊:“霸山的草贼听好了:你们攻击朝庭,杀人越货,作恶多端!今天大人亲自率军征剿。想做良民的,快打开寨门投降,还可以保住一条小命!不想做良民的,定要诛杀你们的九族!”
哈麻随着招讨使何下廖曾征剿过几回草寇,这一套官腔话儿虽忒长,他倒喊得顺溜响亮!但过了许久,不见有人应话,哈麻就一边兜马在阵前来回走动,一边继续叫喊扬威。
******
霸山西寨哨楼上,罗喽头目周四早望见山下战旗兵锋,遮空蔽日,尘土播扬,滚滚而来。他急命众罗喽推岀蒺藜巨木阵,横在道口上,关紧了寨门,又叫各把兵械弓矢都准备好了,然后翻身上马,一溜烟奔聚义厅来报告。
玄姬入归州城寻父,负了阴伤而归,连夜被众人送入仰天洞中,与田钍道人一起在洞内盘坐定气,调元养身。华乢吩咐洞外几个喽罗看护仔细,便和几位好汉下了山洞,各自回房安息去了。
刚过了一日。这日早上,众好汉正聚在聚义厅吃早茶,那厅外校武场上,周四已慌慌张张跃下马来,喘着大气奔入来报:“各位大王,不得了了!朝庭派来无数官兵,在山下排开阵势,正在叫阵挑战哩!”
众人一惊。
华乢急问道:“有多少人马?”
“乌压压一片,不知有多少人马。”周四回道。
“莫不是那二明王已知道了黄金藏在这儿?”陟宫疑惑。
“知道了又待怎样?都是些人,又不是鬼!怕它个鸟蛋!”郑嵬满不在乎。
说过,郑嵬拉住朱阙要往厅外奔去:“兄弟,我俩个去打一仗,管教杀他们个片甲不留,有来无回。”
“哥哥暂等一会。我那副行头还在后头;哥哥的趁手傢伙也连着几天打造好了一对。我去拿来。”朱阙说着朝后厅去了。
谭锺沉思道:“官兵既然来了,就绝不会善甘罢休!只有杀退了他们才有出路。”
众人纷纷点头称是,便各去披挂妥当,取了兵器,上马率八百罗喽风吹火急地奔西寨而来。
郑嵬、朱阙已各提着一副大锤,先走一步了。只见二人并肩攒行,疾步如飞,不多时就先到了西寨。
朱阙火暴性急,命罗喽打开寨门,撤开蒺藜围子,脚步踏起一阵阵黄尘飞扬,来到了平阳之地,对着高呼不止的哈麻,瞪眼骂道:“什么鸟人?敢到咱霸山逞凶!”
哈麻早觑见一个黑不溜湫的壮汉下了山道,立在对面不远处,就在马上把大刀一指:“你这个烧炭的黑汉,怎识得爷爷?爷爷乃是归州府招讨使麾下正职校尉哈麻!”
朱阙由来读不得几天书,也识不了几个字,却会些插浑打科,和郑嵬正是人壬府里的一对憨活宝。他听到那一长溜儿话却只记下了几个字,于是大笑道:“蛤蟆(哈麻)?什么‘死(使)’的蛤蟆?哪有那么多废话?就叫‘死蛤蟆’不就得了!”说毕,一晃大锤,不由哈哈豪笑。
那些官兵听得真切,也都笑起来。
哈麻遭了嘲弄,气得双眼翻白,口吐白沫,怒道:“黑汉无理!看看谁是死蛤蟆!”
说罢,哈麻也不问朱阙名姓,催动花斑马赶近,抡大砍刀照他脖子上劈过来。
这两军沙场搦战,无论敌国还是官贼,都要通姓报名。毕竟是为什么呢?却原是一来显武功,扬威名;二来也好在录功薄上填挂姓名报功。哈麻气得七窍内冒烟,也顾不了许多繁文褥节,只想趁早一刀结果了朱阙。
朱阙觑见哈麻奔马抡刀之势,知是个庸将,会不得几手!又见郑嵬在一旁观战,不由想逞那英雄手段,戏耍这庸将一回。待那马奔近来,只一闪身就让过刀锋。
花斑马却早奔出几十米开外,踏起一地黄尘飞扬。哈麻还当朱阙是小泥鳅哩!一刀劈下去指定了叫他脑袋搬家。那力道便使得过了劲儿,差些摔下马来。他摇摇晃晃地拔转马头,稳定了身子后,捂正了头盔,吐两口吐沫在掌心里,攥紧了刀杆,撒马蹄儿又冲将过来。力劈华山,呼地声响又一刀砍下来。
朱阙复灵巧地又躲开去。
如此交手了十多个来回,那大刀,刀刀劈空,直累得哈麻来回兜马,瞪大眼儿呼哧呼哧喘气,甚为可笑。
朱阙双手握锤相撞个不停,笑道:“爷爷还没开打哩!你倒真象个过冬的癞蛤蟆,快撑腿了帐了!”
哈麻两眼赤红,腮帮子咬紧,鼓着气泡儿一般,还真似个蛤蟆哩!他缓了缓气喘,又拍马舞刀急杀过来。
这番朱阙倒再没躲让,也不用大锤去磕那大刀,只左手握住双锤,瞅准马来,钻身靠近马右侧,右手猛然带紧马的缰绳。
花斑马正奔得甚急,猛然被带紧了脑络子,低头嘶溜溜痛嘶不绝,停了下来!哈麻跨坐不住,“呼”地一声滚雪球般直掼出去三四丈远。整个脸盘儿硬生生栽在地上,春秋大刀也抛出老远。侥幸他有些武功底子,双掌运力卸了一些力道!但爬将起来,晕头转向已摸不着北,只在原地崴来崴去,满脸乌血黄土,鼻梁也擂得扁塌了,口内还啃着一绺儿枯草,只怕爹娘也认不出来了哩!
乌贵一旁瞭阵多时,见堂堂的朝庭副将尽遭耍猴般的戏弄,自觉羞侮,便一边纵白马疾冲出来,一边呼喝众官兵将哈麻拖回本阵,怕被敌人打死,枭了首级示威。
哈麻就哦呀唉哟的捂着花脸被横拉竖曵拖下阵去了。
******
华乢留谭煄守寨,自己早已与陟宫、风玉堂率领了八百多罗喽出了西寨山门,在斜坡上摆下阵势瞭阵。那些罗喽此时看见自家大王获胜,一个个不断挥舞兵器战旗,高声叫好。诸好汉也快意高笑不止。
这厢众官兵人人忍笑不住,噗哧哧都笑出声来,但更惧怕起朱阙的神勇来了。
乌贵催白马在阵前站住,一挺大铁枪喝道:“无名小卒不要猖狂,速报上姓名来,好叫我乌贵在军功簿上记上一功。”
朱阙刚笑落了声音,忽听到“乌贵”二字,又是跌足大笑不止:“刚去了个死蛤蟆,又来了个活乌龟!这朝廷里尽出些乌龟蛤蟆哇!”
这名唤“贵”实寄富贵之意,名儿不错,怪只怪那个乌姓!向日里部下也称一声贵爷,多贵气哩!只到了这山贼口里便变成了“乌龟”。
乌贵咬牙切齿,却极冷静,讽刺道:“恐怕你这草寇,无爹无娘,也无个姓名啊!”
乌贵却有点真本事哩,善打袖箭。他知道朱阙膂力过人,脚步敏捷,若斗起武来没有多少好果子吃,弄不好还坏了性命,于是反激诱他上来,暗里却早扣紧了一支袖箭在左手内,想猝施杀手,一招致命,再枭了他的首级。如此既可震慑山匪,也可扬一份威名,那如意小算盘拔弄得还忒不赖哇!
朱阙却实是少小孤儿,一向江湖飘泊,前几年流落到荆州,才被田钍道人带上霸山,学了些本领,委实不知爹娘是谁哩!这话歪打正着,正伤人心!朱阙果然就被激怒了来,也只当和哈麻一样的囊糠货色,舞锤飞奔上来。
乌贵冷笑数声,放朱阙奔近来,约有二十米远近,忽拔动蝴蝶翅,将一枝袖箭往他左胸上射去。
凭气力朱阙算得力拔山兮气盖世,凭机巧暗术却实在憨赣!那一枝袖箭粗细不过竹筷,长仅六、七寸,在日头下闪着银光,飞速甚疾。待朱阙觑见寒光,那袖箭已流星般飞来,躲闪不及,不由大叫一声:“啊呀!我的妈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