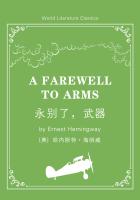汇款单上没有地址,邮戳也有些模糊,但有一个字让我猜到了这是什么地方。
1.天底下的事儿,有的就是滑稽
公元一九八五年,清源村。
山坡下,一辆北京吉普车摇摇晃晃地行进在崎岖的山路上。从吉普车涂抹的蓝白的颜色,站在坡上等着自家羊群回来的村民们认出这是县公安局的警车,但他们却不知道这是公安局长的车子。不过,今天在副驾驶上坐着的不是局长,是派出所的李所长。警车行进到山坡下,再往上走是一条羊肠小道,两边是峭壁般的土坡,汽车根本开不到上面去。这时,吉普车司机停下车,李所长第一个跳下来,接着又下来两位穿警服的人。认识李所长的村民不禁有些错愕。他们想,李所长亲自出马,又看那两个陌生的警察和这少有的阵势,抓捕的一定是重要的案犯,那案犯会是谁呢?就在村民们嘀嘀咕咕的猜测中,李所长问:“钟涛家在哪儿?”村民们面面相觑,无人回答。清源村有三户姓钟的人家,这钟姓人家的孩子,要么叫狗子、铁蛋,要么叫大柱子。至于哪家的孩子叫钟涛,村民们一时还真说不上来。沉寂了片刻,终于,人群中站出一个中年人说:“钟涛可能是钟孝义的儿子,这孩子从小就打架,这回又惹大祸了吧。”说着,便带着李所长直奔钟孝义家,钟孝义猫着腰铡草,见公安局的进了院,慌得差点铡了手指。李所长说:“你就是钟涛的父亲?”钟孝义一听是来抓钟涛,悬着的心一下放进了肚子。但转念一想,钟涛也是自己的侄子,被公安抓了哪成。他灵机一动,先把仨警察让进屋里,借着倒开水的机会,告诉妻子赶快去钟涛家报信,让钟涛出去躲躲。钟孝义的妻子一听,解掉围裙匆匆忙忙地到钟涛家报信去了,一进院子便焦急地嚷嚷:“他大妈,快点吧,让钟涛出去躲躲,人家公安局来抓你家儿子了。”钟涛的爷爷一听,二话没说,把旱烟袋插进腰里,又从小篾筐里抓了一把烟叶,甩开步子向山后走了。
他是到山后找钟涛。
天底下的事儿,有的就是滑稽。比如像钟涛,本来是要做警察了,要到省城做预备警官,可被好心的亲戚理解偏了,吓得钟涛的爷爷直奔后山去挽救孙子。钟涛正在后山的沟里挖甘草。甘草是山上最值钱的东西,卖到县城的医药公司一斤能卖3块钱。挖到开学时,也能收入不少钱。钟涛听见沉重的脚步声,转过脸来一看是爷爷风风火火地过来了。他吓了一跳,以为家里出了什么大事。
爷爷拽了他的胳膊,急急地说:“别挖了,快跟爷爷到山里躲躲。”钟涛一下懵了,挣脱开爷爷的手问:“怎么了,为啥要出去躲呀?”
爷爷指着山前说:“公安局来村子里了,说是来抓你的。你还不快躲一躲。”
钟涛说:“我没干犯法的事儿,凭什么抓我呀,我不躲。这不是躲的事儿。我回家看看。”
爷爷瞪起眼珠子说:“这都啥时候了,还磨叽。你没听说书的说,有个说法叫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咱还是躲躲,好汉不吃眼前亏,你听爷爷的肯定错不了。”
钟涛还想争辩,爷爷已经拖着他向沟底的山洞子里走了。这个洞子是日本人修筑的工事,全村只有三个人知道,那两个已经死了,现在只有钟涛的爷爷知道这个地方。
爷俩藏好后,四周完全静了下来,连鸟和昆虫的声音都没有,爷爷也不说话,甚至没敢点燃一袋烟。
家里却乱了。李所长带着的两位穿警服房的人,一位是县公安局政工办的马主任,另一位是省警察学院负责招生的学生处副处长夏原。李所长问钟白法:“你儿子呢?”
钟白法装傻:“去县城了,走好几天了。”
李所长信以为真,挠了挠头,对政工办主任和马副处长说:“这怎么办啊?”
马主任说:“老钟,你儿子被省警察学院看中了。这次是来面试的。你赶快想想办法怎么能通知到钟涛。”
钟白法一听,失口道:“不是抓钟涛啊。”
李所长急了:“什么,谁说要抓人了?对了,你儿子八成是躲起来了吧。你还愣着干什么,赶快去找吧。”
钟白法将信将疑地望着李所长:“真的不是抓人?”
李所长说:“谁告诉你抓人了,你儿子是要被录取到警察学院上学去,很快就和我一样当警察了,是好事。”
钟白法这才放下心来,猛然意识到这是喜从天降,赶快催促自己的女人和那个报信的婶子沏茶倒水招待客人。
“钟涛呢?”李所长问。
这是关键问题。钟涛呢?
马主任扬了扬下巴,沉下脸说:“冲这条就不适合做警察,这都什么心理、什么素质,就算犯法也不能逃啊。真要干了犯法的事儿,你们这样做,那也犯法,你们这一家子也都得定成包庇罪。躲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吗?”
然后转过来脸对李所长和夏原说:“依我看,还是回去吧。咱们另外再选一个吧。”
马主任即兴发挥的普法教育让钟白法立刻慌了,差点给马主任跪下。李所长解围说:“马主任、夏处长,农民的孩子能考上大学不容易,咱别轻易放弃了,等等看。你们不是看档案了,这孩子是个当警察的料,条件那么好,不招是不是可惜了?!”
夏原转过脸对钟白法说:“你赶快去找好吧,既然来了,我们还是看看。”
夏原是代表警察学院招生的,警察院校要对被录取的考生提前面试政审,只有这两项合格了,才能被录取,这就是警察院校招生的特殊性。县公安局政工办的马主任的任务是配合警察学院招生。李所长则要向夏原处长介绍钟涛家的历史背景、有无前科、现实表现等等的一些情况,用他们的话说,这就叫政审。在钟涛的报考志愿里没有报考省警察学院,不是不想当警察,是不敢填报。那时,警察学院是很热门的院校。录取的学生条件也很高。要么是家里特有背景,但那个年代还算公平,有背景也只能是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歪瓜裂枣的人,还是难以踏进公安院校的大门。
夏原原本是来招县工商局一个副局长的儿子。面试的时候,夏原发现这个学生的视力可能有问题,到县医院一复查,果然戴着隐形眼镜。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隐形眼镜也是稀罕玩意,好多人听都没听说过。这不是弄虚作假吗?夏原很生气,在这个学生的面试表上郑重地写了仨字:不合格。但最后还是负责任地把这个学生推荐到了对视力没有要求的师范学院。可是按照录取要求,指标不能空着,必须按规定招满。夏原从近千份学生档案中发现了钟涛。视力、身高、考试成绩、体育测试成绩,几乎全是优。夏原后来说,当时他看到钟涛的档案,兴奋的程度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差不多。
叔父钟孝义知道自己天真的判断有可能耽误侄子钟涛的前程,于是带着钟家的亲戚到山后找人,直到天完全黑了,也没见到钟涛和爷爷的影子。第二天上午,爷孙两人在洞子里猫了一夜后,估摸着警察该走了,这才回来。到了家,钟涛才知道自己差点与警察学院失之交臂,爷爷懊悔得直跺脚。
白默然说,上警院的时候,钟涛把夏原、李所长和马主任当恩人一样地看待,星期天总去夏原家帮着干家务,弄得夏原一家像捉迷藏似的躲着钟涛。当然,他最感谢的是李所长。李所长在他到省城上学的那天,专程赶到汽车站送他,还说等毕业了你就回来到咱派出所来,我给你当师傅。可是钟涛还是留在了省城。钟涛说,这是他这辈子欠下的最重的情债。
钟涛拿到第一个月工资就回县城看李所长。哪知道,李所长半年前查出肺癌晚期,癌细胞已经扩散,三个月前就死了。钟涛让李所长的老婆陪着到墓地。从李所长的墓碑上刻着的生卒年看出,他去世的时候是五十三岁。一个五十三岁的老警官,正是干事儿的时候,说没就没了。钟涛用一个月的工资买了一瓶“五粮液”。关于买五粮液的事儿,是白默然对我讲的。他说,钟涛第一学期放假去看李所长,李所长头一次见穿着警服的钟涛,乐得像看着自己的儿子。
李所长说:“钟涛等你上了班,请李叔喝‘五粮液’。”
钟涛傻乎乎地问:“‘五粮液’是什么东西呀?”
李所长哈哈笑了,指着钟涛连连道:“傻小子。你真是个傻小子。”
等开学回到学校,钟涛问白默然:“啥叫‘五粮液’?”
白默然说:“是一种很贵的酒。”后又妄加推测地说:“钟涛你可以啊,刚穿上警服就有人请你喝‘五粮液’了。”
在李所长的墓前,钟涛真的像儿子一样地跪下,从包里取出那瓶“五粮液”,拧开瓶盖,把酒洒在墓前。李所长老婆急忙制止说:“孩子,别全倒了,老李这辈子也没喝过这么好的酒,意思一下就行了。”
钟涛固执地把酒全部洒在了李所长的墓前,然后哭了。全身抽搐的像受了委屈的孩子。
2.清源,第一次
这是发生在二十六年前的故事。巧合的是,我到达清源的时间,竟和二十六年前李所长带人到达清源的时间天意般地吻合。只是我没有李所长那么幸运和隆重。村子里只要能走能跑智力还算健全的,都在市县或者省城甚至更远的地方打工谋生,冷清的村庄和那些留守在村子里的耄耋老人一样寂寞地消磨着慵懒的时光。我的“切诺基”停在山坳下,下了车改作徒步前行,仰脸望向村子口,那里空无一人,只有几条土狗懒洋洋地卧在山坡上晒太阳。对于我这个陌生人的出现竟然毫无警觉,好像懒得理我。一边走,一边左顾右盼,右首的山坡下,已经泛黄的麦田长势还不错,这些留守老人把庄稼侍弄成这样,让我暗自佩服。我采访过许多的留守村庄,不少村庄的房子残垣断瓦破败不堪,许多房子早就没有人住了,门和窗子用砖块或者土坯封堵砌死;有的年久失修,几乎要倒塌了。而田地除了杂草已没有庄稼。清源村却仍然呈现着昂然的生机。
听了白默然的话,我去向小学同学“排骨”借他的那辆“切诺基”。“排骨”是那个同学的绰号,顾名思义,就是瘦。瘦的时候是在上小学,如今的“排骨”也发福了,像被发酵粉催起来的面包。“排骨”现在是一家装修公司的小老板,听我说去清源,不想把车借给我了。我说你那辆老掉牙的破车,我还怕开到半路抛锚呢。“排骨”说抛锚不会,我开着这车还去过西藏呢,但是过沟呀坎的慢着点开。我说你浑蛋还是心疼你这破车。“排骨”咧了咧嘴巴拍着引擎盖子说,这是私家车。我一指马路对面那辆黑色“悍马”说,那也是私家车。“排骨”撇了下嘴说,那是矿老板的车。我问排骨他是开煤矿的老板?“排骨”说是开铜矿的,这哥们最牛的事儿是挖毁了秦长城。我说,敢把秦长城给毁了的人,那不是牛,是巨牛了。“排骨”说,这哥们还有巨牛的事儿呢,他挖矿毁了一段秦长城,市文物管理所的去干涉,他根本不理,后来市文物管理所直接给中央打了一个报告,惊动了总理。有了总理的亲自批示,市公安局才去抓人,判了一年,刚释放出来,出来没多久,就买了一辆“悍马”。你说牛吧!
我沿着小道爬到坡上,已是气喘吁吁。到了离村口最近的一处院落前,院门口站着一个七八岁样子的小男孩。问他钟白法的家,他指了指他家的后面,然后在前面一溜烟地跑了,我紧跟在他后面,也差不多是小跑了起来,我知道他是要给我带路的。
这是一个干净的院落。住人的地方还是钟涛小时候住过的窑洞。到现在钟家也没盖起房子来。钟涛一直有个心愿,让爷爷和父亲、母亲住上砖房。但爷爷最后也没住上砖瓦房子。
西斜的阳光洒在这寂静的农家小院子里,我知道这没有污染没有经过杂质过滤的阳光是这个世界最本真的原生态的生命之光。我追随着那个小男孩闯进了清净的院落。窑洞门口站着一位银发干瘦的老者,一身地道的农民打扮。这样的装束打扮给我似曾相识的感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如何接近这位老人,白默然没有给我明示,他和我谈了很多的钟涛,可没有很详细地向我介绍钟白法,有的只是些围绕钟涛的只言片语,根本构不成整体的印象。按照我们记者的职业习惯,采访前总是要把采访对象的性格、背景了解个大概才能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可白默然什么都没说,他说,你去了清源自己去悟吧。这不扯淡吗,明明你白默然是认识钟白法的,而且怂恿我到清源的也是白默然。我突然觉得白默然似乎在利用我。可他利用我又是为了什么呢?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唯一能站得住脚的理由是他要我帮钟涛?如果我的判断准确的话,那么白默然不愧是久经沙场的老刑警,他知道怎么借助别人的力量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我明知人家在算计我、利用我,却仍然不顾一切地钻进人家设好的套子里,其原因,就是因为白默然对钟涛的那份情。我想,白默然可能是不好出面直接帮钟涛,恰好我的出现,让白默然看到了帮助钟涛解困的机会。我入套了。
面对钟白法,我带着试探的意味,模棱两可地自我介绍:“我是北江来的。”
钟白法果然中计,笑呵呵地说:“你和钟涛是同事吧。钟涛咋没回来?”
借着这句话,我判断钟白法还不知道钟涛出事。也就是说,钟涛根本就没回过家,直接亡命天涯了。
既然如此,那我决不能提钟涛出事儿的话题。我说:“我不是钟涛的同事,我是北江晨报的记者,是采访钟涛的。”
钟白法糊涂了:“你采访钟涛该到公安局的,怎么到这儿来了?”
我说:“我是采访钟涛小时候的事儿,比如上学呀,帮助村里人做好事呀等等。”
钟白法警觉地一愣:“钟涛没出啥事儿吧?听你这口气像采访黄继光、董存瑞似的。”
“没有,没有,钟涛好着呢!他是全省的劳模,不只是他一个,我们要采访好多人呢。”说完,连我自己都懵了。我低估了钟白法的敏感。看来,这个山沟里的农民也不是好糊弄的。
钟白法把我让进窑洞里,介绍了窑洞里的人,有钟涛的母亲,还有钟涛的叔叔钟孝义。那个为我带路的小男孩是钟孝义的孙子。窑洞的墙壁上,挂着一面镜框,里面有钟涛一家三口的照片。还有钟涛和白默然的合影。这是一张彩色照片,两人穿着的是八三式警服,警服的颜色是橄榄绿,领口两边是鲜红的领章,衬托着风华正茂的年纪。这照片应该是两人在省警察学院上学时照的,那时八三式警服刚刚在全国公安机关列装。如果说,军服曾经在六、七十年代风靡一时,那么警服在钟涛和白默然走向社会、选择职业的八十年代,同样是许多年轻人的梦想。白默然说,那时他做梦都想当警察,所以才发愤地读书,就是为了能考上警察学院。我说,钟涛也是这样的想法吗?白默然说,你想呀,他能不想吗?只是他不敢想,那时的警察学院说实话门槛挺高的。所以才有那么多的人趋之若鹜。而且那个年代的警察也很受人尊敬,不像现在,警察跟他妈过街老鼠似的,你上街瞅瞅,除了交警,有几个穿警服的。说实话,一个社会,警察没有职业的荣誉感不是好事。我问,为什么会这样?白默然说,有人把这归咎于某些警察的腐败,说是一块臭肉毁了一锅汤。我不这么认为,你说,现在有些人公开喊着号子要打警察,这是为什么?是警察腐败吗?
我感动于白默然的真诚。许多人与记者相处,总是带着几分小心和戒备,像白默然这样坦诚地与我交流,我真的有些受宠若惊了。
我感动于钟白法一家的质朴与热情,这大概就是中国农民最本真的情感。我看得出来,钟白法家的日子过得捉襟见肘,那破旧的窑洞像清源村的一块补丁嵌合在黄土高原的沟壑之中。
夜晚,我躺在钟涛住过的那间偏窑里。钟涛的母亲为我送过来一套浆洗干净的被褥。乡村的夜晚寂静无声,习惯了城市的喧闹,我一下竟有些不大适应这乡村的静谧。远处的几声犬吠,倒像是这静谧的乡村里的噪音。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临睡前,钟白法和我谈了一晚上的钟涛,但都是钟涛从小学到高中的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而且,钟白法这位看上去未见过世面的乡村老农,从他嘴里讲出的钟涛的趣事,一桩桩、一件件,差不多都是学雷锋做好事、少年赖宁之类的英雄故事。钟白法讲得极有兴致,我听得哈欠连天没几件记在脑子里。我想得到的信息是钟涛在出事后,是否回过家?是否来过信息?哪怕一封信,或者一个电话。回家的事儿,显然已经排除。钟涛自出事后,确实没有回过家。 那信和电话呢?
不能这样!在明天离开清源之前,我必须搞清楚这些问题。否则,这趟清源我算白来了。
天快蒙蒙亮时,我听到了公鸡的啼鸣。我一轱辘坐起来,掀开窗子上的粗布帘子的一角向院子里张望,却找不到公鸡的影子,我努力地判断着声音的方位,仍然不知道声音出自哪里。十几年了,久违的鸡鸣让我像初恋似的兴奋。
3.奇怪的人影
我穿好衣裤跳下炕,再系好鞋带走出窑洞。这时,天还没有完全透亮,朦朦胧胧的。这是夏日乡间的黎明,连空气都是那么的清新馥郁。我寻找着鸡鸣的声音,一转身,看到了一个影子,但不是啼鸣的公鸡,是人影。是的,绝对是人影。但那影子离院子足有十几米远,而且又是在朦胧的黎明中,我模模糊糊地无法看清对方的长相。我下意识地冲着人影喊了一声:“谁,干什么呢?”我一喊,那人像猴子似的敏捷地跑了。我拉开钟家的院门冲了出去。严格地说,钟家的院门根本不能称其为门,也就是个木栅栏。我的喊声惊扰了钟白法,屋子里先是一连串的咳嗽声,接着钟白法喊道:“谁呀?”我顾不上答话,径直向那人离去的方向追去。他奔跑的速度很快,像练过短跑的运动员。我很快就被对方甩掉了。但我知道了他奔逃的方向,就是我停车的那个坡底小道。我追到半坡时,看见一辆黑色的越野车启动,并且很快地开走了。越野车没有开灯,行驶出去很远才把大灯打开,然后加大油门扬长而去。很显然,这是一个经过专业训练的高手,他打开车灯的距离恰好在正常人的视线之外,这个距离让我根本看不清汽车的车型和车牌号。我一口气跑到坡下,查看我的“切诺基”。果然车门有被撬动的痕迹。不过车内的东西完好无损。事实上,车里也没什么东西,我随身带着的采访包放在了我住的那间窑洞里。我又试了试汽车马达,仍然能正常发动。我坐在驾驶座上百思不解。
他是谁?
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钟白法走过来了。也许是走得急了,到了我的车前,竟咳喘得说不了话。
我关切地问:“你的气管不好?”
钟白法又咳嗽了几声,摆着手说:“不要紧,老毛病了。早晨起来咳得厉害,过了早晨,到前晌就好些了。你说怪不怪。”
“哦,哦,那得上医院看看。”我脑子里还想着那奇怪的人影和绝尘而去的汽车,心不在焉地应着。
钟白法问我:“你追的是谁呀?咱这地方穷,贼娃子也不上这儿来。你看花眼了吧。”
看着钟白法,我忽然想到了钟涛。
那远去的绝尘的怪影会是钟涛吗?
我带着满腹的疑问返回了钟家的窑洞。钟涛的母亲已经做好了早饭。馒头、鸡蛋、玉米粥和一碟咸菜。因为早晨的事儿,我没吃多少。进屋后,我一直无精打采地坐着,钟涛的母亲一个劲儿地催促我多吃点儿。那表情又带着几分招待不周的歉意。我不知道这简单的早饭是钟家特意为我准备的,还是他们平日里的饭食。这样的季节,在偏僻的离集市较远的乡村,如果不是提前准备的话,他们真的拿不出什么可以招待客人的东西。只能吃些简单的菜食。所以我的突然造访,也让这家人有点猝不及防的紧张和慌乱。又因为凌晨的那个奇怪的背影,我决定离开清源。
离开钟家时,钟涛嫁到县城的妹妹回来了。她转交给钟白法一张汇款单,数目是五千元。汇款单上没有地址,邮戳也有些模糊,但有一个字让我猜到了这是什么地方。这个字是: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