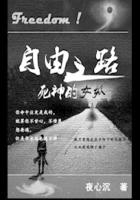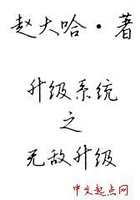雪夜皎洁,月光将大地映得发亮,本应是夜深人静的时分,常山城中却是分外热闹。
士兵卸下了兵甲,民众卸下了警备,人人围坐在巨大的火堆旁,扑啦啦作响的柴木以及赤色的火焰将他们白日的疲惫一扫而光。
妙曼舞女在将领面前扭着腰肢,美酒与好肉不断地被呈上,欢声笑语仿佛驱散了整个冬日的酷寒。这是胜利者应得的荣光,每个人都在尽情享受此刻欢愉,似乎全然无人记得,几个时辰前将将结束的血腥厮杀。
几个契丹女子身着华服,媚眼如丝地朝赵谨俞身旁拥去,送酒的时候特意将丰满的胸脯向上挺了挺,倒是惹得周围的几位将士口水直流。
赵谨俞纵然在战场上是以一当百的英雄,可面对如此艳色美人也是略有些吃不消。他俊秀的脸上写满了窘迫,只得将送到嘴边的酒盏一一接下。
好容易待得那几名女子离去,他摇摇晃晃地走到我旁边坐下,望着我的眼神里已有些醉了,却仍是斟满了一杯酒,递给我道:“来,阿持,此杯敬你,敬你又一次救了我。”
我笑嘻嘻地接下喝了,反问道:“这次你可不敢再小瞧我了吧?”
他连连摆手:“不敢了不敢了,咱们阿持是女中豪杰,配得上巾帼不让须眉一称。”
我得意洋洋:“那是自然。”
他笑了笑没有接话,忽的直愣愣地盯着我的侧脸,看得我半边脸都开始烧热了。我有些不敢偏头,只闷声喝下一口酒,朝空气问道:“你中邪了?怎的这样看我。”
“大约是中了吧。”只听得他在我耳旁悠悠的说了一句,半晌才接着道:“我在想,你究竟是何人?为何每次危难之时你总会出现?你身怀武功,可与**流,又胆识过人,哪一条都不是寻常女子可有的。你究竟是谁?阿持,你究竟怎的,这么不同?”
我答不出来,总不能就这样告诉他我乃妖族,自然与凡人有异,于是我道:“若是人人都一样,这世间岂不无趣得很?何必思虑良多,享受当下不好么?”
他顿了顿,将目光从我身上收回,投之火堆周围的众人,叹道:“是,享受当下方是最重要,毕竟像今夜这般安宁的时光,也不是时时都有的。”
酒足饭饱,当地平民开始牵着手围着火堆跳舞,口中哼唱着古老的民族歌谣,渐渐的,连围观的士兵也都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赵谨俞问道:“阿持,去跳舞么?”
“我不会…”
“我教你,走啊。”他不容我拒绝,竟直接拉起我走进了人群。
这是他第一次牵我的手,我紧张得手心都出了汗,纵然身边分外嘈杂却也压不住重重的心跳声。他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我一时间竟全都听不清,也看不清了,迷迷糊糊中,只伴着耳边的歌谣,觉着自己轻飘飘的,如同一只会起舞的纸人儿。
我是不是也贪杯喝醉了?不然怎么瞧着他的脸,也有些微醺呢?
那天晚上,众人载歌载舞,欢庆了许久,至了子夜时分,方才散了。
一旦过了那股热头劲儿,白日拼杀的疲劳感就如山般压来,回去的路上,我见着好几名士兵甚至来不及回到房中,因着酒力与疲惫太重,便直接倒地睡着了。军中于是派了些许清醒的人,专门将那些人扶入宅邸,以免造成在雪地酣睡,第二日早晨冻死的惨剧。
我回到房中,在床上翻来覆去,却是怎么也睡不着。我一遍一遍地盯着自己的左手看,手心仿佛还残留那种细腻的温度,这样一想,更是辗转反侧,索性决定去外边走走,让寒风吹醒我混沌的思维。
万物俱籁,街上此时已无甚人迹了,我走了一段,却见李光弼和赵谨俞二人立于已燃尽的火堆前。
李光弼站得朝前些,赵谨俞静默于他身后。月光倾泻,将他们的身影勾勒得分外寂寥,与适才的热闹欢愉形成强烈的对比。
李光弼手持一杯酒,将其洒落于木炭上,还未熄灭的些许火光发出呲呲的声响,在寂静的的深夜里显得分外清晰。
良久,才听得他缓缓地,而又沉重地道:“你们放心的去吧,不必记挂家中亲人,我定会替你们照顾好。”
“你们将性命交予我,我却未能护你们周全,是我的过错。”
“你们都是大唐真正的好男儿,你们且先去,待天下安定了,光弼必去阴曹地府陪你们。”
说完,他似是不能自持,剧烈的咳嗽起来。
赵谨俞忙上前轻轻拍打李光弼的背部,宽慰道:“义父,更深露重,你莫过于伤怀了。”
李光弼摇摇头,叹道:“常山一役,我身上背负的人命又重了许多。”
“义父不可过于自责,两军交战,死伤必不可免,能有现下这个结果,已是很好了。再说身为男儿,自当为国捐躯,在战场上抛洒热血,慷慨赴死方是正道。”
李光弼略感欣慰:“谨俞,你长大了,不负你娘临终遗托。”说完,目光却又转为担忧:“于公,我是三军将领,你作为武将有此觉悟,我应感到开心;可于私,我又是你的父亲,自小就拿你当亲生儿子来看,如今想到,你日后性命忧患,我心内又不得不感伤非常。”
赵谨俞恭敬道:“义父放心,孩儿谨记义父养育之恩,孩儿定会爱惜性命,不让义父悲伤。”
李光弼点了点头,正欲再说些什么,却抬眼一看发现我在角落处。
我不知是否该上前打扰,只得隔着距离,遥遥朝着他行了一个礼。
他朝我微微一笑算是回应,之后压低声音对赵谨俞说了一句什么,我却听不大清,只见赵谨俞拜别了他,朝我走来。
“阿持,怎的这么晚还在外边转悠?”赵谨俞踩着落雪来到我面前,英俊的面容遮档了我头上的半片月光,想起适才跳舞时,他也是离我这样近的,我心跳忽的就漏了一拍。
“我…我睡不着。”
“白日里费了这么多力气,夜里还不安睡,你精力也真够充沛的。”他偏头思虑了一瞬,又问道:“那一起在城周走走可好?”
我点点头。
现下无风,就算是雪夜,也未过于寒冷。城中居民皆已安歇,连昏黄的烛灯也没有几盏,但好在今夜无云遮月,所以路面均被照得很清晰。
我伴随他左右,悠悠行着,一路静默无言,他似乎心事很重,我唯恐唐突了他。
再走了一段,我终是忍不住这般静谧,出声小心的问道:“李将军时常如此吗?”
“嗯?什么?”他回过神来,恍惚地问我。
“我说,李将军时常如此吗?就是一个人给故去的将士敬酒。”、
他此会已恢复平日里的样子了,点点头道“是,每当一场战役结束,无论是败是胜,义父皆会祭拜那些战死沙场的将士,并给他们的家人送去安顿余生的钱财。”
我无不敬佩地道:“诚如众人所言,李将军对待军中士兵十分真心。”
“将心比心,所以士兵们才能对义父也报以真心,为他一声令下肝脑涂地,死而后已。”
“也许,也许我不该问…”我踌躇了一会,道:“适才我听见你们二人讲话,赵大哥,你的母亲,已故去了么?”
他听及此,出乎意料地没有多少悲伤,而是很坦然地道:“是啊,我很小的时候她就不在了,现下连她的模样我都记不大清了。”
“那,你是如何拜李将军为父的?”
他答道“我娘和义父原是表兄妹,二人青梅竹马一同长大,早已订下了婚约。义父对我娘是痴情一片,可我娘对义父却只止于兄长之情。后来我娘遇到了我爹,情根深种,为了与他厮守不惜与家族断绝关系,义父纵然心痛不已,可为了所爱之人幸福,也只好毅然放手。我娘跟着我爹,又有了我,日子虽然清贫可也自在快活。但好景不长,我四岁那年,我爹遭贪官所害,丢了性命,我娘心中悲愤,不久便染上恶疾,命不久矣。临终时,她找到我义父,将年幼的我托付给他,并对他说,她这一生最对不住的人,就是他。但她这一生最信任的人,也是他。她希望他能将我培养成一名铁骨铮铮的沙场男儿,莫要再步我爹文士后尘。那之后,义父便收我为义子,教我骑马,习武,念兵书,养育我成人。”
我有些忐忑:“对不起…让你想起不开心的事了…”
他笑了笑,道:“没什么不开心的,都是前尘旧事罢了。”顿了顿,又道:“我说完了,那该你说了。”
“我?我说什么?”
“说说你的家乡,你的家人,你的过往。你不是曾说,你的家乡永不落雪,当真如此吗?”
“自然当真。不仅如此,那里还生着许多奇花异草,处处芦苇飘香,风一吹呀,美不胜收。”
“说得不像是凡间,倒像是书中所写的仙居圣地了。那你的家人呢?”
我歪着头想了想,慢慢地道:“我的家人…阿爹阿妈都是很和蔼的人,阿姐长得很是好看,又温柔又贤淑,不过你不用想了,她已经嫁人了~还有的,就是我阿哥了…阿哥这人,平心而论也是仪表堂堂的,就是脾气不好了些,若是能对我再宽厚那么一丢丢,就更好了。”
他嘴角的笑更甚了,过了一会儿,又问我道:“如今你这般年纪的女子,大多已言及婚嫁了,不知你家里人,是否有给你定下亲事?”
我摇摇头:“没有啊,阿妈常说,我是不知轻重的小丫头,没人愿意娶我的。”
他却没有接话,步子也停下了,我转头一瞥,他正深深地看着我,眼眸里的亮色不知是月光明晃,还是雪色映照。
“阿持…”
他缓缓开口,眸子里的那份温情几乎要将我吸进去,我失了神地回望他,只觉着心中养了一只小鹿,此刻它正用它的小蹄子,调皮地在我心口踏来踏去。
相视良久,他却仿佛忽的想起什么似的,将目光转向别处,不再望我,只哑着声音道:“你出来这么些时日,家里人定是着急坏了,过几天,我便派人送你回家可好?”
我心中的小鹿像是浸了水,刹时冰凉了,我无端感到烦躁得很,只道:“不,我不回去。”
“为什么?”
“不为什么,我乏了,赵大哥,阿持去睡了。”
说完,我不愿再看他一眼,转身大步离去。
原来纵是无风的雪夜,也是很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