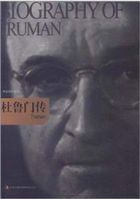1925年春,钱玄同看到《学衡》和《华国》两种杂志中有特别攻击新思潮的内容,于是他把这两种杂志寄送给胡适并附信说,“敝老师”章太炎先生写文章“骂提倡新文化新道德者为洪水猛兽”,又“骂李光地因服膺朱老爹(指朱熹——引者)穷理之说而研究天文历数为非,又以‘学者浸重物理’为‘率人类以与麟介之族比’。则反对研究科学旗帜甚为鲜明矣”(所引章太炎的话,皆出自《王文成公全书后序》,见《章太炎全集》第5册,118~119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信中又说到《学衡》第38期上吴宓、景昌极的文章(指景昌极的《评进化论》和吴宓的《白璧德论欧亚两洲文化》、《论循规蹈矩之益与纵性任情之害》。景氏文大攻西洋科学给人类带来祸患。吴氏两文本属翻译,但皆有引言和按语,申明其反对批判礼教,主张“爱护先圣先贤开创之精神教化”,甚至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制度辩护。),其“议论思想昏乱到什么地位?”他恳切要求胡适出来“打些思想界的防毒针和消毒针”,“做思想界的医生”(拙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40册,351~356页。)。胡适回信说,他读过《华国》与《学衡》的有关文字,感到“近来思想界昏谬的奇特,真是出人意表”。并说:“见了这些糊涂东西,心里的难受也决不下于你。”不过,他“有点爱惜子弹”,认为“这种膏肓之病,不是几篇小品文字能医的”。他告诉钱玄同,“将来你总会见我开炮”(胡适:《复钱玄同的信》(1925年4月12日),见《鲁迅研究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的。胡适不肯打零枪,而准备施放重炮。于是第二年他发表了《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这篇重头文章。
我们抛开胡适和他的对手们的各种具体的思想主张,而从总的思想倾向上来分析,他们是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思想路线。
章太炎、梁漱溟、张君劢、吴宓等人以及被视为新儒家的先驱人物的其他一些人,他们坚持一个根本见解,认为中国文化有自己源远流长的根基,绵延数千年的统绪,必自有其不可灭的生命力。应当首先使自己的文化传统,尤其是儒学始祖们所创立的一些最基本的精神典范立于不拔之地,在此基础上才能谈到吸收西方文化有益于我的东西。否则,在如此竞争的世界上,尽力提倡西化,就会尽弃故垒,使中国不复为中国了。胡适和他们持相反的看法。他强调,文化就是生活本身,西方文化所展示的较高的人类生活,充分说明了它的长处。中国要不甘心贫弱、落后以至灭亡,就应当首先放弃一切民族自大的心理,努力学习西方文化的长处。也只有学习西方文化的长处,才能打掉一些固有文化的惰性,使中国文化生机活跃起来。一个强调固本和弘扬传统,一个强调采新以求“再生”;一个强调“本位”,一个强调“西化”(请注意,我这里讲的两种倾向不是抱残守缺的顽固派与所谓“全盘西化”的对立)。从抽象道理上说,双方各有所本,皆能言之成理。也正因此,都不易为对方所破,所以长期以来,各是其是,各非其非,互不相服。
辩论有它的好处,可以逼使双方把各自的思想弄得明确。但也有流弊,那就是辩论的双方为了自己所强调的方面,而往往忽略了另一些方面,因而容易发生走极端和片面性的毛病,有时会讲出一些激烈的过头话。平心地说,这两种思想倾向代表了解决民族文化危机的两种路向,双方都对现状不满,都企图重新振兴中国文化。但所选择的路向不同,下手的方法不同。这两种思想路向的背后,深藏着一个相当难解的矛盾。
我们知道,近代中国的文化复兴问题,是紧紧地与救国图强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要救国,要图强,建立民族自信心是绝对必要的。强调西化的人,极力要人相信西方文化的优胜,要人相信中国固有文化几乎处处不如人。这在普通人那里,确有损及民族自信心的可能。所以有些并非顽固守旧的人,特别关注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以增强民族自信心。但从另一个方面看,这样着力强调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也确会滋长类似顽固派那种故步自封、妄自夸大的心理,使民族自信心不是建立在真实可靠的基础上。这确实是一个在实践上难以恰当地加以解决的矛盾。正因有这样一个深刻的难以解决的内在矛盾,所以,中西文化的争论延续一个多世纪,甚至直到今天,仍难得到大家满意的解决。
三、理性的文化心理
在近代中国有关中西文化问题的争论中,大多数人都热衷于提出某种方案、某种图式,且都自信,如果按照他的方案、图式去办,中国就能够摆脱文化上长期的困惑,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
实则,一个民族的整体文化问题实在是一个太大太复杂的问题。古今中外,无论多么受人尊敬的人,都不可能使全民族严格按照他所设计的文化模式生活。中国的孔夫子做不到,西方的苏格拉底也做不到。某些尊孔的学者宣称,中国的文化是由孔夫子规划铸造出来的,这只是他们自欺欺人的幻想。孔夫子在世时及其身后,正是百家争鸣的时代,孔子所创立的儒学,只是诸流并进中的一个流派。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从来也没有真正成为事实。况且,提倡独尊儒术的董仲舒自己的思想就很难说是纯正的孔孟之儒。至于后世,则正如梁任公所说:“浸假而孔子变为马季长、郑康成矣,浸假而孔子变为韩昌黎、欧阳永叔矣,浸假而孔子变为程伊川、朱晦庵矣,浸假而孔子变为陆象山、王阳明矣,浸假而孔子变为纪晓岚、阮芸台矣。”(梁启超:《保教而非所以尊孔论》,见《饮冰室合集·文集》第9册,55页。)从孔、孟到纪、阮,其间中国社会不知已经变迁几许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也不知已经变迁几许了。这中间又有道家的流行和佛教的输入。我们最多只能说,在古代创立的诸家学说中,比较起来儒家思想最适合于中国社会需要,最有利于统治集团安天下的计谋。而孔子、孟子的思想,则在儒学流传的过程中比较起来最有长远的影响,如此而已。把中国文化简单地归结为儒家文化,把中国的思想归结为孔孟思想的累代遗传,是完全不合事实的。
既然一个民族的文化不可能依照某家某派或某人的设计发展,那么,在研究文化转折与变迁的问题时,特别是研究中国百余年来困惑着千千万万人的中西文化关系的问题时,人们应当着重努力的,不是去设计各种方案与图式,而是首先解决文化心态的问题。(1986年1月,笔者在上海首届中国文化国际讨论会上就着重地提出这个问题。《文汇报》对此有所报道,见《文汇报》,1986-01-10,并参见该次讨论会的论文集《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胡适在参与中、西文化的论争中所提出的主张和见解,自然也可以看成一种方案。但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关注的,是调整人们的文化心态问题。在我开头引用过的《先秦名学史》的《导言》中,他曾说到,中国人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能在这个骤看起来同我们的固有文化大不相同的新世界里感到泰然自若?一个具有光荣历史以及自己创造了灿烂文化的民族,在一个新的文化中决不会感到自在的。如果那新文化被看作是从外国输入的,并且因民族生存的外在需要而被强加于它的,那么,这种不自在是完全自然的、合理的”(胡适:《先秦名学史·导言》,7~8页。)。他认为重要的工作是找到一种基础,把西方的新文化同中国固有的文化联系起来。他一生的学术文化工作,可以说都是围绕着这个大题目进行的。他既反对“突然替换的方式”,以致引起旧文化的消亡(同上书,8页。),也反对故步自封、排斥西方文化的态度。在这个问题上,他认为必须采取充分理性的态度。“在文化改革的大事业上,理智是最重要的工具,最重要的动力。”(胡适:《答陈序经先生》,载《独立评论》,第160号,1935-07-21。)我认为,贯穿胡适的全部文化主张的中心,就是强调确立理性的文化心态。
研究胡适的学者,对胡适的文化主张是不会感到陌生的,这里没有详加叙述的必要。现在,我只想用力说明,胡适理性的文化心态有些什么主要的特征。我想,概括地说来有如下四点。
(一)开放的文化心态。中国两千多年里未曾遇到文化上真正强大的对手,一向把自己看成文明的中心,文化的唯一策源地,而把中国以外的民族都视为蛮夷。现在大门打开了,有机会看到广大的外部世界,应当放弃自我封闭的井蛙之见,去发现新的文化,吸收新的文化来丰富与提高自己民族的文化。但许多人一来未能摆脱中国中心主义的束缚,二来西方文化是伴着战争与掠夺一起跑到中国来的,人们难以从痛苦、耻辱和愤恨中完全清醒过来。所以长时间不肯正视西方文化的价值,不肯承认它的种种长处,甚至有强烈排斥的心理。而事实上,这个陌生的新文化却正依仗它的长处,在中国横冲直撞地为自己开拓园地。那些受传统文化熏陶最深的人,不免痛心疾首,往往只有靠炫耀祖宗的光荣和期待先圣的灵迹来安慰自己受伤受辱的心灵。胡适幼年秉受一点理学的怀疑精神;少年时代在“华洋杂处”的上海读书,受到严复、梁启超的启蒙影响;接着又到美国留学7年,在那里他有意识地积极参与当地的各种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这使他比任何人都能更好地兼容两种文化于一身,养成一种开放的文化心态。他明白地承认,西方文化达到了较高的发展阶段,比较彻底地摆脱了中世纪的愚昧、黑暗与落后,使人的智力、体能、道德都达到了新的水准。(参见胡适:《东西文化之比较》,此文原是胡适根据《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改写的英文稿。此处据于熙俭译文,收入《胡适》一书,台北,华欣文化事业中心,1979。)他希望中国人能虚心欢迎这个新文化,借助它的锐气打掉中国固有文化太多的暮气,在自由接触、自由琢磨的过程中,造成中西结合的新文化。(参见胡适:《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见《胡适作品集》第18册,140页。)他批评领导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人,在西方文化面前表现动摇、犹豫,力图预设一些堤防,防止因西方文化的吸入而损害中国自己的宝贵传统。这种犹疑的态度,在胡适看来,正是中国现代化迟迟不能成功的根本原因。他强调,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唯一办法是全力地、充分地接受现代的西方文化,而不必担心失去自己的优秀传统。这就是被认为首次提出“全盘西化”口号的那篇著名的英文论文的主要见解。(SeeHuShih,ConflictofCultures,inChinaChristianYearBook,1929,pp112-121.)
(二)世界主义的文化心态。古代的世界,因交通不便,各国家各民族近乎相对孤立地发展。近代世界才开始真正成为人类共同拥有的世界。到胡适生活的那个时代,差不多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已进入世界范围的相互交往之中了。尽管有很多是通过残酷的战争、掠夺、灾难和种种欺诈行为实现的。
作为人类的文化,不管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本质上都是人类为了生活而创造出来的。用胡适的话说,文化是人类应付环境的产物。而应付环境的基本手段与质料,总不过大同小异的那么几种。所以,人类的文化本质上都具有同一性。(参见胡适:《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见《胡适作品集》第8册,55页。)他批评梁漱溟的三种不同的文化路径说是由此立论的,他批评所谓西方文化是物质的、东方文化是精神的说法,也是由此立论的。一定的物质生活,一定的物质器具,是任何精神文化赖以存在的基础。(参见胡适:《东西文化之比较》。)胡适的这一见解,实在比他的对手们高出百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