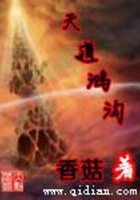原本,是抱着大不了去而复返的心情。却不想,第二日午后便有了结果。
午后,白若梨用餐后原是上街逛逛的,竟看到王家的方向升起滚滚浓烟。
本来就对王家的事上了几分心,看到这样的浓烟,免不了问上几句。
原来,王家夜里莫名其妙的着了火,好好的一座大宅子生生化为了灰烬。
没有人知道那一夜到底发生了什么,但王家的人却晦忌莫深。
王韦氏听说是受了惊吓,竟一夜间患了失心疯。
接着,又有传言说街角的赵匠人在自己家里上吊自杀了。
王家举家迁出了安庆府,说是要到京都长住,什么都没有带走,只抬走了一只破了一个口子的老旧瓷缸,那缸里开了粉嫩的荷花,像极了娇俏的少女。
听路边的商贩说,昨夜丑时失了火,王家连火都没救,王富贵只让人匆匆收拾了东西,今天天一亮就离开了。
听守城的小兵说,王韦氏这次是真真的疯了,离开的时候披头散发的,又是哭又是笑,语无伦次,哪里还有平日里的贵气风范。
听杀猪的屠户说,赵匠人当时也在,看见王家人离开,脸色很不好看,跌跌撞撞地跑回了家,他去看时人已经吊死了。
白若梨后来又拉着宸月去了一趟王家的大宅,里面烧的面目全非,处处都是断壁残垣,那些金器财宝也不知道是化了还是被带走了,她好不容易才在一堆灰烬中找到了几个没有烧变形的饕餮石雕,却发现都已经如同一般死物。
至于那个穿白色僧袍亦正亦邪的贪财法师元尘子,再也没有人见过他。
这件事虽说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但到底是不了了之,官府给出的答案也是模棱两可的,不免让有心人心思活泛。过了这么久,它非但没有被世人淡忘,反而成了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
白若梨和宸月对坐在茶楼喝茶,听着三教九流的人们高谈阔论。
这个说,“赵匠人与韦氏两个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却被王富贵横刀夺爱。”
那个说,“王富贵没错,是韦氏家里贪图王家的钱财卖了女儿。”
又有人说,“是韦氏和赵匠人合谋,打算害了王富贵,再谋他的家财。”
还有人开始讨伐韦氏,说,“韦氏就是个水性杨花、朝秦暮楚的女人。”
这些人说的唾沫横飞,好像都是亲眼所见似的。
左右,三人年轻时到底是怎样的,究竟是谁负了谁,旁人才不会关心。
很多时候,世人宁愿相信猜测,也不愿意去探寻真相。因为,真相往往大都不尽如人意,残酷且让人难过,而世人需要让自己无知而开心的活着。
白若梨摇头叹息,“于他们三人而言,那不过是一场往事罢了,哪里会有那么多的不堪。”
宸月接过她斟的茶,淡淡地开口,“有的时候,我更喜欢妖族,虽然他们贪婪,但绝不虚伪。”
他的声音淡淡的轻轻的,好像是在同她说话,也好像是在自言自语。
她也不和他计较,只为自己斟了杯茶,话也说的随意,“世人就是如此。”
白若梨的确随意,因这些流言于她毫不相干,她也懒得去管,说出那样的话也不过是想到了就说罢了。
宸月听她这样说,也不再出声询问。聪敏如他,自然知道她的心意。
于是,两人一时间相对无言。
白若梨抬头,无声叹气,终究是率先开了口,“玉将军来找你,可是有长安谷的什么消息?”
白若梨话不多,宸月更是惜字如金,虽说两人都受的住沉默,但两人都清楚彼此相处时间有限,自然是能多说一句话就多说一句。两人相处,她自然免不了要做先说话且多说话的那个人。
宸月目光一闪,“你想的太多了!是魔界的事。”
他那一瞬的惊慌,虽然消失的快,她却是看的清楚。
轻轻摇头,她苦笑,“若是魔界的事,你怎会不说与我听?”
白若梨又不是傻子,他虽时常对她冷嘲热讽,但她也明白他是尊重她的。如今两人是夫妻,一荣俱荣,一辱俱辱,若真是魔界出了什么事,他虽不会让她插手,但却绝对会和她商量。
“你帮不上忙!”他的声音冷硬了几分,不知怎地,竟给人一种色厉内荏的感觉。
她附上他握杯的手,“你骗不了我的,我了解你。”
“了解我什么?”
“你把我拖在这里想干什么?”
“我……我没有!”
“若真是魔界出事,魔君大人不用回去亲自处理吗?”
“事事亲历亲为,我早就累死了!”
“你是不是要说,若是这点小事都处理不好还要那些魔王何用?”
“我……”
“你是不是还要说,你手下人才济济,你无须操心?”
“本就如此!”
“下一句你就会说,你留下来不过是为了看海!我倒不知道,原来你对风景如此情有独钟。”
“慧极必伤。”
“你这是夸我聪明?那我就受了。出事的是谁?”
“你们白家这一代添了一位小姐。”
虽知他故意说了好消息,她也不点破,只笑着问道,“哪家添的?可取了名字?”
“司命长老,白若棠。”
“白若棠?”她重复了一遍,记住了她这位最小的妹妹。
宸月不再言语,低头把玩手上的茶杯。不过是普通的粗瓷茶杯,端在他手上却如同稀世的珍宝。
见他如此,她笑的越发苦涩,“说说坏消息吧,终归我是要知道的。放心,我不会冲动。”
宸月皱眉,恨不得冲过去抱着她,“你二哥出事了。”
她一副就知如此的表情,“二哥他……他可还活着?”
“人还没死,不过……废了。”宸月多少有些不忍与心疼,他知道她与这位二哥的关系一向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