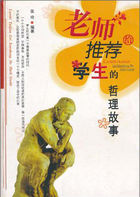秋高气爽,湛蓝的天空下,红墙朱瓦庄严肃穆。暖暖的高阳照在上阳宫内,刻意压低的气氛,在彼此之间起伏。
陆景清慢慢的抬起头,目光清澈,顺然道:“好。”不知道她是用了什么样的力气说出这句话的,她自己更不明白,为何自己的内心深处,为何总在逃避着自己的记忆。
这样的话语一出,周遭的空气瞬间清朗,陆景清更加的明白,自己如此的避讳曾经的记忆,或许不知道,更为好。这是她此刻心中的想法。
月上柳上,晚宴甚是丰盛,宁宇并没有什么心思享用,陆景清知道,一定是边疆的战事,将她困扰了。
摆手,示意宫人们撤下膳食。待膳食撤完之后,殿中只留着陆景清与宁宇,陆景清开口道:“善兵者,谋之。你不相信为你领军打仗的人?”
宁宇微微一叹,神色清明道:“何出此言。”
陆景清淡笑,“你如此的忧心,我看不仅仅是因为不放心领兵的将军,恐怕也是因为北齐国的原因,可是?”
宁宇一脸沉静,“懂我知我者,莫过你心,我的确担心的并不是我的将领不懂领兵作战,而是因为,如今的场面,曾是我亲自演变而成,我对那个人的纵容,才会如此田地。”宁宇的眸色有些许的微沉,陆景清第一次见到这样子的宁宇,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原因,让这个一直对着她笑的男子,露出这样悲戚后悔的神情,然而,再去纠结那些事情已经是枉然。
陆景清静了静心,幽幽开口道:“那么这一次,就不要再放过了。”她淡笑,浅浅的笑容,眩晕了悲涩中的宁宇,仿若星辰般,照亮了他的幽暗心底,一如当初,芙蓉花下一舞倾城般的醉人,那般的纯澈清明,直直通人心底,他断然是忘不了那个场面的,就是那一次,他似乎第一次觉得,生命,或许应该还要有别的什么,所以后来有了芙蓉王后。
宁宇也随之一笑,心中清明许多,即使如此,那又如何,他给了群起反之的机会,当然也能够再次的将他覆灭。
北齐金华殿中,宁阳一脸的笑意,心中畅然,宁宇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本王,也必定让你尝尝自己的母亲在别人的手里,被人威胁的滋味。
“来人。”金华殿中,宁阳高声道。
急步跑进来一个太监,跪在宁阳的身后,道:“王上有何吩咐。”
宁阳扬了扬手中的发丝,眼中甚是得意,道:“去,把这个快马加鞭,送到边城,让他们转送给宁宇,告诉她,孝贤太后,很是想念他呢。”
宁阳缓缓说道,一字一句,皆是他畅快的复仇快意,是他心中压抑已久的仇恨。
小太监领着宁阳手上的发丝,焦急出门。金华殿内,宁阳畅快的笑声传来,守在殿外的宫人,闻言心中微微颤抖,他们之前知道覆灭南朝的王上难以近身,而今,看着殿中的宁阳,忽然觉得,宁宇的薄怒与宁阳的阴狠相比,前者虽然曾近霸气的将太上皇逼下王位,可是后者,所有人的脑中却突然显现出一个画面,安贵人的死状。
那绝对可以用惨烈来形容了,几十个彪形大汉,齐齐的**安贵人,而王上,却是亲眼目睹了整个过程,并且要求所有的人,记住那个场面。思及此处,所有的人心中打了个机灵,定是要小心服侍王上,万万不要让自己有这样子的下场。
只是这个消息,虽然未传到清朝帝都,但是在北齐的王宫内,曾经数度被人议论,而王上并未镇压,似乎王上的意思是要更多的人,议论安贵人。若说起清朝帝都的那位不羁,那便是群臣齐齐迫他废了中宫,而他硬是以一句“本王若是不废呢?”挡回所有人的嘴,那样的为红颜倾醉,天下间,怕是只此一人,而王上,却以那样的酷吏,让一个女子受此屈辱而死。两者大相径庭。
巍峨的金黄大殿之上,众臣齐齐跪拜,道:“参见王上。”
所谓的,一朝天子一朝臣,识时务者为俊杰,为官者,大部分心中清明,断然是不会去撞枪口。
清朝的边疆,青木与叶田在帐中商议战事,忽闻得外面有人焦急来报,莫不是北齐又来犯了?
“进来。”叶田已经是几日未曾合眼,北齐的战略,几乎都不按牌理出牌,白日不战,晚上火光四起,又不见来犯,令他甚是烦心。
一小兵,急急进来,迅速呈上一物,便已经退了出去。
叶田拆开来一看,见是女子的发丝,不以为然道:“这四殿下究竟弄的什么名堂?”叶田甚是不解,如今的宁阳的已经在北齐登基称王,按理,他应该称一声北齐王,但是他愣是改不来口。
青木接过来一看,眉中一紧,似乎是想到了什么,急忙对着外面道:“来人。”看着他如此着急的模样,叶田一脸的不解。他刚想要开口问他,帐中便进来刚刚的那个小兵,青木一脸的谨慎。
“送来此物的人,可还在?”青木焦急的问道。迫切得到答案。
小兵眼见他如此神色,这当中必然是大事,不敢怠慢,答道:“小的,命人暂时扣押着,此刻人还在营中……”
不等他说完,青木急急道:“快带进来。”
不一会儿,一个满脸奔波,略选疲劳的将士被带了进来,被为首的士兵踢中膝盖,双膝跪在地上。
“这是何人的发丝。”青木本是书生般秀气的脸庞,此刻却是盛怒。
来人,不屑一顾,丝毫不以为然,口中喃喃道:“孝贤太后娘娘的,王上说了,快马加鞭,送给清朝帝都的皇帝。”
闻得此言,青木脸色一白,叶田也是如此,刑法中有之,割发代首,宁阳此举,并不是其中之意,而是另有深意。
清朝帝都,昭阳殿内,宁宇一脸的愤然,手中握着来人刚刚呈上的一束发丝,心中微痛,宁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他当做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