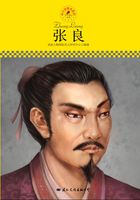家世述——父亲梁巨川殉清自杀——中西小学堂——八国联军进北京记忆点滴——启蒙学堂与《启蒙画报》——彭翼仲与《京话日报》、《中华报》——考进顺天中学堂
问:听说梁先生的父亲梁巨川先生在辛亥革命后抱定以身殉清的宗旨,自杀而死,当时在社会上引起反响。您能不能谈谈这件事的始末?
答:我父亲名济,字巨川,应顺天乡试中举人,始在清王朝任内阁中书,后任内阁侍读。这里我想先扼要讲一讲我的家世,然后说说我父亲的为人和家教,最后再谈他殉清自杀的始末。我家祖先与元朝皇帝同宗室,姓“也先帖木耳”,蒙古族。元亡,末代皇帝顺帝偕皇室亲属逃回北方即现在的蒙古,而我们这一家没有走,留在河南汝阳,地属大梁(开封),故改汉姓梁。至第十九代梁由河南迁广西桂林居住。梁的儿子即我的曾祖父梁宝书,应乡试中举人后,又进京会试中进士,历任直隶、正定等地知县和遵化知州,此后全家便在北京住下,没有再回桂林。我的祖父梁承光在北京即顺天府应乡试中举人,后在山西离石县(当时叫永宁州)做官。我父亲走的也是这条路,只不过没有做地方官吏,而在内阁任职,官衔从七品做到四品,并不是什么大官。我的外祖父也是进士出身而做官的。祖母、母亲都能诗文。所以说我出身仕宦之家,也算是书香门第,是不错的。我父亲的自杀,是离不开我家几代在清王朝做官这个背景的。
说到种族血统,自元亡以后经过明清两代,历时五百余年,不但旁人早不晓得我们是蒙古族,即自家人如不是有家谱记载,也无从知道了。但几百年来与汉族通婚,不断融合两种不同的血统,自然是具有中间性的气质的。再说我家由中国北方而南方,又由南方而北方,我祖母、母亲系统亦如此,其后代亦难免兼有南北方人的两种素质和禀赋,亦赋有一种中间性的。我所分析的这种中间性,至少与父亲和我这两代人的气质、秉性是相关的。我父亲的自杀与这种秉性的形成也是有关的。
我父亲天资不高,但秉性笃实。他做学问没有过人的才思,做事情更不以才略见长。他心里相当精明,但很少见之于行事。他为别人最不可及之处,是意趣超俗,满腔热忱,一身侠骨,不肯随俗浮沉。因其并非天资高明的人,所以思想不超脱;因其秉性笃实而用心精细,所以遇事认真;因其具有豪情侠气,所以行为只是端正,而并不拘谨。他最看重事功,而不重视学问,古人所说“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不被其泽”的话,正好点出我父亲一副心肠。我最初的思想和做人,受父亲影响最大者,就在这里。
我有一个哥哥,两个妹妹,兄妹共四人,我排行第二。父亲对我们是宽大和慈祥的,尤其对我。儿时记忆,大哥挨父亲的打,仅有几次,被厉声训斥的事很少;而我则一次挨打的事也没有发生过。我小时候既呆笨,又执拗,应属“该打”之列,但父亲却对我绝少正言厉色的教训。父亲对我的教育,与其说是教训,毋宁说是提醒和暗示。我儿时完全没有感觉到来自严父的一种精神上的压力和威迫,他从未以端凝严肃的神气对待儿童或少年。
有这么一件印象极深的小事。大约在我八九岁时,我自己积蓄得一小串钱(用麻线贯串之铜钱),常挂在身边玩。有一天忽然不见,各处寻问,并向家人吵闹,终不可得。隔天父亲在庭前桃树枝上发现,心知是我自己遗忘。他不斥责,亦不喊我来看,却铺纸写了一段话,大意是说他有一小儿自己将钱挂在树上,却到处寻问,吵闹不休。如此糊涂,真不应该。写完后交与我看,亦不作声。我跑去一探即得,随后不禁自愧,追悔自己的举动。
这桩事很能说明父亲对我的管教方法。在我七八岁至十二三岁之间,我所受父亲的教诲,大体上有三个方面:一是听他讲戏。父亲平日喜欢看戏,常以戏中的故事、人物讲给儿女们听;孩子们也常随他去看戏,但大都似懂非懂。再是同他上街,购买日用品或办一些零碎事,借此练习经理事务,懂得社会人情。三是经常听他对我们生活和做人的告诫。例如关于清洁卫生及如何照料身体,如何尊长爱幼等事,他都极为耐心而细致地嘱告我们。到我十四岁以后,渐渐有了自己的思想见解,或发于言论,或见诸行事。父亲认为好的,便明示或暗示鼓励;不同意的,也只是让我知道他不同意而已,却从不加以干涉或制止。当我十七岁和十八九岁时,有些关系颇大而与他见解相左之事(如我加入京津同盟会,参加辛亥年革命党的活动),他仍不加干涉。就在父亲的这种不干涉之中,我自以为是,自以为非,逐渐形成独立思考的习惯,成就了我一生的自学,自进,自强。
我出生于光绪十九年即1893年农历九月九日重阳节。其时,我父亲已经三十七岁。1894年爆发了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惨败,震动了清王朝的若干有识之士,起而加紧进行维新变法。我父亲是支持维新变法的,他当时草拟的奏折,表明他主张维新,进行改良。不同于康、梁的,是他主张从教化百姓入手,由官到民,一步步进行。其大前提当然是维护清王朝统治的。他的这种维新改良的主张,反映在对儿女的教育上,便是舍弃传统的四书五经,学做八股文之类,而让我们去学ABCD,读一些传播近代新知识的书。康、梁变法失败之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运动风起云涌,以致我本人在辛亥革命前夕也放弃宪政主张,投身革命,加入了京津同盟会。
面对清王朝的覆灭,父亲是无可奈何的。他在家中曾规劝我不要参加那些激烈的革命行动,但仅仅是规劝,而并不禁止。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登台表演,北洋军阀的各类人物像走马灯似的,我父亲均不以为然。民国六年(1917年)张勋率辫子兵进京复辟,我父亲曾不具名地给张勋写信,希望他成功后实行“虚君共和”的主张。张勋是打着“忠君”旗号的,当时北京城里清王朝的大小臣民一时都从失望中振作起来。我父亲原以为张勋敢这样做,是将身家性命置之度外的。没想到事败后张勋即惶惶然躲进荷兰使馆,以保全自己的性命。我父亲对这类举动历来深恶,自此,他常流露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要以身殉道,感召后人的意向。家人只当牢骚话听听而已,谁也没有在意。
民国七年(1918年)旧历十月十日是我父亲六十寿辰,家人早半个多月就张罗着给他做寿。他在这期间,于9月21日悄悄写下《敬告世人书》,而后又写下遗书多封,家人均不知道。当时我们家居崇文门外花市,父亲为写这些遗文,避免家人觉察,住到儿女亲家彭翼仲先生家中。彭是我父亲的挚友,其时在北京主办《京话日报》,家住北京西城积水潭畔。我父亲在六十寿辰前三天的凌晨,一人出门,在积水潭投水而死。
问:当时社会上有何反响?
答:第二天《京话日报》首先刊登我父亲自杀的消息,并全文发表《敬告世人书》等遗文,随后各报纷纷转载,在社会上引起反响。对我父亲之死,大致有两类意见:一是赞扬,当时有副对联,上联是“忠于清所以忠于世”,下联是“惜吾道不敢惜吾身”,就代表了这种看法;一是批判,认为既是殉清,当然是逆潮流而动,很不足道。《新青年》杂志曾专门就我父亲之死展开讨论,陈独秀、陶孟和、李大钊、胡适等都写过文章,均持批判的态度。但亦间杂有一种看法,认为殉清不足取,但以身殉道的精神,不应全盘否定,意即“道”可以不同,献身都是共同的。
问:您自己持何种看法?
答:我也曾写了文章。我当时的想法和看法是复杂的。作为父子,他突然以这种方式死去,我首先是痛苦不已。对清王朝的灭亡和革命党的胜利,我同父亲的态度并不一致,但彼此一直相安无事。再说,我父亲主张维新,对新学持开明的态度,且为人忠厚笃实,包括他以身殉道的意念和决心,我心里也是敬佩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我赞同父亲所坚信不移并为之献出生命的那个“道”。
问:梁先生,您小时候除了家教之外,都进过一些什么学校?
答:我六岁在家开蒙读书,请了一位姓孟的先生,从《三字经》、《百家姓》入手。还未念到四书五经,赶上光绪帝变法维新,停科举,废八股,都是父亲极力赞成的。这一年是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早在光绪十年四月初六,我父亲就在日记《论读书次第缓急》中写道:“……却有一种为清流所鄙,正人所斥,洋务西学新出的名书,断不可以不看。盖天下无久而不变之局,我只求实事,不能避人讥讪也。”根据父亲的一贯主张,又宣告废止了科举八股,便让我读完《三字经》之类的启蒙课本之后,不再读四书五经了,其时又没有学校可上,便找到一本四字一句、朗朗上口的《地球韵言》的书。记不清是哪里出版的了,总之是什么欧罗巴、亚细亚、英吉利、法兰西……全书押韵,小学生念起来铿锵有声,便于记忆,这恐怕是我国最早的一本世界政治兼地理的儿童教科书了。父亲的这一做法,是当时北京同类家庭中所做不到的。
次年,我七岁。北京有了第一个“洋学堂”,即新派人物福建人陈创办的“中西小学堂”。父亲便立即把我送了进去。陈把自己住宅的前院辟为教室,收了二三十名学生,地点在宣武门棉花胡同。所谓“中西小学堂”,“中”是指读中文,“西”是指读英文ABCD。这在当时,读的人觉得新鲜,连左右邻舍的平民百姓也对这些小学生另眼相看,十分稀奇。我在这所学校读了一年多,很有味道,可惜闹义和团,八国联军进了城,学校被迫关门,我也因此休学。
问:八国联军进北京,距今已有八十六年了,能亲自耳闻目睹这一历史事件者如今已为数极少。梁先生对这一重大事件尚能记忆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