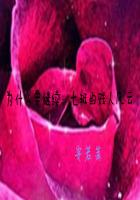脱脱的神情犹豫了一下,立就恢复了以往的神态。她是在怜悯我吗?还是想起了她自己的过往……
“你可没看到你安排的那场好戏。”脱脱戏笑道。
“他们是何时醒来发现的,早上?还是昨天晚上就闹开了?”或许是我心亏了,今早才故意赖的床。
其实我没有资格谈谁亏欠谁,是我先对他用心不良也罢,他一念之差也罢。从我们互相背叛,互相算计开始,我的身份就已经单纯是他的敌人,等到他知晓实情,定也与我势不两立。
“是啊,昨天闹得可凶了,那位天仙下凡的王嫣霞误会严木乔投靠了我们、已是禽兽败类,她想要刺杀严木乔,被我们制下,单独关在另一处了。而那位林紫燕在我的添油加醋下,恨死了那对狗男女,认为是王嫣霞假借救人的名义,勾引了她的严木乔,誓要杀了王嫣霞以泄恨。而那位一直以来清高傲慢的严大侠,也与你所料相同,他以为自己毁了王嫣霞的清白,硬是要杀了督主,然后自杀谢罪。可他一想那王嫣霞还在我们手中,就不得不乖乖就范,答应为我们办事,不仅说出了剑谱的下落,还愿意帮我们去夺取严木峰手中的地图。这还真是应了那句‘英雄难过美人关’哪。”
说完,脱脱惬意地晃了晃杯中的香茗,双目微眯,眼角流转着心事,似是在想什么,泯了口茶,润润嗓子。
“那接下来,督主是自有打算了?王嫣霞是手中的筹码,必定严加看管。让严木乔与林紫燕装作逃脱,好替督主拿到那份地图。”我向脱脱挑了挑眉。“不过,严木乔那么爽快就答应督主,督主还是应该多留份心。”
“不错嘛。不过可惜了那严木乔,亏得他还这么惦记着你。”说完,脱脱走到我的身边。
我正对着镜子,打理自己的装束。心底想询问严木乔怎么个惦记我,却终是默然,不答一语。
现在竟看不惯自己脸上的伤,便先用一块灰白色的粗布蒙住脸上,脸上的伤疤要尽数褪去应是要花上好些时日,幸好额上的伤浅些,若不细看已经看不出了。
“他问督主,你人在何处。督主骗他,已经永远也见不到你了。”
“是吗。”我淡淡应了一声,只是甫听到这消息,手中的动作明显顿了一顿。
脱脱注意到我心中的变化,却依旧自顾说着,也不知是何用意。“那家伙还伤心了一阵呢。倒是你啊,对那样的大侠、这般想着你的大哥哥,可是好没良心。”
“是啊,我已经是个没良心的了,可是这世上能有多少人值得相信?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设下那陷阱,除了尽力为督主得到剑谱和地图的下落之外,也曾想试试那严木乔的为人,可惜……”话末我黯然,不想再说下去,刚想起身,却又被脱脱按住。
“你究竟是什么丫头,这心里存的都不是一般人的心思。要说计谋,一般大人都莫及,要说性情,像是有人欠了你几世债似的。也不论我们是善是恶,一直帮忙动着坏心思。莫非,那严木乔是你前世的仇人?”
“算不上仇人,不过是近些时日我恨极了人,只消他有一丝背叛,便成了我报复的人,要怪只能怪他运气不好吧。”我紧紧看着脱脱的双眼,眼底深邃,嘴角却只是淡淡地笑道。
她听到这话,说不上开心还是不快,怏怏地离开了。
我刚想翻出手机,却又罢了手。留下照片又算什么?就像从前一样,回忆匆匆从眼前晃过,然后渐渐淡忘,总比牵挂却又无法触及来得好,不如渐渐忘掉……或作那南柯一梦,兴许心中还能好过些。
人,始终都是需要选择遗忘些什么的。
准备好要带回去的东西之后,我悄悄地离开了聚来客栈,朝着那日来时的路回去。才走出十多步,我就回过头,心想毕竟这些天来有了些羁绊,虽不能在你们面前,却也该郑重道个别。
玉连城、脱脱、严木乔,还有那些一面之缘的人们,我不过是你们生命中的插曲,一个变调的音符。趁我还没让自己犯下更错的事,回到原来的世界,试着努力地去改变自己曾经走错的轨迹,回到爸妈身边。不再一昧地去纵容别人,为难自己,然后消极、崩溃、逃避……
走出一段路,我又回了一次头。客栈就像照片那么小,就这样吧,像一幅梦中的画,渐渐消失,直到记忆也模糊。
等我翻过几个沙丘,回头时已经看不到客栈了。狠下心,断了念头,一直向着沙漠走去。但是直到身处真正的沙漠,我才发现,我根本认不出原来的那个点。只见风吹着沙丘不断移动着。
我无力地坐在地上:“天!这根本不可能,在我回去之前,就已经成了一具干尸了。”抓着一把沙子,沙子却狡猾地从指缝间滑走,“老天,为什么?为什么!告诉我,究竟怎样才能回去!”
“啊——啊——!”我歇斯底里地叫着,眼泪重重地砸落。我回不去了吗?我,再也回不去了……
突然天边传来阵阵沉闷的风沙吼声,越来越清晰。
天!这竟也能让我遇上!沙暴!
我本能地往回跑了几步,却停了下来,然后低头傻笑,自嘲着。我不知道自己是面对眼前的厄运认了命,还是此时此刻才真正认清现实。
转过身,面对远处不断逼近的“猛兽”,我的笑容愈发扭曲。
想回去?看看即便是你把自己小命都搭进去,也不知道回家的路在哪一边,多么可笑!
忽的,一股力道环着腰将我截过,天旋地转的懵劲还未过去,臀部撞着马背就是一阵生生的疼,痛得怀疑骨头都要被砸碎,几乎飙泪。
不过我还是死死抱着马背上的人,因为接下来他要带着我“逃命”。
牵引缰绳、调转马头,而后便是飞驰着远离这大漠。
玉连城不明白,自己明明是好奇跟来,想探探丫头的底细,此刻却多此一举地救下这个想寻死的。他已给了她再一次选择的机会,若她还不抓紧些,那她就活该被甩在这沙漠,死生由天。
回到客栈,玉连城下马直接回了房,脸上的阴霾却是吓退了好些人。而我刚被扶下马,未走几步路,就忍不住掉了眼泪,伴着嘴角溢出的低低笑声,心中却是笑得愈发猖狂。
脑海中突然浮现出这么一句话:笑得歇斯底里,哭得心灰意冷。
原来,一个人后知后觉竟能到这般地步。
自从那日跟他们来到这客栈,我一直潜意识告诉自己:这不过一场梦、一场游戏。可如今梦醒了,游戏也结束了,我才发现眼前依旧不是我所熟悉的那个世界。而我或许——很可能再也回不去了,没有亲人,没有挚友,没有安身立命之地。
我,孑然一身,一无所有。
一阵刺耳的鸣声过后,恍惚的我抬头便见一片苍白,天旋地转。
“怦!”
众人惊得目瞪口呆,这几日“活泼”得过分、时时处处用尽心机的小丫头,在一阵疯笑之后昏了过去。下属们碍于男女之别没有出手帮忙,直到脱脱发话:“还愣着干嘛!抬我屋里看看,可别出什么事了!”
印象中这样的昏迷是第三次了,心里完全被恐惧浸润也已经是第五次了。之前的苦肉计,他们多半是手下留情的,我虽吃了些苦头,却痛得没什么真实感,想着忍忍便可过去了,忍忍或许就在原来的世界醒了。终是因为身体底子弱,昏过去了一会儿。
再之前的一次昏迷是在大学的时候,身处异乡一场大病,恰逢元旦假期室友们都回家了。病情隐瞒了家里人,咬着牙硬是挺了过去。犹记得上一刻还攀着梯子要回床铺上,下一刻睁眼自己已经四脚朝地趴着了,一只拖鞋离了大半米远,双脚冻的刺痛,踩在冰冷的地面。看了一眼手表,估摸着昏过去了五到十分钟。翌日脸上浮现出一块青瘀,大概也是昏过去的时候撞到了什么。
若往前追溯高中的时候,那一日不冷不热的天气本该最适合长跑考试,但不擅长跑步的我依旧体力不支,拼了命也才勉强及格。上午最后一节的体育课只要考好试就能提前放学,可就在刚出校门没几步路,气息还未完全平复,身上开始冒冷汗,伴随着清晰的心跳和模糊的听力,脑中一胀,眼前的世界瞬间失去了色彩,只有一片耀目的苍白和灰黑,如同失去了立体感的平面胶卷。我慌乱又疲惫,一边想着尽快调整好自己,一边也没有停下回家的脚步。一面恐慌于感官的异常,一面又庆幸自己并非全然失明,能够看到行人和建筑的大概轮廓。即便到了家也没有立刻好转,身边母亲的话遥远的好似从天边传来,我心中嘀咕着:妈,先别说了,反正我也听不清,等我调整好……等我调整好……终于在大约一刻钟后,我恢复了正常的感官。
再向前追溯是初中一个冬天的傍晚,我和同学一起骑自行车回家。一辆摩托车后面横着的货物带了一下我的把手,瞬间我控制不了自行车的方向,然后重重地摔了。被摔懵了的我依稀记得摩托车主回来问了我“没事吧”、“在赶路”、“很急”就离开了。前后的同学停下来询问我的伤势,我勉强笑着说“没事没事”,把磨破了大半的手掌悄悄藏在宽大的袖子里。回到家我一声不吭到卫生间用冰冷的自来水冲洗手掌上的污垢和血,悄悄拿了缝衣针剔出嵌在肉里的一颗颗细小石子。上一刻还自嘲着这双手似乎并非长在自己身上,下一刻钻心的痛就让我皱着眉不禁倒吸一口冷气。父母询问情况,我依旧只是轻描淡写。可刚一从卫生间里出来,眼前的一切就像破碎的玻璃,而且一块一块越发细碎,直到变得像老旧电视机里的那种雪花纹。难道轻微脑震荡?胸口仿佛有一口气堵着,双耳也是一阵胀痛,“啊——”我大叫了一声,再睁开眼的时候,世界才又一点一点地拼凑起来。
昏迷之前,我的脑海中瞬间闪过这些记忆。
现在,我似乎应该醒了。
如果说之前客栈里的“我”不过是为了应付这场突变而做的虚假伪装,那么真正的我是否更为固执、懦弱、冷情、自私……容易轻信他人,同时又天真的可以。
我昏迷了多久?沙暴过去了?看天色现在应该几近日中。
“脱脱姐,督主……”毕竟我是不告而别,不知她们是否介意,也不知玉连城是否仍对我存着疑虑。
脱脱依旧在座位上品茶,一瞬间犹豫后,还是换了话题。
“丫头,那严木乔和林紫燕已经走了,等会儿督主也要先上路了。真想不通,为什么督主会留下我来照顾你这小丫头。不过,丫头,明儿个,我们也要上路,虽然会慢些,我们也要去京城。”
“去京城?”
“是啊,丫头,去过京城吗?”
“没去过。只听说大漠和京城都多风沙,我是江南人。”
“倒是第一次听你说起家乡的事。不过,京城那儿,没风沙。”
“我们那儿……听说京城有风沙。”注意到自己想的并非真正的京城,而是从前那个世界里祖国的首都,便改了口。
脱脱看着我,听得莫名其妙,自己在京城住了那么久,怎不见风沙?之后却也没说什么,转身离开了房间。
玉连城要走了?不知为什么,我总是时不时记挂着他,之前也一样,严木乔在眼前倒没什么想法,玉连城的事却在脑子里一直转着,他的神情,他的身世,他琢磨不透的心思,他的野心……
难不成,我这颜控族的花痴病又犯了,见了美男就沦陷?
下了楼之后,我才发现,刚来时热热闹闹的聚来客栈,现在已是人去楼空。大堂里,只见客栈的掌柜和跑堂等人,我好似入了个空荡荡的梦境。
玉连城?我慌慌张张跑出大门,心底里竟又不愿相信这只是我的一场空梦。
太好了,这不是梦。
只见玉连城又像我初次见到他时那般,淡然骑在马上,因为远了些,看不清他的神情和样貌,我不自觉地走向前,才看清他正吩咐着脱脱。脱脱的身边有个两人留了下来,兴许是以防不测。
“小芸。”他看向我,我便走了过去,就站在马边,和前两次一样。
他突然从马上跨下来,宽厚有力的手掌搭在我的肩头。之前他带我回客栈的时候似乎在生气,可现在他的表情平静无风。
我仿佛是听到了久违的称呼,眼眶有些湿润、有些发烫,可明明之前严木乔也这么称呼过我。是因为感激今日他出手救了我?还是源于心动?
出乎他的意料,我猛地给了他一个熊抱,却不敢太过分,最终只是调皮而又真诚地说了一句:“督主,一路顺风,京城见。”看到众人震惊的表情,我的脸刷的红了,一转身,迅速地奔回客栈。
啊——!一时冲动!虽然别人只当我是个孩子向督主撒娇。但同为女子的脱脱,眼睛可是雪亮的。脱脱回来后,会不会说,我吃她家督主的豆腐!啊——
我不敢从门口探出头去看,脱脱会不会在看我笑话?等我终于有勇气探出头,玉连城一行人已经浩浩荡荡地走出了好一段路,看着脱脱即将回来,我脑筋一转,打算从后门溜出去。走之前,我嘱咐了掌柜的一声:“告诉脱脱姐,我就在这附近,去挖些仙人掌和芦荟带走。呃,等会再派个人来帮我。午饭给我送到房里就可以了。”
我突然又想着该用什么来装那些扎手的小东西,看着小二放在一边的空食盒,我灵机一动,便要走了食盒和一把小匕首,抱着东西飞也似地逃了。
大漠边某处总会有一大片一大片的仙人掌、仙人球和芦荟,大小不一且又参差不齐地分布着。我勉强挖了些约莫十公分高的小家伙们,小心翼翼保留它们的根茎,打算把它们养在京城里。
想当初在异乡日复一日的工作之余,全靠着小家伙们带走我的负面情绪。看着食盒里满满当当地排了几十株,我心里美滋滋的,像是得了什么了不得的宝贝。
我还在贪心地往食盒里添更多的苗儿时,脱脱派来的人已经到了。
海风疑惑地看着,只见小丫头拿着匕首在地里戳啊戳,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埋什么。
“小姐,你在干什么啊?”
“弄些苗,这些可是好东西,以后到了京城可就没这些了。”古代不比现代,现代若是想要什么,某宝随时买来便是,可在古代,“地域性”强得很!
我回过头,发现这位就是我还在严木乔身边时,一借口上茅房,就跟着我带我去密室里商量事情的那位。不过每次商谈,他都是安分地守在门外。估计,他还不知道我干的那些好事吧。玉连城是担心我怕生,才故意给我安排的这家伙吗?
“可这都只是些杂草啊。”海风心中想,眼前的丫头果然只是个小孩子,喜欢整这些野花野草的。
“什么杂草!你知道它们的名字么?这是仙人掌,这是仙人球,这是芦荟。虽说都是些普货,可好歹也是人见人爱的肉肉们啊!”我毫不吝啬地为眼前的“草盲”普及知识。
“名字倒是好名字。可小人想不知道这些,也不需要知道这些。”他说的理所当然。
“知识面前人人平等,真没上进心。那,”我点着这些小家伙,一一说出它们的功效,“仙人掌、仙人球的刺可以用来捉弄人,芦荟的叶肉加工后可食用,也可外敷,美容养颜。”
不能说我肤浅,也不管它们的药用价值,起码我是真的只想这么用它们。
刺人的?吃的?美容养颜?海风心想:呵,这果然只是个小孩子,还是个女孩子!
“还有一点,它们耐旱、生命力顽强,可以给人们的心灵以寄托。”我一直眼馋那几株大芦荟,想着自己兴许是对牛弹琴,两人的思维根本不在一个频道,“你跟我来。”
“呃,请问该如何称呼?”我刚想唤他帮忙,却想起还不知道他的名字。
海风虽然不服被一个小丫头支使,也不知小丫头的身世如何,可毕竟是督主的客人:“小人叫海风,大家都称呼我小风。”
“海风?是因为生在海边吗?”
“不是,是因为家父姓海,母亲生我时又起了大风,才取名海风的。小人是京城人士。”
我一脸“哦,是这样啊”的表情。
“今年贵庚?”
小丫头问得这般仔细,海风倒有些不好意思了,除了西厂里的同僚们,鲜少有外人在乎过他的私事。“小人今年二九。”
二九?才十八啊,比我小。难怪和其他下属相比,他的举止看起来还是显得稚嫩些。只是在这冷兵器时代,风沙是最能“磨砺”人的。
“小风,帮我把这棵芦荟最外面最大的几片叶子掰下来,还有那、那、那,那几株。”
“是。”小风惟命是从。
噗噗,指使人的感觉真挺不错啊,万恶的封建社会。
小风英勇地为我代劳之后,又不辞辛苦地充当搬运工,或抱着或捧着那些芦荟叶片。我拎着沉沉的食盒,要多开心有多开心,总算是扫去了之前的阴郁心情。
与其在这世界愁苦度日,不如寻些乐趣,让自己活得更开心自在些。
“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不拍风雨不怕……啦啦啦,啦啦啦……”我开始毫不避讳地“发起疯”来。
“小姐,你在唱什么啊?”
“我家乡的童谣。”
“……劳动最光荣……”
小姐,果然还是个小丫头。
回到客栈,脱脱果然拉下了一张脸:“都过了用饭的时间,你这一晌午上哪去了!”看到随后而来的海风,和那满满一抱的芦荟,“丫头,你又有什么鬼主意啊?”
“嘿嘿,好吃的,和好用的。”于是我乐颠乐颠地上了楼,“小风,跟上来,把这些放到我房里。”
海风看了一眼脱脱。天!小姐,你怎么在脱脱大人面前也这么叫我啊,叫我名字就行了啊。感受到脱脱投过来问询的目光,海风不敢再看,低着头跟上了楼。
突然脱脱叫道:“丫头,刚刚督主临行前……”
我像是狐狸被踩到尾巴一般,迅速合上门,耳不听为净。冲动是魔鬼,代价相当的大啊!
等我把饭吃好,午时已经过了。我本着把食物以秋风扫落叶的速度解决,然后继续整蛊我的芦荟和盆栽。我把食盒打开,好让里面的小家伙们透透气,顺便在根部洒了些水,就不再管它们了。刚想把芦荟叶里晶莹剔透的肉给剔出来,发现还没找到容器,便向门外唤道:“小风,给我拿个坛子来,我要装芦荟。”
刚刚打发他也先去吃饭了,我不是那种封建主子,剥夺他人自由的事我没兴趣。
谁知上来的是脱脱:“丫头,你好没良心,你忘了,你早给我出的馊主意,把那些酒坛子都给砸了。真是可怜了我那几十坛好酒。”
“你以为唬小孩子哪?那天你找到剑谱来见我时,我闻到你身上的酒味全在你袖子上。而且砸酒坛,免不了湿的是鞋,而你湿的就只有袖子。再说了,就算砸了那些酒坛,我不信这么一家客栈里就再也找不出一个坛子。”
“说你是丫头,又没个丫头的样,说你不是丫头,又做这些小孩子家家做的事。那,你要的坛子。”于是她从门后取出一个小坛子,入了房内,“丫头,你究竟在做些什么呢?”
“好宝贝。”我故作神秘,捧过酒坛闻了闻,幸好酒味很淡,应该是空置了好些时日的,问道,“干净的吧?”
“放心,海风说了你是要放吃的,我特意找了个干净的。倒是好奇,你这宝贝吃食究竟是不是像你说的那样,美容养颜?”
将坛子放在桌上,我对脱脱挑挑眉:“哦,原来是冲着这来的。莫说这是野草,在我们那儿,用这做的吃的、用的都好卖得很,纯天然。”我扫了房子一眼,“不过,在这里,没有工业化,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纯天然。”
“也别说什么纯天然不纯天然了,你倒是打算怎么用它?”见我自顾自就坐了下来,也没个礼数请她先坐,脱脱自顾也找了个位子坐下。
“这是芦荟,用的就是它的叶肉,因为卖得好,我们那儿就专门种着来卖。可以把它整片叶肉都磨成汁,虽然有点粘,但涂在脸上清凉凉的,对皮肤好,身上也可以用。或者把它的叶肉剥出来,切成粒,腌渍加工一下,就可以吃了,因为可以清热排毒,故而有美容养颜的效用。”我边讲边切芦荟叶。
脱脱见了芦荟那晶莹的叶肉,煞是喜爱:“丫头,做成之后,能否也分我些?”
我心眼打了个转,应道:“好,承蒙脱脱姐这段时间的照顾,丫头给您些孝敬也是应该的。只是希望脱脱姐别再用那件事来打趣我了。”
脱脱看在我这么听话,也乐意分她些成果,就松了口:“好,说定了。”于是她便离开,为明日的启程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