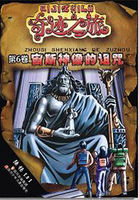“不错。”石越把心里的想法全部说出来后,竟连信心也奇妙的增加了,“自古以来,如若国家财用不足,又不想加税,往往便会卖官卖爵,百姓拿着钱和米,便可以买到官位、爵位。此法固不足取,然其之所以常常实施,却也是因为当国家财用不足之时,富民却颇有余财。所谓卖官,究其实质,卖的其实是未来的税收。只不过国家不肯担加税的名声,这‘税收’是由那些买官者通过刮地皮来收取罢了。这等行径,最是虚伪恶劣,相较而言,国家财用不足时,向富民立契据借钱,规定担保之物、利息,到期偿还,窃以为更为光明磊落……不瞒相公,自张商英上钱庄兼并之策后,我才真正知道,当今之富室巨贾究竟多有钱。只须方法得当,向彼辈借一万万贯缗钱,绝非异想天开。”
司马光听得入神,但他却绝不相信商人们会把钱借给官府——既使是司马光也知道借钱容易讨债难,更何况还是借给官府,更何况要借的,将是总额高达一万万贯的巨款。司马光的心里,对官府的信用,也是心知肚明。
他忍不住摇了摇头,道:“子明所言虽然有理,却只恐商贾断不会借钱给朝廷,何况是如此巨款。”
“原本我也担心借不到。但相公请看这个,这乃是曾、蔡、李三人给我写的信。”他一面说着,一面从袖中抽三封信笺来,递给司马光。
司马光打开信来,仔细读去,原来三人信中之意,竟都大同小异。都是力劝石越向南海海商、东南巨商举债,以渡此难关。三人在信中,举出许多例子,说明东南、南海的巨贾是如何富裕,而此次交钞、钱庄的双重危机,对东南、南海的巨贾们影响最大,他们对此亦最为敏感,若朝廷有合适之方法来应对,这些巨贾们定会支持。而三人都认为,目前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国库没钱;故成败之关键,便在于借重执政三公的声誉,由朝廷向商人们借钱。在蔡京的信中,甚至还进一步提出了具体的方法,他自称受到秦观与高丽在杭州谈判之启发,想出此策——即朝廷向商人借钱,约定之还款时间、还款利息,可以各不相同,如此安排合理,便可以减轻未来朝廷之还款压力……
石越知道司马光对于这种事情,定然非常谨慎,又道:“对商贾来说,此番名是帮朝廷渡此难关,其实亦是自保。何况据我所知,南海海商还有求于朝廷。只须朝廷妥善行事,钱一定是借得到的。”
司马光却并没有急着表态,只是将信折好,还给石越,沉默了一会,才简单的问道:“如此子明想以何物为担保?”
“盐税与盐场租金。罢榷盐之后,朝廷每岁在盐税、场租上之收入,可达一千万贯,且这个数目还在增长。每年便用这笔收入来还债。虽说如此一来,以后十年,每年朝廷之税收便要少一千万贯,但这亦只好另想他法。”
改革盐政后,食盐产量大增,食盐需求更加旺盛,这是有目更睹的。这亦是蔡京最大的功绩。若单从每年在食盐上一千万贯的账面收入来看,熙宁初年榷盐的平均收入,都在每年一千二百万贯左右,这笔收入较榷盐要少。但是,虽说食盐是一本万利的买卖,但这中间官府要为此付出的各种成本开支,却也不容忽视,即使工艺最简单的畦盐法,生产周期便要超过半年。这样折算下来,反倒是通商法的收入更多。
实行榷盐法时,尽管熙宁初年全国食盐总产量较之过去增产了百分之五十,最高曾经达到三万六千四百五十万宋斤,但却仍然不能满足国内食盐需求,官盐每宋斤要卖到四十多文,有些地区甚至贵达四十七文,不仅缺斤少两,质量亦极差。而贩卖私盐不仅质量好,而且每宋斤才卖到二十文,有时甚至一宋斤半才卖到二十文,是以虽有严刑峻法,亦无法禁绝。而改革盐政后,虽然官府的盐税、场租成本,每斤高者二十文,低者亦要十文、十五文,但盐场主通过各种方法控制成本,竭力提高技术,增加产量,盐价在各地亦低至二十五文至三十五文,食盐质量远远比过往的官盐要好,甚至还出现了各种精加工的精细盐,大大挤压了私盐贩子的生存空间。而食盐产量在几年之内,更是迅速暴增,全国每岁产盐超过六万万宋斤。
更让人吃惊的是,宋盐还成功的将便宜的契丹盐赶出了河北路,甚至还一度反攻契丹市场。在契丹境内,原本有两个天然的大盐场,不仅开采容易,而且几乎不用加工,便可食用。因此盐价极其低廉,其在宋朝河北路通行一百多年,宋朝都无可奈何——过去宋朝在全国各路都榷盐,惟独在河北路,却只能实施通商法。一百多年来,宋人根本想不到,有一天他们竟也会迫使辽主禁止宋盐入境。
这件事情在司马光的印象中最为深刻,盐税与盐场收入,不仅超过朝廷岁入的一成,而且还是一笔非常稳定、并且持续增长的税收。连司马光都相信,迟早有一日,宋盐能通行周边各国,盐税超过二千万贯,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要将这样一笔收入挪腾出来,而且时间长达十年,这令司马光十分心疼。他并非蔡京,随时都抱了个赖账的心思。在司马光心里,官府信用不佳,借不到钱是一回事,但既然借了钱,那就一定要准时归还;而既说了盐税是担保,那么朝廷就不能再挪用这笔钱。这些在司马光心里,都是天经地义的。他对商人的确抱有一些成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就会随意的欺侮商人。
“先发行五千万贯盐债,以一百贯为面额。还款期限与利息,可着太府寺商议以闻。为策万全,我还有一个想法,凡是购买两万贯盐债者,可以请朝廷赐其祖母、母三代以内亲诰命;十万贯者,可请朝廷赐其本人或三代以内亲男爵;五十万贯者,赐本人子爵。无论这命妇,或是男、子二爵,皆不受俸禄,仅为荣衔……”
“这……”司马光不由得皱起了眉头。
石越生怕他反对,不待他继续说下去,又说道:“此不过都是些虚衔,并非卖官鬻爵。如此亦不过是为投其所好。那些富商巨贾,一生最为耿耿为怀者,便是地位低下。如今买点盐债,或荣及高堂,或得封爵,亦觉体面。人好攀比,比如若有两家商贾,同在一城,家产相当,一家若买了这盐债,封了爵位,另一家不买,不免便觉低了一头。皇上常说,为政者当弃虚名而取实利。朝廷重名爵,不以之轻许人,此为正理。然今日之事,却不得不从权,只取实利。况且,费五十万贯巨款,而只得一虚名子爵,亦能使天下知真子爵之贵。”
“老夫所虑者,是惧为后世开一坏的先例。无论是借钱、封爵,在今日看来,自无不可。然奈后世何?”
“正因如此,我才望能与相公、荆公同心协力,为后世留一典范。”石越诚声道:“为政者不能不顾及天下后世,但亦不能因为担心后世,便此束手束脚,不敢为天下先。愿相公思之!”
司马光一时默然。
石越也只是默默的望着司马光,耐心等待他的回答。他并没有想过司马光马上便会给他答复。这些办法,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会留下什么样的后果。他甚至想过发行国债筹钱,但在这个时代,想要普通的老百姓购买国债,那简直便是异想天开,而且最后肯定会演化成另一种苛捐杂税。那样的方案,不仅无法说服司马光,连他自己也说服不了。但是他却知道,宋朝朝廷向商人借钱,是有“先例”的,不过这发生在另一个时空的历史上罢了。而他提出来的方案,更加完善,更加负责任,但数额也却更加庞大。所以,如果司马光最终反对,他也不会觉得意外。他已有心理准备,如若司马光能答应考虑几天再答复,便已经是巨大的成功。
然而司马光却让他惊讶了。只是考虑了一小会,司马光便抬起头,望着石越的眼睛,平静的说道:“既然此前已经议定,由子明来负责此事,那子明便放手去做罢。”
“多谢相公!”一时间,石越的眼眶都湿润了。没有人知道这段时间他承受着多大的压力,他万万没有想到,会如此容易得到司马光的支持。
司马光轻轻点了点头,端起炉上温着的酒壶,给石越和自己斟了酒,双手捧起酒杯,温声道:“国虽多难,亦能兴邦。”
“国虽多难,亦能兴邦……”石越默默念着,举起酒杯来,一饮而尽。
3.
国虽多难,亦能兴邦。
然而石越与司马光,在熙宁十八年一月二日的时候,并不知道次日会接到什么样的报告。面临着一系列可能葬送十八年励精图治的成果的危机,石越与司马光前所未有的赤诚相见。司马光许诺全力支持石越的危机政策,石越也接受了司马光全面战略收缩的建议。
为了打消司马光的疑虑,石越痛快的接受了司马光提出来的三项主张:节省朝廷开支,立即结束对西南夷的用兵,与西夏议和。后两项主张在本质上,其实也是为了节流。
石越知道,在司马光心里,解决财政问题最有效的办法,永远都是裁减一切不必要的开支。尽管司马光已经在很多地方表露出他改变的一面,但他同样明白,一些形成了很久的思维定势,几乎是不可能改变的。
无论如何都不能忘记,司马光已经六十七岁了。
他必须要尽可能的安抚司马光,以尽可能避免在将来的某一天,司马光突然出现动摇。而且,适当的战略收缩,在石越看来也是必要的。尤其是司马光主动提出接纳西夏使者,与西夏议和,更是正中石越下怀。石越取得战略优势后,并无对西夏赶尽杀绝的想法。而宋朝却在灵夏地区驻扎了太多的军队,使得军费开支一直居高不下,倘若能与西夏议和,便可以减少在灵夏地区的驻军,化兵为农,裁减西北军队数量……可以说,只有实现这一点,当年与西夏战争的目的,才算是彻底达到了。宋朝财政状况可以因此得到立竿见影的好转。
司马光提出的严禁边将生衅,减缓两北雄心勃勃的塞防工程进度,加快厢军屯田与裁汰厢军的速度等事,也是石越能够接受的。
但是司马光对益州,尤其是西南夷的态度,却让石越心里感到不舒服。
司马光一面坚持镇压陈三娘之乱,但在对西南夷的态度上,却出现了大动摇。他要求果断结束对西南夷的战争——这个主张,背弃了此前王、马、石三人达成的先取得军事胜利再体面议和、结束战争这一共识。司马光并非不明白在军事胜利后再谋求妥协是正确的,但交钞危机爆发、扩大,却还是让司马光改变了态度。
人人都知道西南用兵是目前最大的开支。
石越知道司马光素来立场鲜明的反对劳民伤财的开疆拓土。在司马光眼里,大宋现有的疆域足够大了,民众的赋税也足够重了。任何战争,除非有足够的胜算,并且有显而易见的长远好处,否则,司马光在骨子里都是反对的。如果说司马光认为“利不百,不变法”,那么在司马光看来,便是“利不万,不打仗”!
儒家自古以来就有强烈的将战争主要视为一笔经济账的倾向。甚至早在盐铁会议之前,追溯到汉武帝时期儒生第一次真正对政治发生直接影响的时代,他们就已经异常鲜明地表露出了这样的倾向。从汉武帝时代的儒生们开始,一直到魏徴,为了弥补对外战争带来的经济损失,不断有人主张将异族的俘虏变为汉人的奴隶——而在国内议题上,儒生们一千多年来,却始终都可以被视为“废奴者”。
这种刺目的矛盾或者说双重标准,格外彰显了儒生们在政治上的最基本的立足点。
真正的儒生,一定是将国内的民生问题置于最重要的位置的。
而司马光正是真正的儒生。
所以,石越能够理解司马光的心情。西南夷的问题,在司马光那里不是原则性的。在他认为必要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放弃那里,以节省大笔的开支。
甚至连一个春天他都不愿意再等。
因为这对于司马光来说,是一道轻重之别非常明显的选择题。只要结束在益州路的军费开支,就算石越真的借了两万万贯缗钱,四五年内,他也能有办法连本带利还清这笔债。那笔总额将高达两万万贯的盐债,在司马光心里,实是产生了很大的压力。
但对于石越来说,他脑子里的观念也是根深蒂固的——在司马光心中,那里可能不算是“中国本土”,而只是“化外之地”,是可以抛弃的;但在石越心中,那里毫无疑问就是“中国本土”!这道选择题对他来说,没那么容易取舍。
所以,石越不动声色的答应司马光,他将与他一道说服皇帝与两府,“尽快”结束对西南夷用兵。一定要抢在说服皇帝之前,督促王厚与慕容谦尽快出兵进剿。
当天一回到府上,石越就立刻修书一封,派人五百里加急,送往王厚、慕容谦军中。一面又筹划着要尽快与曾布等人商议发行“盐债”的细节。
然而,一月三日从辽国传回来的急报,却给了石越与司马光当头一击。
职方馆河北房侦知,大约从去年十二月十日起,辽军开始大规模的向西京道与南京道集结!职方馆的细作更言之凿凿的说,辽军还在南京道集结了十门以上的火炮!而种建中调阅陕西房的情报后,赫然发现辽国名将耶律信在熙宁十七年十一月,已经离开河套,前往大同府。更往前,陕西房的细作还侦知,熙宁十七年秉常征高昌之役中,军中竟有辽使随行。
种种迹象显示,辽国将有大规模的用兵,而兵力集结于南京、西京两道,目标所指,不言自明!
雪上加霜的是,就在一月三日这天,宫中又传来坏消息,皇帝一度出现昏迷。
两府宰执们聚集在禁中政事堂内,新年才刚刚过了三天,但宰执们都已经感觉到,最寒冷的日子终于到了。
“此事暂时不能公开。”司马光并不是在和众人商量,而更象是在颁布命令,“先选一批可靠的使者,昼夜兼程,前往两北各镇,令诸守牧将帅暗中加以戒备。禁军立即以演习的名义,取消休假!还有,派人快马去杭州,告诉秦观立即将细节谈妥,无论他用什么法子,在二月十五日之前,他必须出现在开京!”
司马光的态度,令石越大感惊讶,亦让他感到振奋。他从未想过,在关键时刻,司马光竟会有如此魄力,敢于直接向两府的宰执下达命令。要知道,在座的宰执中,还有王安石。他看了一眼王安石,发现王安石竟没有表露出任何不快之意。这不禁又让石越对王安石刮目相看。
“若有必要,我可以找个借口,亲往大名府。”石越本不愿意此时离开汴京,但如果辽国果真想要南侵,那么他就必须亲自去一趟河北,才能放心。
“暂时尚无此必要。”石越发现正在记录会议内容的李清臣忽然停下笔来,惊讶的抬头看了司马光与自己一眼,或者,李清臣原本以为能让石越出外,司马光应当会顺水推舟。
却听司马光又说道:“契丹部族分散,其若果真大举南侵,从聚集军队到出兵犯境,至少要两三个月。子明此时当留在朝中,不必如此着急去河北。郭公,此事须得劳烦足下跑一趟,去大名府巡视诸城寨修建进展,检阅河北禁军训练。”
郭逵为难的看了韩维一眼。枢密副使郭逵并不是司马光的下属,但司马光的语气,却让他一时无法拒绝,但他也不敢答应司马光。尽管他心里面或许更盼望着与辽军打一仗。
“某去河北,自是义不容辞。然此事恐还须得皇上许可……”
郭逵话音刚落,早就心怀不满的王珪已接着说道:“郭公说得不错,非止是郭公去河北,便是派使者去两北诸镇、杭州,下令禁军以演习的名义集结,这些都事关重大,若不请旨,恐不得独断。权出于上,不出于下,皇上虽抱恙,为人臣者,岂可遂此欺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