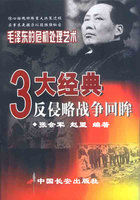我见状,只得活动活动渗出血丝的手指退到一旁,钱二爷也没多说话,目光似电的扫了一眼面前的防护网,随后伸出两根红润光泽的手指,食指与中指夹住金属网的链接条,只听得“嘣”的一声脆响,金属条应声折断。
我不由得瞪大了眼睛,视线死死盯在金属条断裂的位置,断口平整利落,这种只在影视剧里边看到的架构场景,世上竟然真有人能效仿行之。
虽说钱二爷练过内家功,但中国武术历来是杂说纷纭,为了显示本宗武术的精妙之处,其中不乏有吹捧脱离实际的元素,能真正做到如传说中的功力,既无考证也无科学依据,这种以血肉之躯斩金断铁的力道,若不是亲眼所见,又岂会相信世上有这般高人。
也就是在我愣神的功夫,钱二爷像是把玩竹签一般,与锁槽连接处的金属条依次应声折断,不到五分钟的功夫,便将防护网打开一道可供人弯腰通行的缺口。
可能是消耗的气力太过巨大,钱二爷的呼吸此时有些粗重,但脸上并无汗水渗出。
坐在角落里的沈洁然虽然没看清我们使的是什么工具,但听闻金属条折断的声音,也是察觉出了其中的蹊跷,脸上震惊之余不免透着些许恐惧。
钱二爷调整了一下呼吸,准备妥当之后,便示意即刻行动,我将手电咬在嘴里,当即从缺口爬了出去。
升降机与岩壁之间留有一道两人多宽的空隙,爬出升降机并不费劲,但此刻岩壁上异常的湿冷,伸手摸在上面,有一种透彻骨髓的寒意。
我举着手电往上看了一眼,深邃的井道一眼看不到头,头顶竟是些崩断的钢缆,摇摇晃晃的在空中轻轻摆动,像是数条细蛇在黑暗中游弋。
而在距离头顶三米多高的位置,岩壁上映着些许亮光,正是从对面岩壁中散射而出。看来之前看到的白光不是幻觉,在左侧的岩壁上果真有一道停靠的门禁。
钱二爷这时也从升降机内爬了出来,在看到上面的亮光之后,神色凝重的眯着眼睛道,“难以置信他们在这里修建了防御工事,这里距离地面至少有两千五百米,氧气和食物补给严重不足;
另外,远古的厌氧菌群在这一深度也有存活,如此极端的条件对人类的生存来说,是一项极大的挑战,难以理解这处工事的意义所在啊。”
我听闻钱二爷的感叹,脊椎骨也顿觉一阵发凉,倒不是这项工程对我的持续震撼,而是看着在头顶晃动的钢缆,再想想距离地表两千多米的垂直高度,就算我们这些人有猿猴的攀爬能力,如此长的距离,怕也是扁舟过海、望洋而兴叹。
原本指望逃到下边能够找到补给物资,这下物资没找到,却被永久性的困在了两千多米的地下,而后就算找到物资,恐怕也只能穴居地底,在幽闭的环境里悄无声息的离开这个世界。
只希望若干年后考古队也好,石油矿井钻探队也罢,能够发现我们这些人的尸骨,对这次考察事故有一个定性的评估记录,不然这他娘的比矿难事故还令人绝望。
我越想越觉得压抑,脑子里的思绪也愈加不着边际,稍一失神,一个重心不稳,差点从升降机上栽倒下去,一旁的钱二爷见状急忙将我拽住,低声问我怎么回事,这摔下去可就是有去无回了!
我头皮一紧,立马回过神来,转眼看了一眼脚下,下面深邃的幽黑不知通向哪里,用手电一照,光线就像是射进了无底洞,十多米便戛然而止。
看来,井底比我们之前预想的还要深,只是不知为何钢缆的长度只延伸到这里,而机井的深度要远大于钢缆预设的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