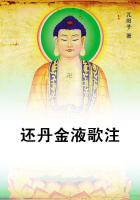我们还有很多急欲破解的悬念,为什么悬棺里的女尸外表完好,而内部却被烧坏了呢?为什么崖壁上的岩石里会浮现闪光的缠着绷带的木乃伊呢?余旭东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到底在哪儿呢?密林中偷袭并全追踪我们的黑影是什么呢?为什么埋葬吉娟的坟成了空坟呢,她的尸体究竟去了哪儿?虎纹石阵又是什么人摆成那种特殊阵形的呢?
可是,对于这一连串的问题,秦教授也不能作答了,但他认为,现在定居阆中的那个老专家吴敌,或许能够破译虎纹石阵里的字符,从而找到突破口,继而破解上述悬念中的一两个,或许可以全部破解。
我们将信将疑,但是,觉得眼下也只有先找到吴敌,寻求帮助。
告别秦教授,我们三人前往阆中。
孙友元说,我有个收藏界的朋友,叫春节老人,就是阆中的,到他那儿落脚准把我们款待得乐呵呵的。
番茄说,这个名字真怪啊,怕是在网上认识的吧?可靠吗?
孙友元说,的确是个网名,起初是在QQ的收藏群里认识的,不过,后来见过几回面,还跟他做了几笔交易,从他那儿淘了几件青花瓷器。
春节老人住在阆中古城的郎家拐街。
一见面,番茄就问,你这个名字怎么这样怪啊?有什么来历吗?
春节老人说,你们抬头看看天上的星星,这些星星中,有一颗叫“落下闳星”,是几年前,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批准,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将国际永久编号为16757的小行星命名为这个名字的。因为,落下闳是中国古代的杰出天文学家,被称为春节老人。而我们阆中正是落下闳的故乡。
孙友元大笑着嚷道,这么说,你盗用了天文学家的名字啊!
春节老人说,不是盗用,是纪念!
番茄嘟了半天嘴道,说的什么呀,我都没听明白,天文学家怎么又叫春节老人了啊?
春节老人道,因为这位伟大的天文学家落下闳创造了《太初历》,将每年的开头“元月”与每年春季的开头合在一起了,“迎接新年”就成了“迎接春天”,从而创造了春节,所以,他就叫春节老人。
番茄疑惑地说,难道古代不是在正月过年?
春节老人笑道,你以为春节自然而然就是每年的开头呀?实际上,汉代以前,中国历法的元月与春节并不一致,甚至,各个朝代的元月也不相同,夏朝用孟春的元月为正月,商朝用十二月为正月,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以十月为正月,汉朝初期仍然沿用秦历。但是,汉武帝刘彻感到如此历法太乱,就命令大臣公孙卿和司马迁组织编“新历”。司马迁从民间广纳贤才,在民间网罗天文学家,先后从全国各地招来20多人,落下闳就是其中之一。而落下闳创造的《太初历》是我国第一部完整的历法,把正月定为岁首,又定每年正月朔日为一年的第一天,冬季十二月底为岁末,并且首次在历法中制定了24节气。于是,这就把四季的顺序同人们的生活习惯、劳动习惯统一起来了,比西方早了六七百年。
孙友元说,我记得好象浑天仪就是他发明的吧?
春节老人道,是呀,落下闳创制的赤道式浑天仪是世界上第一台精密完整的观测仪器,沿用了两千多年。他的浑天说是世界最早以地球为中心的先进宇宙结构理论,并且对后世天文学家张衡、僧一行等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春节老人的客厅里,挂着一套比较夸张的汉服。
番茄走上前去仔细看了一阵道,你平时要穿这么夸张的服装?
春节老人笑道,表演时才穿!
孙友元道,表演?你会演戏?
春节老人道,刚才不是说了吗?我取这个名字就是为了纪念历史上的春节老人落下闳,每逢重要节气和传统节日,我就会穿上汉服装扮成落下闳去参加游街庆典。
我说,那你不是很忙哦?
春节老人道,前些年是有些忙,不过,自从这城里来了个怪老头,我就不那么忙了。
孙友元有些惊讶地问,怪老头?
春节老人道,是呀,这个怪老头也常常扮演春节老人,人们说他比我扮得更像,也许是他有年龄和阅历上的优势吧。因此,每每他上街做秀时,我就避开了,不跟他抢镜头,也乐得自在地休息。可是,不知他是不是心血来潮,每年总有些时候,见不到他的人影!
我问,这个怪老头叫什么名字呀?
春节老人道,叫吴敌!
我猛地伸了个懒腰,感叹道,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呀!
番茄问,可以带我们去找他吗?
春节老人点点头,带我们出门。
我们在北街找到吴家,敲开门,一位朴素的老太婆开了门,听我们说,找吴老,她就说,你们找他啊,这个疯子到千佛镇边上的构溪河去了,他一年在构溪河边住的时间占了大半。
千佛镇看起来有几分古韵,特别干净,清雅。这个川北小镇的仲秋,并不像神农架那么阴冷,天地和暖,金黄的阳光给条条青石板小街着上了盛装,迎接我们的踏访。
远远看见几只秀气的小船,在碧玉般的河面上缓缓滑行,群群白鹭优雅地玩着水上芭蕾。树林茂密,竹林层叠,三三两两的野鸭,不时从林中钻出,飞入河中嬉戏。牛羊在岸边自由自在地踱步,时不时在绿油油的草地上舔舔舌头。
沿着河岸慢走,不时有石板小径从树林里伸出来,村姑提着桶踩着石板走到河边,洗涮杂物。顽皮的鱼儿从清澈的水底窜上来,招呼我们。我们的影子,树的影子,还有构溪河那些宝贝顽童的影子,倒映在水中,一幅极其罕见的国画便流动起来了。些微的秋风中,河水泛起缕缕波纹,轻轻抚慰我们疲惫的眼睛,清洗着我们积满都市尘埃的心灵。
落霞与孤鹜齐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
我不由得吟出一句诗来。
这好象是《滕王阁序》里的句子吧,好象是王勃写的,番茄说。
我说,钢琴家,你还喜欢这些呀,记得这么熟!
“我挺喜欢诗词的,有空便会拿一本出来翻一翻。不过,我只看古体诗,基本不读新诗。”番茄折了一根芦苇在手里,边走边在空中轻轻挥舞。
我说,那你的思想也太落后了吧,为什么对新诗不感兴趣呢?
番茄说,我觉得古诗词特别的洗炼,短短几行,便包含了无穷的信息,其营造的美妙意境,若以今天的散文诗来表达,往往要数千言。加之,古诗词很讲究格律美,读起来真是一种享受。
难道你不知道,古诗词渐渐落伍,正是由于其刻意讲究形式和格律的结果呀!
当然知道。可是,我认为,那形式和格律正是考功夫的,现在一些人不能做到,便说古人迂腐。要知道,做到形式美、格律美、思想美的统一,多么不容易,可是,不少古诗词做到了这一点,从而流传千古。今天的新诗,能达到这个效果吗?
我狂笑了几声说,其实,今天也有不少诗人讲究形式美,比如,将一句话活生生地折断成几行,便成了所谓的诗,还有的,把方块字码成几何图形,也便成了诗。
殊不知,这些所谓诗人搞出来的“砖梯”、“砖窗”在唐诗宋词的“曲线美”面前是多么苍白无力!番茄气愤地把芦苇折断丢入水中。
其实,她没有听明白我的话,我也是在讥讽那些所谓不拘一格的新诗呀,不少新诗弄巧成拙,总是竭力展现韵律上的缺陷,入耳如乱石互撞,入嘴如蚕豆碜牙。这些,正是我深恶痛绝的。
番茄没有理我,几步跨到我前面,与我拉开了十多米的距离。这就到了孙友元身边。
我赶紧追上去补充道,既然是“诗”,当然要追求一点诗味,闻之有乐感,吟之有韵味,即所谓的韵律美,就像歌曲要追求旋律美一样,能唱,能听,好听。好的新诗总是应有韵律美的!
孙友元说,其实,新诗也有写得好的,若徐志摩、戴望舒的诗,美妙的意境和韵律,巧夺天工的结合,常让人陶醉,释之不能。
番茄停住脚步,看着我,笑了,温柔地挽住我的胳膊道,没想到我们对于诗词的见解如此相似。
我说,爱好不同怎么可能走到一起呢,人以类聚嘛!
番茄说,可是,事先我们都没有表露过这方面的爱好,也许这正是冥冥之中的某种安排吧!
孙友元听不下去了,抗议道,不许光天化日之下打情骂俏,再说就把你们扔到河里喂鱼!
沿着河岸走了四五里,看见几顶桔黄色的帐篷搭上河边草地上,穿得花枝招展的姑娘摆出各种造型照相,还有的干脆就躺在草地上晒太阳。几个小伙子撑着遮阳伞,像雕塑一般坐在河边,长长的钓竿垂在江面上。
我们已经在吴敌家属那里打听到了,他的帐篷是紫色的,也是成天坐在河边钓鱼,手里握着长长的钓竿,嘴里叼着10厘米长的黑色烟斗。
金色的阳光下,一个钓鱼翁的剪影扑入眼帘,那极具特色的烟斗尤为引人注目。
吴敌老师!
老者缓缓转过头来。
吴敌老师!
老者站起来,钓竿插在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