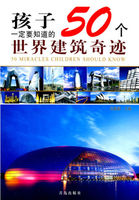教我们口语的美国老师中文名字叫赫本安,为了帮我提高语言技巧,送给了我一本美国民歌集。我自学了吉他伴奏,开始跟着“西蒙和葛芬柯”、“彼得”、“保罗”、“玛丽”等欧美乐队的演唱录音学习英文歌。当我接触到甲壳虫乐队演唱的歌曲时,觉得他们的用声方法十分特别。我还记得,第一次听到爱情歌曲是在1978年我二哥周勇刚进新华社工作不久。有一天,二哥邀我到他宿舍去听一个叫“邓丽君”的人唱的歌。以前我听到的几乎全是革命歌曲或样板戏,心想,中文歌能有什么好听的呢。二哥把一台笨重的开盘式录音机搬到他的宿舍。刚一开始放,邓丽君唱的《香港之夜》就完全令我陶醉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在这以前,我还从没有听到过用中文演唱得如此动人的爱情歌曲!
第一次见到砖形的盒式录音机时,我不懂得这种录音机如何使用。因为原先只见过那种笨重的开盘式录音机。记得有一回,一位大学同学说起“立体声”,我对这种东西是什么毫无概念,直到他让我试了一下他的随身听。那是我听过的最美妙的声音。当时,我只有一辆自行车。那时候,拥有私家车是件无法想象的事。我上大学期间,雪铁龙被引进到中国。我于是开始梦想,有一天自己也能拥有一辆汽车。当国内重新开始引进西装时,我曾兴奋地对一个朋友说:“哇,能想象得出,将来有一天我们大家都穿上西装吗?”在我看来,这样奇妙的景观简直不太可能在真实生活中出现,就好像说将来有一天,我们大家都会乘坐飞碟上下班一样。我曾在纸上信手涂鸦,画了些小人儿,个个都身着西装。我觉得,能在当时的中国长大,真是遇上了好时候。因为男士穿上西装在我看来,真的很帅。那些年里,让人感觉最赏心悦目的变化也许就是女士们已经不再穿那种色调单一、样式古板的衣服了。她们已经开始烫发、穿高跟鞋。
有一次,我和一个朋友经过东长安街上的北京饭店。这座饭店始建于20世纪初。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这里曾是举行国宴的地方,许多来访的外国领导人,包括胡志明、赫鲁晓夫和尼克松等人都曾在这里下榻。1974年饭店扩建以后,将近八十米高的饭店主楼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期,仍旧是北京城里最高的建筑。它是我们那时候看到过的最宏大、最豪华的饭店。饭店大门是自动的。当时,我还是第一次见到。那时的北京饭店一般只允许官员、外国人和与外国人有关的中方人员进人。看着那些进进出出的人,我心里想,早晚有一天,我也会自由出入这座饭店,我将拥有这样做的权利。我不明白,为什么外国人能够出入豪华饭店,而像我这样的中国人就要被挡在门外。我知道,当时能出入这里的中国人只是少数成功人士。无论是政府官员、商人还是顶级翻译,能进入这里是他们作为成功者的一个标志。我明白,这也是我今后需要努力的方向。
我一方面用心感受着新奇、愉快的大学生活,另一方面,也在努力提高自己的英语能力。为了扩大词汇量,我经常会把国外杂志上的文章翻译成中文。记得有一次,在《时代》杂志上读到一篇关于“布鲁斯兄弟”乐队成员约翰·贝鲁西之死的文章,我当时不但不熟悉“布鲁斯兄弟”是些什么人,更不能理解“药物服用过量”这个概念。这些文章涉及到的许多内容和背景同我的成长环境与人生经历迥然不同,因此,阅读时常常会有一种震撼与错愕的感觉。
父母每月给我30元生活费。大学第一年,有一次我买了一条当时很流行的牛仔喇叭裤。大哥知道后,不让我穿着它去他们学校看他。父母甚至要我把裤子扔掉,我当然不同意。最后,大家只好达成了一个折衷的方案:我只在北大校园内穿这种时尚前卫的裤子。这个插曲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那个年代新旧价值观之间的摩擦与冲突。母亲经常教育我,在学业上和人生追求上可以出类拔萃,而在日常生活中要尽量和大家伙儿一样,不要让自己太不合群儿。我那会儿比较喜欢前卫一些的衣服。我还买过一件有垫肩的条绒夹克衫,让母亲大跌眼镜。倒不是因为价格贵。其实,她总是宁愿买贵一点儿、质量好一点儿的衣服,只要服装样式不是古怪的那种。在我成长的过程中,父母总是鼓励我为人处世要低调。上大学以后,我觉得,一个人其实可以有自己的个性。
刚上大学的时候,我只是一个来自偏远郊区的乡下男孩。北大校园里都是来自全国各地最优秀的学生,包括不少各省的状元。我们班几乎每一位同学的英语都说得比我好。入学第一天,简直让我有“惊恐万状”之感。
我们男生住在北大32楼。和我分在同一宿舍的有来自北外附中的帅哥王劲(现任荷兰壳牌石油公司大中国区总法律顾问)、北京人刘潇、杭州人包凡一、温州人李毅和来自江苏江阴的俞敏洪。王劲从小学起,就在北外附小学英语。包凡一来自浙大教师家庭。他的美国英语发音在我听来,非常标准。同宿舍几个人当中,英语基础比较弱的大概只有我和俞敏洪两个人。我的英语单词发音还可以,对话能力就差了许多。俞敏洪英语发音不太好,讲英语和普通话都比较费力。我们一个来自北京远郊,一个来自江阴农村,初到北大的时候,面对这么多优秀学子,都有一种茫然无措的感觉。
入学那天中午,大家在食堂排队买饭的时候,我听到前边两位同班女同学竟然可以英语交谈,而我当时只能讲简单的英语。为了提高英语水平,我只有沿用以前练习小提琴和备战高考的方法,每天早晨五点起来读书。我会坐在楼梯上,借着楼道里的灯光,阅读从图书馆借来的英文书。开始的时候,每页都会遇到四五十个生词。我总是强迫自己逐字查阅字典,记下每一个单词的中文意思。我当时的阅读包括从狄更斯、简·奥斯汀到海明威、福克纳等不同英美作家的作品。在这个过程中,我忘记了查阅字典的枯燥,逐渐被这些作品的内容深深吸引和打动了。我从最初强迫自己查阅单词,到后来渴望掌握更多词汇,以便更自由地欣赏文学巨匠们的创作。
为了练好口语,我有时会骑车去颐和园,希望能找机会和英语地区来的外国游客交谈几句。我的一位专业老师告诉我,我说英语时还需要掌握正确的语调。我只好尽力克服自己怕羞的心理,主动去和外国人说话。我最早尝到被人拒绝的滋味就在那个时候。因为有些外国人旅行中并不愿意和生人聊天。有些人却很热情,看到有个中国年轻人愿意用英语和他们交谈,显得十分高兴。这也让我对学好口语感到更有信心。记得第一次遇到来自澳洲的游客时,我很难听懂他们说的话。我问他们是什么时候到北京的,他们回答“Today”(今天)。但是today这个词,澳洲人的发音听起来和todie(去死)是一样的。我费了好大劲,才弄明白对方的意思。那是我第一次接触来自悉尼的人。他们非常友好,很喜欢来中国旅行,对一个中国学生能上前跟他们讲英语,感到非常好奇。
第一学年结束的时候,我和如今已是北大英语系文学教授的刘锋成为班上仅有的两名全优生。我的英语专业能力,尤其是口语水平已经有了很大提高。我在各方面仍力求做到优秀,然而从内心成长而言,上大学后最大的一个变化是我在观念上的转变。我意识到,自己其实并不需要在各方面都成为第一。我需要去接触、感受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不需要在每一方面都成为第一。因为回过头来看,大学期间光有高分是毫无意义的。
从大一开始,我便广泛地参加到系里和大学各种体育和文艺活动之中。我在中学时曾经同时参加学校和县里的乒乓球队和足球队。到了北大,虽说我平时给人的印象仍然比较腼腆,可一旦玩起来,我就变成了另一个人。由于我什么都喜欢玩,而且会玩的东西很多,很快同学们就对我另眼相看了。我不仅参加足球赛、乒乓球赛、运动会和歌咏比赛,还喜欢跳交谊舞、迪斯科、弹吉他唱歌、演英文话剧。当我在系运动会上同时参加跳远、三级跳远、4×100和4×200米接力赛,并获得三级跳远第一名时,许多人看我长得并不高大,甚至有些瘦弱,根本没想到我能获得第一名。参加各种课外活动也让我结.识了许多其他年级和专业的同学,逐渐找到了一种自在的感觉。我还被选为系学生会的文体委员。我意识到,虽然有些同学比我长得帅,有些同学读书比我多,但我还是可以按自己喜欢的方式度过我的大学生活,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任何东西。
1983年,我上大一的时候,大哥得到了一次去美国深造的机会。对于刚对外开放不久的中国来说,美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典型,也是物质繁荣的象征。
起初,我非常希望做一名联合国同声传译员。1983年的一天,我在系里的布告栏上看到一则通知,一个培养文化外交官的双学位项目即将在北大开设。我从没有想过要做外交官,但外交官是一个能够代表国家走遍世界的职业。这个职业在我眼里充满着荣耀和诱惑力。这个新项目要从包括北大在内的五所北京高校选拔二十多名学生。经过口试和笔试,我很顺利地被录取了。
大哥去美国以后,我一直梦想有一天我们能在美国团聚。我十分渴望也能有机会去美国学习。这样,可以进一步提高英语水平,也能让我近距离了解美国社会。这个机会来得比我想像的还快。
就在双学位项目开始后不久,根据中美两国间达成的协议,美国迪斯尼公司将从我们这个项目和设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另一个双学位项目中挑选六名学生,到美国学习一年。这个消息让我异常兴奋。然而,要成为最终被挑选的六个人之一,并不容易。经过笔试和口试两关淘汰之后,最后阶段的候选人还要接受迪斯尼公司代表亲自面试。竞争格外激烈。当时我唯一的想法是,“我一定能去!我一定是这六个人之一!”我期望的结果又一次出现了。最后六个人的名单中果真有我!
我们将要去的不仅仅是美国,而且还是美国文化中一个颇具象征意义的地方——迪斯尼世界。我获得了一项前往美国佛罗里达州艾波卡特中心学习的奖学金,将在那里同来自其他九个国家的学生一起学习一年。我得知面试结果后思绪万千,想到我这个来自南口、至今还没有开过汽车的乡下男孩,就要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大的汽车王国了!我将亲眼看到世界流行音乐之都,看到田纳西·威廉姆斯和海明威笔下那些故事发生的地方!想到这些,我已经迫不及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