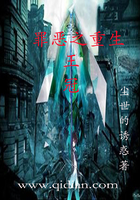自从买了车,泡夜店、喝酒、认识不同的人、更换各种男友,舒舒的生活基本处于糜烂的状态。
而在大年三十这天,喝到步伐蹒跚的舒舒第一次没在外面过夜,开门开灯看到大提琴盒子的瞬间,心里就像游乐场的跳楼机突然卡在了半空,胸闷、惊慌、手无足措。
不再有任何上台表演的机会,那么,练习那些熟烂于心的曲目又有什么必要呢!
就这么跟自己赌气着,红着眼,找了锤子把琴盒子砸烂,却心疼,放下锤子去看里面的琴变成什么样了,发现琴不在里面,又疯狂地去找,在沙发后面找到之后,拿了把剪刀把其中的一根弦给剪断,既而抱着它嚎啕大哭。
任寒舒,任寒舒,你连那些被不忠的女人都不如!那些男人虽然对她们不忠,但至少逢年过节都会准备好礼物老老实实地回家跟她们其乐融融地吃团圆饭。而你呢,只不过是那些男人消遣的玩伴!沈辰楚丢弃的玩偶!你以为你现在有了那么几百万,就能跟沈辰楚站在同一条级别线上了,你还远着呢!
长期积压的不快犹如拉开闸门的洪水般顷刻爆发,舒舒抱着断了弦的大提琴哭得咳得五脏六腑像是要呕出来。
突然一阵手机铃声响起。
哭声嘎然。
舒舒从地上爬起掏出包里的手机,愣愣地盯着屏幕上一串陌生的号码,一会儿铃声停止,没过几秒,又继续响起,没完没了,于是接起。
“怎么办,肚子好饿,陪我一起吃饭好不好?”阮缪晖的声音低沉沙哑,孩子气得请求着。
距上次见面已经两个多月,期间两人没再联系,而两个月后的第一通电话竟是希望她能陪他一起吃年夜饭。惊讶之余又有很多疑问,为什么没跟家人一起吃,为什么要叫上她,为什么不是在该吃晚饭的时间……
可是,
“好……”舒舒没多问,只是缓缓地说了个字。
*** ***
车子早已等在小区楼下
“在酒吧外面看到你了,所以我觉得你应该也没吃饭。”舒舒坐上阮缪晖的车子,他对她说的第一句话。
然后呢,舒舒想问,然后呢,看到我一个人狼狈地走出酒吧,狼狈地回家,是不是好笑到值得同情的地步了?
即使内心翻腾,但起先的发泄让舒舒失去了说话的力气。她不明白自己明明跟阮缪晖根本没什么共同的语言,甚至曾互相嘲讽,却答应跟他一起出来吃饭。
是不是因为,在大年夜,谁都不想孤独……
大年夜的街道因为寒冷显得格外萧条,几乎所有可以填饱肚子的店都打烊了,阮缪晖的车子开了很长一段路,最后在一个空旷的巷子里来回转了半个多小时后,终于在街角看到了一家咖啡店。
停好车子,两人小跑到咖啡店内,不约而同地用嘴哈气暖手,继而看着对方像孩子似的大笑。
咖啡店是老外开的,老板没有过节的想法,所以在大年夜仍然开着,店里几乎没有其他客人,点的食单很快就上了。舒舒的一盘意面、一碗浓汤、一杯“最后之吻”,而阮缪晖只是要了威士忌,不像是来吃饭的。
“为什么没回家?”阮缪晖的嘴唇触碰杯壁、微泯、吞咽,不经意地问。
“很早以前被赶出来了。”舒舒边舀浓汤边回答。
沉默
“你呢?”亦是一副不经意的语气。
“前段时间被赶出来了。”阮缪晖望向窗外。每当遇到措手不及的问题,望向远方是他唯一可以掩饰内心不安的动作。
两人有一句没一句的搭着话,谁都不想深谈。
酒至微醺,舒舒靠在藤椅上睡着了,直到零点的烟花在空中炸开,她才睁开眼,惺忪间,看到阮缪晖正望着她,单手微晃着酒杯,红着眼。
舒舒一惊,披在她肩上的西装外套滑落下来。
“对不起,我睡着了。”
“没关系。”阮缪晖莞尔。
“很迟了么?”
“刚过零点。”抬了抬手腕,瞄了一眼手表。
“走路回去?”
点头
买了单,推开咖啡店的门,雪花迎面扑来。裹紧了外套,舒舒还是连连打了几个喷嚏。
“上车吧。”
“酒后驾驶可不好。”
“只是进去坐会儿,酒热散了再走,不然容易感冒。”
“为什么不去咖啡店……”
“怎么?”打断,“怕我对你做什么?”
卡语
“他们零点打烊。”
舒舒望向店里的橱窗,灯关暗了下去。
“上车吧,外头冷。”
车内开了舒适的暖气,舒舒在副驾驶座上深感困意。
“去酒店睡吧。”阮缪晖的话在耳边轻声响起。
舒舒猛地清醒过来。
“那边有个套房,我住的。”
舒舒顺着阮缪晖的手势望向窗外,哦,中盛集团所属的酒店大厦,立在市中心的湖畔,灯火耀眼夺目。
舒舒挑眉,正要开口 ——
“有间客房。”阮缪晖哪里不知舒舒此刻要说什么,不想两人又上演嘲讽的戏码,只好抢先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