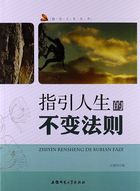花袭龙露出水面,露出水面的位置距离娄惜有六十多米远,他疲倦向娄惜招手。娄惜启动游艇,缓缓使了过来。
“有明显的标志,仁贤祠,”花袭龙一边上船,一边喘着气说,“旁边不远有县衙和一个明显的三岔口街道。”
典籍记载,仁贤祠在县衙的西边四百步远,是明朝万历年间阖邑公所建,祀故吏部郎中毛一瓒的祠堂。
娄惜查找地图上的仁贤祠及县衙,果然,县衙到花氏祖宅大概不到一公里的距离。
娄惜通过对讲机指挥小艇向东南方向,距离大艇一公里处停了下来。随后他和花袭龙驾驶大艇靠了过去。两船靠在一处后,娄惜让两个驾驶师傅驾着小艇先回了潜水俱乐部。
花袭龙整点装备再次下水,这次他的注意集中在一个碾盘上。族谱显示,那块石板,伯父离开前将它放到了碾盘上面。
湖水依然蔚蓝清澈,花袭龙的搜索并没那么容易,他像未出生的婴儿一样牵着脐带在母体的羊水中翻滚着,一家挨着一家寻找。
终于,他看到一家倒塌的房屋的院内有一个石磙模样的物体,他缓缓下潜,靠近了观察,但下面淤泥太深,只能看到圆柱体的半个脊梁。他用手一摸,突然眼前像出现了一只墨鱼,吐得周围的水质全然浑浊,沙尘暴一样四下弥漫开来。
花袭龙感觉得到,那滑滑的淤泥所覆盖的就是一个石磙。他顾不上周围的浑浊,继续下潜,他要确信一下石磙的下面是不是一个碾盘。
他的脸部和眼部因为潜得太深而被水挤压的生疼,但很庆幸,他摸到了碾盘,碾盘上的淤泥有一尺深,像棉花一样松软。他围着碾盘,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浑水中四处寻找,石磙的另一端他摸到几根弯曲的树棍,水太浑浊,一切都看不清,他觉得是树棍。
顺着树棍他向前继续摸索,突然他摸到一个圆形的物体,外形有点不规则,他抱起来,用两只手进行辨别,还没半分钟,他触电般惊恐起来,两手一扔急忙向上潜。
骷髅!那是个死人的骷髅!刚才的也不是树棍,而是肋骨!这下把花袭龙给吓毁了。
这水下是不是有鬼?
花袭龙并没忘了上升过程中要停留两分钟的安全要求,而这个要求让他丢了魂的恐慌又变成了恐惧,他恨不得能一下子窜出水面。
七八分钟之后,花袭龙露出了水面,他的脸上苍白,潜水镜取下后他看到了瞿教授和娄惜期盼的眼神。作为一个三十几岁的男人,一个历经军旅风雨的退伍老兵,面对游艇上一老一少,他突然觉得自己很鄙夷,这要是说出去恐怕只有被取笑的份。
“怎么样,找到了吗?”娄惜好奇地问。
“碾盘找到了,水弄混了,我先上来拿网,待会儿水净下来再找那块石板。”娄惜和瞿教授都很兴奋,不管怎么样,距离秘密又近了一步。很快那个隐藏已久的宗卷就要显现出踪迹了。
花袭龙没说话,他平静了一会说:“我觉得不对劲。”
“哪不对劲,怎么了?”娄惜问。
“碾盘上有一具尸体。”
“啊——”娄惜和瞿教授不约而同地惊讶起来。
“怎么会有尸体?腐尸吗?”
“不是,是一具骷髅架。”
娄惜一边点头,一边“哦”了一声。接着她说:“估计是来打捞东西死在这里的,应该是很久以前的。我怀疑是不是过去有人来过这里,说不定早就察觉到宗卷的秘密了。”
瞿教授说:“也不见得,这个人也许死了很久,也许刚死不长时间,这水下大鱼多,食肉鱼类也不少,三两个月就会被鱼类吃得只剩骨头。”
花袭龙听了毛骨悚然,那可是他刚刚用手拿起过的,但瞬间又为之担心起来,“会不会宗卷已经被盗走了?”
“那就看那块石刻还在不在,如果不在,估计宗卷的踪迹从此怕是要消失了。”瞿教授也很担心。
花袭龙的心被揪了起来,他对伯父留下来的秘密会不会丢失的担心远超过对水下这具骸骨的恐惧,他甚至急着要下水再探个究竟。
三个人一起探讨了近半小时,最后决定再下去仔细寻找一次,看那块石刻是否真的还在,如果不存在,他们就必须另觅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