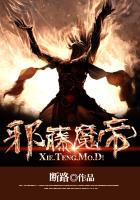小琴未能料想到她回到草荡后,遇上的第一个熟人会是慧清。当她从一辆刚刚抵达草荡镇的公交车上下来的同时,慧清也刚好从一辆红色出租车里钻出来。南方灼烈的阳光和的激烈竞争,使她越发显得黑而细长。和尚却还是原来的样子,一点儿也未显老。她叫了他一声,和尚垂着眉眼只是在喉咙底里低低地嗯了声。小琴说:“师父不认得我了么?我跟苏梅两个还到慈航寺里来找过你呢!”
“噢,苏梅。”和尚这才抬起眼皮来,目光躲躲闪闪地打量了她一眼,那声音仍然低低地,一个字一个字仿佛瓶底里的气泡慢腾腾地冒上来——“一个多月前我还在沥东镇上碰见过她,带了个孩子在买菜。”
“她孩子……多大了?”
和尚摇了摇头说:“好像说是她侄儿,我也未仔细看。”
“那她还好么?”
“老了,”和尚又睃了她一眼,“女人一过三十就比男人还老得快。不能瘦,一瘦脸上全是皱纹,可她似乎比你还要瘦得像根肋骨。”
她顿时觉得胸口仿佛被几片甘蔗叶子拉锯了一下。刚到海南的那些日子里,她曾经努力不去触动有关苏梅的所有记忆。白天,人像汽车的四个轮子一样整天为生计机械而又匆忙地奔波着,生存的巨大压力挤榨了她的思想。可是到了晚上,尤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思念的触角又会抑制不住地伸向记忆中的那部分温柔和甜蜜也是痛苦。苏梅,苏梅,她在心里一遍遍地默念着,她曾经是为这个名字离开草荡的,如今又被这个牵肠挂肚着的名字诱惑回来了,可是想见的面还是不能见,想说的话还是不能说。
“师父哪里去?”
“听说江宁村有个灵净庵来,未经佛协和宗教科的批准,是村民们擅自集资造起来的。这些非法的小庙小庵跟我们慈航寺自然是比都不能比,可奇怪的是就有不少人喜欢去那里烧香拜佛,受那些神汉巫婆们的蛊惑,倒是慈航寺这样正正规规、受国家批准保护的大寺庙香火越来越不济了!阿弥佗佛,施主们怎就不知道那些神汉和巫婆都是招摇撞骗的!”和尚说到这里便有些愤愤然,声音陡然从喉咙底里翻腾了上来——“菩萨怎么会跑到凡人身上去呢?佛法理论都是能通过科学的考验,而佛教又是为求无上的真正的平等的觉悟,不是为求得人间天上的福报。可是那些神汉巫婆根本就是为了骗钱!我今天就是特意去灵净庵查访的,要真是这样,就应马上把这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毒瘤铲除掉!”
小琴说:“我也去江宁村,正好跟师父同路。”
“施主也去灵净庵烧香?”
小琴想了想说:“回家。”
和尚便在那里站住了脚:“你也是江宁村人?知不知道有个叫骆福龙的,办了个公司倒了?”
“‘龙发’公司倒了?”她吓了一大跳,“我刚刚从南方回来,一点儿也不知道家里……”
“倒得一塌糊涂,只怕骆福龙这一辈子再也翻不了身!早两年前还威风得不得了,又上报纸,又上广播电视的。人得势时切莫太猖狂!和尚我骆福龙的苦头也是吃过的,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可出家人是不应该记仇的,这么多年来我也从未想到过要报复,可是他的报应还是来了——菩萨都是看在眼里的!”
小琴却还是不能相信。她跟二哥平时不太联系,偶尔打个电话回来,也只是匆匆地询问一下娘的身体状况,娘也从未告诉过她这事儿。“师父是从哪里听来的消息——”
和尚不以为然地说:“要是你再早回来几个月,就到哪都能听到有人说起‘龙发’公司倒闭的事。先是印染厂失了火,弄得三死一伤,接着几百户人家的集资款又都被他小舅子和姘头卷走了。银行跟信用社要抽回贷款,集资户们也逼着要还钱,几头一夹攻就挡不住了,听说整个公司都卖了还亏空上千万元呢!家里那幢楼房早已只剩个空壳子了,拿得走的东西都已被那些集资户抢得精光,连门窗都不留一个。最后赶到的一个集资户什么也没拿到,看看地上还有块破毛巾,就把它捡起来说:‘也好,拿回家去能抹抹桌子。’他一看情形不对,就早早带着老婆儿子拍拍屁股溜走了。可是多少人一辈子的血汗钱就都这么有去无回了!”
和尚又指指不远处印染厂里那两支正浓烟滚滚着的大烟囱,说:“那厂的老板现在已经是一个台湾人了,台湾人买下了‘龙发’公司后,还另外在五锄头买下了一千来亩土地。知道州报记者徐小恩么?这个台商就是徐小恩的叔父,四九年跟着他父亲逃出去的,如今又风风光光地回来了!”和尚说到这里又深深地叹息了一声——“我爹当初不跑,吃了大亏!”
她还不愿意相信和尚所说的这些。她一口气跑到二哥家里,看到却是和尚所说的一个屋壳子,连门窗也全被撬走了,只留下一个个可怕的黑洞,仿佛一张张掉光了牙齿、再也无法闭合了的嘴巴。只有一楼的几个窗洞里遮着一些塑料纸和破草席,里面住着十来个外地人,地上铺满了一溜排的稻草和破草席,男男女女混居一间,烧着蜂窝煤和煤油炉,油烟将那墙壁和天花板熏得一片污黑。
邻人们都参加了集资,看见她纷纷走了过来,顷刻便将堂前和走廊里都挤挤得满满的。他们紧紧地围住了小琴,或向她哭诉自己那笔钱的来之不易;或盘问福龙的下落;或痛哭流涕地跪在她面前哀求把本金还给他们,利息什么的都不要了,仿佛钱都在她手里;也有痛骂骆家祖宗十八代的,招来这么个野种祸害乡邻——他们正苦于找不到福龙,他妹妹的突然出现,成了众人一丝意外的希望。
越来越多的人将小琴挤得都快喘不过气来。她拼命地往外挤着,一遍又一遍使劲儿解释:“我刚从外面回来,什么都不知道——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她嗓子都快喊哑了,肩上的背包被人拉断了带子,一双皮鞋等到她挤出门外早已不像样子。她哭丧着脸,终于摆脱了那个乱糟糟的场面,惊魂未定地朝大哥家奔去,耳朵边却还老是听见那几个瘦骨伶仃的老头和老太婆的哭求声——“你要替我们跟他说说啊,跟他说说啊,要是他不把那笔钱还给我们,可让人怎么活啊?!”
她老远就闻到一股鱼腥臭,越来越多的绿头苍蝇像蜂场里的蜜蜂一样把她引向了一幢墙上斑驳着一道道跟汗渍一样青苔的两层楼房。她随即看见那走廊和道地里都是黑压压的一片,密密麻麻地摊晒着成千上万条黑鱼干,都已差不多有一筷子长了。一个脸上跟树皮一样充满了皱纹的小老头蹲在边上抽烟,手里拿着把还未扫过地的新扫帚,不时地站起身来,挥舞着驱赶那一群群喧哗而来的已经着陆或正准备着陆的绿头苍蝇。她朝那小老头看了几眼,还不敢相信,又盯了他好会儿,才敢确认真的是自己的大哥。
她叫了他一声,他好像没有听见,于是她又叫了声。等到她叫第三声的时候,他才慢慢地转过身来。
“要命呵,接连下了好几场暴雨,八个池塘一下子就有六个都让那河里墨黑的污水涌进去了!那些黑鱼都有一筷头长了,一大早我跟你两个侄儿一起去抛食时都还好好的,好几箩筐的小鱼饲下去,嘁嚓嘁嚓地一会儿就都没有了。万万没有想到傍晚过去,六个池塘上面都只见白花花地一片,汆满了死鱼。筋骨好一些的,还在往岸边撞着,一下一下地,把岸都要给撞坍了——它们是难受呀,只是不会说不会叫喊呀!”他絮絮地说着,眼里滚动着泪水,那些纵横交错的沟壑都慢慢地得到了灌溉——“要把这么多黑鱼喂养到一筷头长多么不容易呀!我跟你两个侄儿没日没夜地轮流守着这八个池塘花去的精力不说,光是饲下去的小鱼小虾就花了多少钱啊!现在还剩下两个——八个池塘的黑鱼还剩下四分之一!那些害千害万的印染厂!那些断子绝孙的化工厂!
“你二哥的公司倒掉了,他现在比我还走投无路!他春风得意的时候,我们一点儿也没有得到好处过,你知道的,他向来都是野花香,总是觉得外人好,眼里从来没有自己的同胞手足,没有我这个当哥哥、你这个当妹妹的。他宁可喜欢用外人,去相信杨志原、张千还有那个从饭店里逃出来的安徽小婊子,就从来没有想到过让自己的亲兄妹和侄儿侄女们去他公司里担任什么职务。他们剁了他的肉他还不知道,还把他们当成能割了肉换、最最要好的朋友。外面的人都说他的公司本来不会这么轻易倒的——要不是志原暗地里让银行和信用社不但封住了给他的贷款,还在紧要关头要抽回以前贷给他的那些资金,‘龙发’公司就不会倒得这么快!
“杨志原为什么要这样做?外面传来传去的说法很多:有的说他嫉妒福龙,福龙一回回地上电视和报纸,还当了市里的政协委员,可是他辛辛苦苦地爬了这么多年,还没有这么风光过,外面的人说起草荡乡来,都会说起骆福龙的名字,就不说他杨志原的;有的说你二哥不知怎么得罪了州报记者徐小恩,那女人本事通天着呢,只怕连县委书记都得罪不起,她说一声,地方上的小干部都不敢不听的;也有的说福龙收留的那个安徽小婊子还在‘皇家’饭店里时就已被马林看中了,饭店里的人知道后,跟福龙要人,福龙没给——那些当官的能那么好惹么?他们掐死你跟踩死一只蚂蚁一样容易得很。马林就指使志原给他来点儿颜色。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知道呢?可是他还把杨志原当成是好人。他也一直都把张千当成是最得意的助手,让那安徽小狐狸精给他管钱,可是这两个人早已是串通好了的。印染厂起火后,他们就趁乱卷了八百万元的集资款一走了之。他自知公司要挡不住了,眼里才重新有我这个哥,逃走前的那天晚上把娘托给了我,要我把她给接过来,还让我替他办了好几件事。他春风得意、要风得风的时候,我们可是一点儿也没有得着过他的好处——”
忽然他一跃而起,举着那把扫帚扑向一群正轰鸣着过来的绿头苍蝇,那敏捷的动作足以说明他还并未像他外表一样衰老。
就在这个阳光不太卖力的午后,刚从南方回来还风尘尘仆仆着的小琴坐在阔别几年了的大哥家门槛上,坐在那无数条散发着腥臭的黑鱼干旁,听着成龙唠唠叨叨的讲述。屋旁的直路上忽然匆匆走过三四个妇人,走在后面的急催着前面:“快些快些,菩萨就要上身了!”她这才注意到村里的布机声已经变得稀稀落落,家家户户往昔闭得紧紧的大门这回也几乎都大大地敞开着。
“轻纺业不景气了,这些人没事做,又到灵净庵去听菩萨‘开话’了。”成龙说,又回到老地方重新蹲了下来,将那扫帚柄搁在一条腿上,摸出一枝烟来,小心翼翼地去掉了还在燃着的那个烟蒂上的过滤嘴,接在那整枝的头里。可是还没有吸上一口,那烟蒂就被掉了下来,倒浪费了那枝烟头里的好些烟丝——成龙老是做这种得不偿失的事。
“你二哥的公司倒掉后,轻纺行业就一直再也没见好过,很多布厂也都跟着纷纷倒掉了,还勉强撑着的几家也是做两天放三天假,也真是奇怪,轻纺行情不景气,别的行业也都跟着倒霉,连菜场上的生意都比以前差了一半!早些年前都还有几亩承包地,现在地也没剩下多少,都差不多被征用光了。女人们没事做就整天打牌、搬弄是非吵架;男人们也打牌搓麻将,都是赌钱的。现在有了灵净庵,除了拜菩萨,也给他们弄了点儿事情做做,是是非非倒是少了不少。新造的灵净庵比以前的那个要气派好看多了,你还没看见过吧?去看看吧,你大嫂和娘今天也都在那,你大嫂今天说不定还要‘开话’呢!”
他划亮了一根火柴,又重新点燃了那枝烟,火苗子蹭地跳了起来,烧去了一小截烟丝,把他心疼得不得了。
“你大嫂现在也有观音娘娘在身上哩!”他说着这话的时候,目光透过那淡蓝色的烟雾炯炯地望着半里路外的灵净庵,脸上才有了些许欣慰之色。
无所事事的村人们在某天清晨忽被屋外一阵叽叽喳喳的叫声吵醒,随即一个个都吃惊地发现门前的水泥电线杆上蠕动着一团团粉红色的肉,再仔细一看,居然是一只只都被掉光了毛的麻雀!早先“龙发”公司倒闭、轻纺行业前所未有的不景气和得癌症的人越来越多,又接连出了几桩车祸时,村里上了年纪的人都已在议论会不会是邪气太重,又因没有把灵净庵重新修建起来,得不到菩萨的缘故?便有几个老人提出重修灵净庵,带头捐了款,家家户户也都相继慷慨地拿出钱来。兰香因为福龙的事,自觉罪孽深重,犹豫了一个晚上变卖了儿子们给她准备的那具棺材和坟基,将所卖之钱都捐了进去;张芳捋下了手上的金戒指和耳环托婆婆替她一起捐上去;白歌私底下也送来了两千块钱;就连苏北女人都极难得慷慨地拿出了一百八十块钱。
庵址仍然确定在老地方。本来要另择,但领头人之一的兰香坚持要在那里。她不止一次地想着毛狗要是地下有灵,知道他跟他娘栖身了那么多年的灵净庵就要重新修建起来了,也定会跟她一样高兴。动工那天,附近的工匠都来了,场面比谁家造房子都要热闹几倍。不到半个月时间,五间齐大的正屋和边上两间东西厢房都已结顶。
正式完工那天晚上,有人说是看见福龙出现在成龙家屋旁的那条直路上,集资户们便怀疑他躲在他兄弟家里了。一群人在成龙家屋旁守到晚上十点多,终于忍不住过去敲门,嚷嚷着要福龙出来。过了半天才见那门松动,露出苏北女人那张面盆大的圆脸,怒气冲冲地朝敲门的那个妇人骂道:“婊子,半夜三更想来勾引我老公?!”便吵骂起来。愤怒的集资户们一拥而上,将苏北女人痛痛快快地打了一顿!被打得鼻青脸肿的苏北女人于是坐在地上号啕大哭,口口声声地骂骆福龙,骂他害了她一生世!这一场哭骂后,就见她接连不断地打哈欠,目光也直了,站起身来趄趄趔趔地在屋里乱走,口里大声叱着,见谁都视若无睹。吓得成龙以为女人发了疯,赶紧上前抱住了她,哀求她回房里去睡觉,却被她扬手劈了一巴掌,又听得厉声喝道:“狂徒,我乃灵净庵观世音菩萨!”
离开那些黑鱼干和大哥,小琴向灵净庵走去。她远远瞧见庵门口似乎有许多人在进进出出地蠕动着,还隐隐约约传来一阵吵闹声。这吵闹声来源于两个卖蜡烛的小贩。他们一个是本村人,另一个来自邻村。邻村人的到来抢夺去了本村人的不少生意。本村人便以地域理由要求那人滚蛋。他们吵得非常厉害,几乎要在庵门口打起架来。一切规劝都变得无效。村人们正在生气地乱嚷嚷,忽听有人喊:“活佛来了!活佛来了!”一时百口噤声,一齐扭过头去虔诚地望着日渐老迈的桑宝根推着他那辆三轮车缓慢而来。
庵屋刚盖好时,请人定塑的菩萨还未送到,村人们便急不可待地要在这空荡荡的庵里举办第一场佛事。这日清晨,起早过来的村人看见庵门口铺了一地的破麻袋,桑宝根婴儿般蜷着身子在那里睡得十分香甜。夜里奇闷,蚊子又多如烟,村人们都难以想像这地方没有蚊香蚊帐也没有风扇也能睡得了人,却因是桑宝根,也就见怪不怪了。便用脚将这精瘦的小老头儿踢醒了,喝令他卷了那些破麻袋睡到别的地方去。
一会儿众人渐至,附近最有名的几个神汉巫婆也全都赶到了。第一个“开话”的是住在镇上的月神。半柱香过后,一连打了好几个哈欠,再懒腰一伸,“龙图菩萨”便上身了。众人端坐在两旁的竹椅上虔诚听讲。门口一黑,桑宝根也进了来,目光炯炯地径直走向“菩萨”面前的供品,一把抓起那些糕点便往口里塞。嘴里吃了不够,又端起盘子来要把那剩下的都倒进麻袋里里。边上便有人上去劈手夺下了那盘子,又将他一把拎起就要往外拖。猛听得怒喝:“大胆!竟敢冒犯活佛!”——“龙图菩萨”动了怒——“瞎了你的眼睛,这是活佛转世,你看不出来?!”
众人一时都目瞪口呆,面面相觑,那人更是被吓得面如土色。
“菩萨”语气稍稍缓和了些:“桑宝根身上有仙气啊,你们凡人的眼光是看不出来的,你们整天浑浑噩噩地梦里不知身是客,都做过些什么自己还糊里糊涂着,桑宝根却都早已看得一清二楚,只是没说,只是用装疯卖傻遮盖着站在暗里看着你们!”
一语点破,众人再细细回想,越想越觉得桑宝根果然非同寻常。村里那么多的人年纪轻轻的都得癌症死了,偏他露宿街头,寒冬酷暑身上都只披几块破麻袋爿儿,又尽捡地上的脏东西吃,反倒无病无灾。若说他那疯疯癫癫的模样,根据那些电视剧和传奇小说里获得的经验,但凡那些仙人、神人都大智若愚,往往会以乞丐、疯子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譬如《红楼梦》里的那个疯疯癫癫的跛脚道人,譬如《画皮》里那个叫化子。众人越想越紧张,懊悔过去对他多有得罪之处。
那会儿小琴眼睁睁地看着桑宝根从她面前经过,一股随之而来的浓烈的气味使她屏住了气,好会儿都不敢呼吸。麻袋的日益消失,使桑宝根身上的麻袋爿儿很长时间内都得不到替换,它们自下而上逐渐霉烂、缩短,大腿根和臀部雪白的肌肉已经若隐若现,可是再贞洁的女人也不会去计较他,不会觉得他流氓。这一身装束使村人们更加亲切地联想到济公就是这样子,这样与众不同。他们以最虔诚和敬畏的目光迎接着这位衣不遮体的活佛的到来,包括正在做道场的老先生们和念着“阿弥陀佛”的老太太们,他们都放下手里的活计站立了起来。可是他似乎只对他们恭恭敬敬奉送上来的饭菜和供品感兴趣,因为当他得到这些食物后,随即就转身离去了。但这并不有损他在村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沉默和漫不经心恰是此刻他们眼中真正仙人的品质。
他们曾经肆无忌惮地奚落过两个从慈航寺里过来化缘的小和尚,问他们现在寺里还养着多少女人,他们师父还包不包那些出租车的女司机了?还有多少施主在供着他们吃喝嫖赌?看着那两个小和尚狼狈而去,他们都开心得哈哈大笑。——慈航寺算什么?那里不就是有几个吃喝嫖赌样样都来的花和尚吗?可恶的是还口口声声地把菩萨和阿弥陀佛挂在嘴上,作出一副六根清净、道貌岸然的样子。他们的可笑也正在这里,谁都清清楚楚了,还装。村人们现在可是有了自己的庵,自己塑起来的菩萨,自己的寄托。即使没有佛事,他们也都喜欢往庵里赶。那些无所事事的日子里,每天一早起来,早饭后想着的第一件事便是到庵里去,否则那段时间将会成为一块令人难以忍受的空白。他们像过节般地隆重迎接着每一场佛事的到来,在这些佛事里每次总会有一两个巫婆或神汉出现在庵里当场“开话”,仿佛文艺晚会上的那些特邀明星,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而那些新出道的,最初也往往是从这里开始出名的。
小琴正在人群里寻找着慧清,忽然听见一个瘪嘴瘪脸的老太太大声宣布说:“菩萨开话了!”于是随着桑宝根的离去重新出现的嘈杂又得到了最有效的禁止。大殿里所有站着坐着的都被定住了姿势。她远远望见苏北女人坐在最中心的位置上,像一团剔去了骨头的肉堆放在一把竹椅上,已经闭上眼睛在开始打哈欠了,预示着一场破绽百出、拙劣的表演即将到来。她还在旁边等待着洗耳恭听的人群中找到了自己白发苍苍的母亲,母亲似乎比任何人还要虔诚地跪在已经有菩萨附在身上了的大媳妇面前,不停地磕拜着,握在手里的那几柱香升腾着一缕儿一缕儿安慰般的叹息。
她一直都没能找到慧清。
佛事快要结束时,一辆卡车从庵前的石子路上颠簸过来,上面装着满满一车死黑鱼。半个小时后,刚刚“开完话”的苏北女人坐在自家门槛上号啕大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