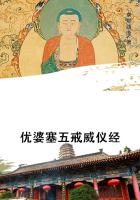断了一只凳脚的椅子勉强地用什么像是横梁一般粗壮的物体作以支撑,而椅子上被绑着一个人,而这个人却是--
他的父亲,亦国栋。
他有些难以想象这样的发展情节,他似乎都要以为自己在做梦,在风中蔓立的寒冷,还有野草时不时刮过他脸上带来的疼痛时却让他彻底清醒了一大半。之前在大厅里只是看见父亲接了个电话便匆匆离开了。
这是真的!
几个像是混混一般的人物,一个高瘦,一个矮胖,还有几个带着帽子尾随在后面,看得并不真切,那个个子最高的男子手里拿着一根棍子,不断地朝着手掌心拍了拍,痞性十足但他生涩并不熟练的动作却暴露了他并不是长干的这一行。
亦楚凡很难想象这些人竟然猖狂到了这种田地,敢在亦家的底盘亲自绑架,但他又疑惑起来,这个偏院一般人很少知道,除了老一点的家丁还有亦家的人,其他人是没有可能知道的,而这几个劫匪却似乎相当了解这亦家的地理位置,破旧的房间内虽然有足够大的空间但却昏暗,他靠着白日的光亮只能勉强地看清楚,他眯着眼睛盯着屋内的一举一动,只见那站在一旁的胖子又是摔了一只杯子,而那个像是老大一样的人物,把玩着手里的打火机,一开一关,一关一开,来往反反复复,眼神却足够挑衅危吓,“你到底拿不拿出钱来!”
亦楚凡的心里忐忑又紧张,他盯着那几个土匪,却突然发现这几个人像是父亲找来的搬运画作的工作人员,他暗暗心惊,担心歹徒会伤害父亲的性命,他掏出口袋里的手机,正要拨通一大串的数字,想想又怕惊动屋内的人,改发信息求救,可是,就在他打出几个字的同时停住了。
他的脑海里像是回放电影一般,这十几年的画面全部地跳了出来。
三岁,他进亦家,顶着私生子的名号,父亲只是拍了拍他的脸,又转过身去抱比他大一岁的却从小出生在父亲羽翼保护下的亦湛远。
五岁,他喜欢的玩具却因为亦湛远一句随意的喜欢,被父亲拿走送给了亦湛远。
七岁,他和同龄的孩子打架,他父亲给他的却是一巴掌,却连机会都不给他解释。
十二岁,他生日,父亲却因为观看亦湛远比赛而忘记。
十六岁,父亲无情送他出国,回来才知道,亦湛远已经接管亦氏旗下的企业。
……
这全部的点点滴滴,都像在无情地提醒他,他父亲的爱,只属于亦湛远,哪怕千分之一都不曾吝啬给他过。这些年来,若不是亦雯,他都不知道自己存在的意义,他痛恨他的父亲,他更痛恨自己的存在,是不是因为自己是私生子,是不是因为他不够努力,做的比亦湛远差,可是他哪里错了,他在亦国栋的眼里不过只是一颗后补的棋子,像是一块臭抹布一般,挥之则来,挥之则去。他恨他!
眼泪滴在手机的屏幕上,他像是花了极大的力气,颤抖着拇指一个一个字地删去,像是要将心底沉淀多年的委屈连同痛苦一齐抹去,他笑了笑,眼神却带着充血的恨意还有狰狞,那么一瞬,他那么希望自己的父亲可以去死!可以消失!可以不让自己的生命不再这样痛苦!
屋内昏暗无比,却能清晰地听到打火机的声音,一个戴着帽檐的男子突然站起身来,将一叠纸张摆在亦国栋的眼前,他的声音极为沉稳,“亦国栋,你可真是个伪君子,当年媒体公众都将你报道成什么为朋友两肋插刀肝胆与共,你他妈的都是个屁!”男子说得极为气愤将头上的帽子甩手一掷,又是朝着地上绌了一口唾沫,“当年A市远郊那块工程,你知道有多少人死在里面吗!哼!我们的父母都是初到城市打工的老实人,却没想到这豆腐渣的工程会要了他们的命!你在公众面前做好人,却拉了林家做替死鬼,真是个老狐狸啊!呵呵,可怜了你那位生死患难的好、朋、友啊!”
亦国栋撑大了双眼,不可置信地道,“你们在说些什么,什么林家,什么替死鬼,我为什么听不懂!”
说话的男子单手掩面,深吸了一口气,又是叉着腰,眼神朝着一旁的胖子示意了下,“反正也是死到临头了,二狗,把文件和证据给他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