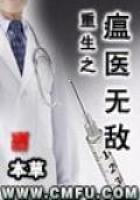每当提起农村,脑海中出现的景象多是一条巷子,几排土房,老人们追着冬日的太阳、夏天的阴凉,婆娘们三五成群扛着锄头下地干活或打着笑着干活归来,孩子们玩着自创的玩具:几块石头称为“扛”,折的纸板叫“四角板”,还有猪羊的骨头节,装着玉米粒的沙包……器具简单,但玩得不亦乐乎。汉子们忙里偷闲玩着一副破“牛九”,被老人们称为不务正业!傍晚,圈子里的猪大声地哼哼着要吃的,母亲们扯着嗓子叫孩子们吃饭,叫骂声里藏着疼爱,一巴掌打过去,不知是在解气还是在给孩子拍土……我就在这样的环境里出生成长。那时的“艰苦”不存在于孩子幼小的心灵中,一块粗粮饼子饿了吃起来分外香甜,几块过年的水果糖到现在也没有化掉甜味,妈妈锁在柜子里的苹果香至今没什么能比得上,孩子们都像树苗似地长大了,走上了人间千百条不同的道路。黄土地贫瘠,但人们的向往和追求不贫瘠,农村的日子平淡,但农村里的故事不平淡,与城市一样上演爱恨情仇,一样经历风吹雨打,一样经历沧桑巨变——愚生一家也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乡村,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为什么叫愚生,但仿佛他一直就在这个地方存在似的,时不时地会在我的视线和脑海中出现,也许因为他和别人不一样,也许因为他的可怜。总之,他是村子里的一个典型,走过了一段不寻常的人生轨迹。印象中他个子有点高,驼着点背,有时偏胖有时偏瘦,他说那是有些地方人好,有些地方人坏的原故。他爱笑,傻傻地笑,但对人并无恶意,孩子们跟在他的身后嘲笑他时,他会去追逐着佯装打人,却把自己兜儿里的糖果塞进他们手中。小时不知事,只知道从14或15岁开始,愚生每年都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在家里,爹妈早逝留下他在哥嫂家生活,哥嫂的孩子穿得总比他好,年纪很小却把他指挥得团团转,他却像疼爱亲弟妹一样对他们好,并不生气,也不反抗。渐渐地,我们这些娃娃牙牙也长大了些、懂事了些,才知道每当年后二三月份,哥哥嫂子就不愿再要愚生呆在家里了,他们塞给他一床破旧的棉被,两件烂衣裳就紧紧地关上了大门,愚生站在门外,瑟缩着央求:再暖和些,天再暖和些就走,但屋内再无应答之声。
愚生背着铺盖卷,寒风中离开了村子,谁也不知道他要上哪儿去,谁也不知道他啥时候回来。人们有同情的眼泪,却并不能挽留他不走上流浪的路。
时间一如往常,迈着不紧不慢的步子,把世界带进了春天、夏天和秋天,有人说起在天水见过愚生,有人说在兰州见过愚生,都说愚生很亲热地跟他们说话,记得村子里的每一个人,说他在车站、旅店这些地方讨钱,过得好像还不错!是吗?他又是如何熬过了一个漫长的冬天……
十一月,愚生还会回来,人们说他把自己在外面要的多少钱交给了哥哥嫂子,他们会让他在家过个年,但年一过,愚生还得被赶出家门,甚至连身上稍稍新一些的衣服也会被扒下。果然,正月十五过了没几天,愚生又被赶了出来,任凭他怎么央求,院墙内是毫无反应。村民们骂那嫂子哥哥无情,骂急了,那嫂子跳上墙头,用尖细的嗓子喊到:你们好,收你们家去,看你当爷爷供着还是当孙子疼着!人们哑然!
这样年前回,年后走,不知过了多少个年头,愚生一次回来比一次老,一次回来比一次穿得破旧,不知他在外受了多少罪,遭了多少白眼,曾给哥哥嫂子要回过多少钱。总之,在我离开村子若干年后,关于愚生的消息就越来越少了,但有人说,愚生还是对同村的人亲热有加,见到熟识的人便问这问那,别人问他过得如何时,他也总说还好还好,但眼见一年不如一年。
有一次去兰州,无意中看到过街天桥上有个乞讨人,放下两块钱刚想走,却听有人叫了一声我的小名,仔细一看,正是愚生,已是苍老邋遢得没了样子,心里一酸,不由想起了他一生的遭遇,问他过得可好,他仍说,还好还好!那双冻得发黑的手上是零零碎碎的几元钱。我掏出二十元钱,塞进他手里说:“老哥,买碗羊肉泡吃吧。”
他想站起来,可眼看不太可能,我便拍了拍他的肩,无言地走开了。那一天我的心情格外的糟!傍晚,我忍不住又到了那个天桥,想再为他做点什么,可除了一些烂果皮和两张旧报纸之外,他已不在。
又是一年春节前,我回家探亲,村里人说愚生死了,不会再回来了,有人说倒在某个水渠里,有人说就在平凉的某个街角,总之,他的模样再也不会出现在人们眼前。这个不幸的人,来到世上走一遭,受尽了磨难,悲惨地离开了这个人间,在他心里,可曾有一点留恋?在他的脑海中可曾有过幸福的时刻?真不知生命于他可有任何一点意义?想到这些,我久久不能入睡,满脑子都是儿时他追着我们塞糖的样子,还有那张傻傻的笑脸……
屋外,山村的风在呜咽,那难道是愚生长长的哀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