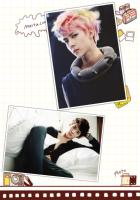宋宪民
赵玉山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调县里担任文联主席才半月时间,在工作上还没完全进入角色,就先让县委宣传部姜部长狠批了一顿。如果没有老同学这层关系,彼此感情深笃,平时又经常胡闹,脸皮厚一点儿,他都没脸出姜部长办公室的门了。
赵玉山一直在山高路远的横河乡工作,算来整三十年了。
他是既沾了玩笔杆子的光,又吃了舞文弄墨的亏。开始在横河乡林业站干临时工,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由于勤奋好学和具备这方面的天赋,竟无意中练出一手好文章。后来便往外投稿,省报市报难上,但县里的小报上却经常出现他的名字。那时乡里人才匮乏,乡领导又慧眼识才,便将赵玉山抽调到办公室干通讯报道员。赵玉山如鱼得水,在最初的几年里写了许多有分量的好新闻,为扩大乡里的知名度做出了重大贡献。尤其让赵玉山引以自豪的是,他的一篇通讯稿件竟上了《人民日报》头版头条,连县委宣传部多次进京运作没办到的事,他没费吹灰之力就变成了现实。随着名气的上升,赵玉山就不再满足于写新闻稿了,便悄悄搞起了文学创作。当初的动机是追求某种境界,让人们知道,他不仅会写新闻稿,还能创作文学作品。虽然没有成名成家,但也在各级报刊发表了一些作品,还出版了一部以乡镇干部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在全县文艺界轰动一时,尽管是自费出版。仕途上也算得上一路顺风,先是办公室主任,很快又当了副乡长副书记,继而升任乡长职务。由于追求执着,不管担任什么职务,赵玉山始终没有辍笔。但乐趣中也包含着苦恼。只要有一点儿空闲,小说中的人物就禁不住在脑海里闪动,像妖魔鬼祟缠身一样,怎么都无法摆脱。他想,自己这一生已经与文学创作结下了不解之缘,仕途看来要降到次要的位置了。
症结的根源就在这儿。以前怎么写都行,当乡长后却出了问题。尽管是业余创作,所占用的也是别人打牌下棋聊天喝酒看闲书的时间,可人们并不理解,无不在背后议论,说现在外面的世界是一日千里,当了乡长还写小说,写小说能写出“GDP”吗?能写出山区群众的小康生活水平来吗?简直是不务正业!这倒无所谓,关键是书记和县上的领导也对他有了看法。横河乡本来就是穷乡,工作一直处于被动地位,这一来自然就把责任推到了他身上。相近的看法是,横河乡的工作上不去,尽管有许多客观原因,但与赵玉山不务正业也有很大关系。该着赵玉山倒霉,岂知刚出现一线转机,又立刻消失了。
事情是这样的,年前县里调整乡镇领导班子,书记调另一个乡任职去了,上面虽然对赵玉山有看法,但总的说四平八稳,没出现大问题,相比之下能做到这一点也不容易了,再说又是穷乡僻壤,是个好汉不干赖汉干不了的地方,矬子里选将军,赵玉山很有可能接任书记职务。但就在这时,乡里却出了一个大乱子。按照县****局的要求,乡里几个****老户的问题年初就得到了圆满解决,他们还信誓旦旦地保证以后坚决不上访了。
不知什么原因,他们突然又翻了杠子,借乡里放松警觉之机,人不知鬼不觉地悄悄去了北京。接到上面的电话后,赵玉山慌了,只好亲自出马,与县****局的张局长一块进京,连哄带骗强拉硬拽,好歹将人领了回来。虽然没出现严重后果,但在最关键的时刻却给了他致命一击,也就是说,从根本上斩断了他的升迁之路。不仅升迁无望,还有可能调整到其它乡镇任职,那是最不情愿的事了。看在老同学的份上,关键时刻还是姜部长伸手拉了他一把。姜部长为他选择的单位是县文联。县文联是文艺界的主管单位,挂靠宣传部。宣传部长是县委常委,虽然没有人事权,但管辖之内的事还有一定权威。县里在年底考核各级班子时,姜部长正好到外地出发,不知问题出在哪里,县文联在一百多乡镇和部门中考了个第一名,是倒数的。按照县委县政府规定的末位淘汰制,倒数第一名的主要负责人必须调离本单位,并且降职使用。姜部长回来后面子上过不去,曾在常委会上大闹一场,但终因生米做成熟饭,便无可奈何地挥泪送别了原来的文联主席温光超。赵玉山是要好的老同学,又有这方面专长,姜部长便把空出的位子选定了赵玉山。考虑到是平级调动,还能发挥特长,又到了这把年纪,再也没有比文联更合适的地方了,而且不用请客送礼就进了县城,所以姜部长在电话里一表露,赵玉山就很痛快地应了下来。
不念哪家经,不知哪家难。赵玉山以前到县里开会,经常去县文联聊天,将文联当自己的娘家来走,看着什么都亲切,可真的过去上班后却渐渐失去了原来那种感觉。别看县文联衙门不大,只管理着区区五六个协会,但这个小小的文联主席比乡长还难干。怪不得来文联之前有人提醒他,县文联不是人干的地方,如果按那个年代分析定位,便是全县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干文联要具备两样东西:一是头上长角,见了人就拱;二是身背智囊袋,随时搞阴谋诡计。赵玉山当时没有理会,心想他们是在上纲上线,是故意吓唬人,问题不会那么严重吧?
现在看来,他的切身体会是,虽然谈不上阶级斗争,但也狗撕猫咬问题成堆,如果没有良好的心理准备,足以望而却步。
但后悔已经晚了,就像上了套的拉磨的驴,已身不由己了,挨皮鞭挨棍子都得死拉到底。再说这也是让领导改变对自己印象的最后一次机会,干不好更对不起姜部长,所以赵玉山从报到的第二天起就进入了工作状态。经过调查研究和认真思考,终于理出了几条振兴和繁荣全县文艺事业的工作思路,待进一步修改完善后,准备向姜部长作一次全面汇报。想不到还没作好思想准备,姜部长就突然找他谈话,将他弄了个措手不及。
这天早上,赵玉山上班特别早,机关是八点钟上班,还不到七点半他就来到了办公室。在横河乡干乡长时,尽管工作干得憋气,但多少还是有点权威性,多数情况下都能受到部下的尊重,起码有秘书写材料,更用不着亲自动手提开水和打扫卫生,除了书记就他大了,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土皇帝。可来到文联后情况就不同了,虽然成了一号首长,可人家却不这么认为,更没有给他多少特别的尊重,甚至将他作为刚到的“新兵”来对待。县文联挂靠宣传部,人员配备由宣传部统一安排。因编制紧张,这些年在人员的配备上,出出进进的始终保持在三人左右。因文联的业务职能与宣传部其他工作相比并不重要,或者说可有可无,所以即使这样也算大慈大悲了。赵玉山填补了文联主席的空缺后,文联依然是老少长短三个人。除他之外,再就是副主席高长水和主席助理苗青了。高长水比赵玉山小一岁,今年四十九了。高长水从省美专毕业,学的是国画专业,因美术人才奇缺,毕业时没托关系就进了县文化馆。
十年前县里组建文联时,作为重点选拔对象,就选调进了县文联,并兼任美协主席。高长水的初衷是,文联虽然没多少油水,但毕竟是县里的局级单位,凭自己的专长和能力,就是熬也能坐上主席位子。没想到自己估计错了,尽管文联主席不是要职和美缺,但毕竟是部门的一把手,萝卜不大长在脊子上,那些想提正职苦于无门的,年龄大了找养老地方的,当作提拔重用中转站的,还有那些从乡镇回县城心情迫切而又一时没有合适位子的,无不削尖了脑袋往里钻。总共才十年时间,就换了六茬子主席,别说当主席了,这个副主席还是托人弄了几幅名人字画换来的。这次调整,按说该轮到他了,没想到半路又杀出个赵玉山来,结果是不仅没当上主席,这些年连创作也荒废了。其实高长水心里有数,就是赵玉山不过来当主席,也会有王玉山或李玉山挨号等着,龙袍三辈子也披不到他的身上,因为他没有坚强的后盾和特别的背景。仅去年发生在他身上的“裤带事件”,就早已使他威信扫地,永无抬头之日了,尽管是千古之冤。好在赵玉山是圈内人士,又是内行,还有一定的级别,人品也不错,与前几任主席相比,高长水想来心里还是比较平衡和塌实的。高长水自知仕途无望了,便专修业务,试图在创作上搞出点名堂来。苗青学的是中文专业,有文字功底,大学毕业后通过关系直接分到了文联。个人创作上虽然用了不少功夫,可来文联整十年了,一直没有写出像样的东西来,只在报纸和边缘文学刊物上发表了一些豆腐块文章。说起来挺寒碜,但苗青却不这么认为,她说这叫藏龙卧虎、厚积薄发,一旦大作出手,定会一鸣惊人的,还当着赵玉山的面吹过大牛。
赵玉山明白,多数成名成家的作家都有过类似艰难曲折的磨砺过程,可他不相信苗青能写出像样的作品来。还大学中文系毕业呢,连起码的会议通知和领导讲话都写不好,怎谈得上创作文学精品啊!赵玉山指的是前几天举办的那次纪念活动。高长水不懂材料,任务自然落到了苗青头上。到了活动的前一天上午,苗青才将材料交到赵玉山手里。不知苗青不会写还是态度不端正,反正是写得一团糟,为了赶进度,害得赵玉山连中午饭都没吃上。如果不是碍着女同志的面子,赵玉山非发火不可。工作不怎么样,地位和荣誉倒挺计较的,听说这个主席助理就是她在姜部长面前哭鼻子,姜部长没办法赏给她的。赵玉山认定,文联工作被动,年底考核倒数第一名,原来的温主席没有工作思路,没搞好与外界的关系是主要原因,但与高长水和苗青不配合,甚至拆台也有直接联系。赵玉山毕竟在官场上闯了几十年,深知内部稳定比外界关系还重要,利用好了是左膀右臂,处理不好就会成为埋在身边的定时炸弹,说不定啥时也会将自己炸得血肉横飞,其下场比温主席还要悲惨,所以赵玉山便时时处处小心谨慎,在相互关系上尽量不出现丝毫的差错。就从作息制度说起吧,高长水说夜里加班搞创作,苗青既要夜里加班搞创作,早上又要送孩子上学,经常迟到早退,不仅拿制度当儿戏,理由还挺充分的,说省里市里的专业作家和画家没有坐班的,都在家里搞创作,我们却坚持上班,凭这一点也应该受到表扬。赵玉山想,你们又不是专业作家和画家,充其量不过是业余爱好者,有什么资格与省市的相提并论?但考虑到实际情况,自己又初来乍到,还是放任自流了。可文联毕竟是管理机关,现在县里又在大抓特抓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三日两头的检查卫生,别看是不起眼的小事,忽视了也会影响部门形象,所以赵玉山只好天天赶早上班,亲自打扫卫生。
赵玉山憋着一肚子气,独自打扫完室内和室外的环境卫生时,已经到了八点多钟。直到这时,高长水和苗青还没有过来上班。扔掉手里的拖把,赵玉山禁不住骂了声妈的,什么作风啊!随后就趴在桌上给两人打电话。赵玉山急着让他们过来,是诚心征求意见,深入研究一下自己起草的那份工作方案,定稿后抓紧向姜部长汇报。这些工作必须赶在“五一”前完成,挺紧张的,满打满算还有两个半月时间。然而,一个人也没找着。不仅没找着人,还让高长水的老婆李桂兰喷了一脸口水。
赵玉山先拨的高长水的手机,手机关着,接着就打家里的电话。电话是李桂兰接的。赵玉山问高长水干什么去了,怎么没过来上班?李桂兰没好气地说,你问我,我问谁啊?我还到处打听他到哪里鬼混去了呢!你是他的领导,得多管着他点才行啊!李桂兰是高长水从农村带出来的,因干文联的手里没有权力,又拉不下架子求人,这些年一直在家里闲着。李桂兰开始对高长水挺放心的,可天长日久便听到了些闲话。搞美术的本来就有风流画家的臭名,很多人又给李桂兰耳朵里灌风,说高长水画画时天天与女人混在一块儿,时间长了哪有不出事的。
李桂兰就有了警觉,处处监视高长水,可好几年了也没搞到真凭实据,只得自寻烦恼。赵玉山因是圈内人士,早在横河乡时就听说过高长水和苗青关系暧昧的传闻,但他并不十分在意,别说文艺界了,哪个单位没“办公室之恋”的类似新闻?算不得原则问题,没这样的花边新闻反倒不正常。他担心的是,如果两人真的有了感情,并且沆瀣一气,抱起团来与自己对抗,那才难办了呢!自己的前任就是很好的例证。但从维护高长水的威信和大局出发,赵玉山还是耐心地对李桂兰说,你们是夫妻关系,如果胡乱猜疑,岂不是拿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故意往丈夫脸上抹黑。我了解高长水,他是个很正派的人。李桂兰就撒泼说,还正派呢,他做的好事全县没有不知道的了。你别护着他,我知道干你们这一行的没一个好东西,除了破鞋就是大流氓!赵玉山被噎得面红耳赤,又无言以对,只好扣死电话。刚放下电话,电话机就响了起来。赵玉山以为是两人回的电话,拿起话机一听,却是宣传部办公室的人打过来的,口气也挺严肃,说让他赶紧去宣传部,姜部长找他有要事相谈。赵玉山不敢怠慢,匆忙中带上那份方案就急匆匆去找姜部长。
文联在县委办公楼顶楼,与宣传部间隔两层,本来直上直下冲着,可楼下的部门图清静,不顾楼上部门的反对,硬将楼道堵死了,去宣传部只得绕很远一段距离,可此时却给赵玉山提供了思考问题的机会。赵玉山边走边将需要汇报的几个问题大致梳理了一遍,试图汇报得更圆满一些,只有得到姜部长认同与支持,才好顺利开展工作。一边琢磨着,不知不觉就来到姜部长办公室门口。他没像以前那样直接往里闯,而是轻轻敲了几下门,得到允许后才推门进去。因为是要好的老同学,赵玉山以前来找姜部长时,对方每次都是起身迎接,递烟倒水,热情有加,可这次却一反常态,连让他坐下的意思都没有。赵玉山尴尬极了,站了一会儿,只好在沙发上找了个合适的位置坐下来。
见姜部长不高兴,板着脸不说话,赵玉山没敢直接递材料,但又不能老是僵持着,就试探着问,姜部长,你找我有事?见姜部长没有反应,赵玉山愣了愣又说,这些日子只顾调查研究了,没及时过来汇报工作,不知领导有什么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