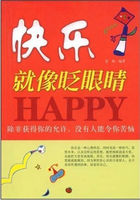1589年(万历十七年),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的战争长达六年之久,他随着统治区域的扩大,管辖部民的增多,以及王权的建立,组建了一支军队。这支军队,在那时候分为四个兵种:环刀军、铁锤军、串赤军与能射军。这仅见于《李朝宣祖实录》,现抄录如下:“左卫酋长老乙可赤兄弟,以建州卫酋长李以难等为麾下属。老乙可亦则自中称王,其弟则称船将;多造弓矢等物,分其军四运:环刀军,铁锤军,串赤军,能射军。间闲练习,胁制群胡。”
老乙可赤也就是努尔哈赤,降建州卫酋长李以难等,隶之麾下。他多造弓矢,分为四军,练习骑射,严定军纪。四军编制,是后来四旗和八旗的基础。
建州四军的军队数量,《李朝宣祖实录》记载:1592年(万历二十年),“努尔哈赤部下原有马兵三、四万,步兵四、五万,都精勇惯战。”但这话出自建州贡民马三非等之口,有夸大的可能性。
三年后,朝鲜通事河世国到费阿拉,大概目睹:“老乙可赤麾下万余名,小乙可赤麾下五千余名,常在城中,而常时习阵千余名,各自骑着战马、着甲,城外练兵。而老乙可赤战马则七百余匹,小乙可赤战马四百余匹,并为考点矣。”这时努尔哈赤已统一建州女真,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明朝官员余希元至费阿拉,入城前,有建州骑兵四五千左右成列随行;又有“步兵万数,分左右列立道旁者,到建州城而止”。以此推算,当时建州的步骑兵大概有二三万人。这些军队,已按旗编制。《满洲实录》在记述1593年(万历二十一年)古勒山之役时,作如下记载:
“太祖兵到,立阵于古埒山险要之处,同赫济格城相对。命令各王大臣等各率固山兵,分头预备。”
而《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也作了同样记载:
“上至古勒山,对黑济格城,据险结阵。令各旗贝勒大臣,整兵以待。”
由上可知,努尔哈赤早已将建州士兵编成各旗,而且很早以前就有军旗。
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朝鲜人申忠一到费阿拉,所见建州军旗:“旗用青、赤、黄、黑、白,各付二幅,长可二尺有余。”
努尔哈赤始设四旗一事,清朝有的史籍系于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根据《清太祖高皇帝实录》所载:
“上以诸国徕服人众,复编三百人为一牛录,每牛录设额真一。开始,我国凡出兵校猎,各随族党屯寨而行。猎时,每人各取一支箭,凡十人,设长一,领之,各分队伍,毋敢紊乱者。其长称牛录额其。至是,遂以名官。”事实上,努尔哈赤于这一年对建州军队进行了一次整编。他“复编三百人为一牛录”,每牛录设额真一员,以黄、白、红、蓝四色为旗的标志。这种划分,为以后八旗制度的确立奠定基础。
1615年(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努尔哈赤除建州外,已经统一哈达、辉发与乌拉,史载其降俘乌拉卒骑,“不下数万人”;又征抚很多东海女真部民。建州幅员益广,步骑增多,“归附日众,乃析为八”,除原有四旗,再增设四旗,这样一来共为八旗。
女真社会历史发展同生产关系所产生的特殊社会结构——八旗制度,既有利于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又有利于满族共同体的形成。努尔哈赤通过八旗让分散的女真部民组织起来,管理女真的农业、采集业、畜牧业、渔猎业与手工业生产,提高了女真的社会生产力。
同时,随着对瓦尔喀、虎尔哈、卦勒察、萨哈连、蒙古人、达斡尔、汉人等的征附,得到一部人就编为一牛录。努尔哈赤把各部女真人等都收录旗下,加速了满族共同体的形成。天命初年,已发展到约四百个牛录。
除满洲八旗之外,1621年(天启元年,天命六年)开始设蒙古牛录,1622年(天启二年,天命七年),最初设蒙古旗,1635年(崇祯八年,天聪九年),最初设蒙古八旗,旗色同满洲八旗相同。1631年(崇桢四年,天聪五年),努尔哈赤的继承人皇太极将满洲八旗中的汉人拨出,另编一旗。
汉军初名乌津超哈,在满语中的意思是重兵,因其多使用大炮等重型武器而得名,后又叫做汉军,以黑色为旗帜。1637年(崇祯十年,崇德二年),分设汉军为二旗。1639年(崇祯十二年,崇德四年)又增设汉军二旗,旗色为纯皂(黑)、皂镶白、皂镶黄、皂镶红。1642年(祟祯十五年,祟德七年),汉军扩充为八旗,旗色改为同满洲八旗、蒙古八旗相同,取消了黑色。自此,实际有蒙古八旗、满洲八旗、汉军八旗,共二十四旗,但习惯上依然称之为八旗。
努尔哈赤建立八旗制度,作为总的纲领,把女真社会的行政、军事、生产统治起来。女真各部的部民,被按军事方式,分为三级,加以编制。努尔哈赤采用军事方法管理行政、管理经济,让女真社会军事化。
所以,在努尔哈赤统治时期,全部女真社会就是一座大兵营。这一点,也正是努尔哈赤统治时期女真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
努尔哈赤以八旗作纽带,把涣散的女真各部联结起来,形成一个组织严密的、生气勃勃的社会整体,在那个时候是有积极意义的。这正是他崛起东北地区,统一女真各部,实施社会改革与屡败明朝军队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放弃自己的目标而去大力实施就会取得成功。努尔哈赤创建八旗制度,本是我国满族发展史上一件大事,也是他的一大功绩,可谓大手笔。
处理问题要彻底
扬汤止沸,釜底抽薪。处理问题要彻底。但你必须保证抽出来的“薪”能够把自己的火烧得更旺,否则,听任这些“薪”堵塞自己的炉灶,只冒烟不冒火呛坏了自己,那才是糟糕之极。《吕氏春秋》中说:“夫以汤止沸,沸愈不止,去其火,则止矣。”告诉我们在解决问题时,要注重消除引起问题的根本原因。
西汉高祖二年(前205),汉王刘邦与楚王项羽大战于彭城,却失败了。刘邦问属下:“谁能为我去一趟淮南,让九江王黥布发兵叛楚,把项羽留在齐地数月,我便有把握取天下。”随何说:“我愿意出使淮南。”于是随何同二十余人一起去淮南。
到淮南,九江王黥布三日不见,随何反复劝说,分析其中的利害。他说:“大王发兵叛楚,项羽必然留在东南之地,那么汉王刘邦夺取天下势在必得。所以我请求大王仗剑归汉王,汉王一定会割地分封大王,这样淮南一定会归大王所有。所以,汉王派我来进此愚计,希望大王稍加留意。”黥布终于同意了。黥布叛楚,等于从后面牵制了项羽,刘邦的危机解决了。
随何说服黥布反水,便是釜底抽薪的一招。这一招在商战中也常常使用。上世纪90年代末,长虹买断中国70%彩色显像管,便是典型的例子。
从1996年开始,市场彩电价格大战拼得如火如荼,使得彩电整机价格节节败落。在整个彩电零部件中,显像管占成本的70%左右,整机价格下降,显像管首当其冲。在这种情形下,长虹凭借雄厚的资金与良好的商誉作后遁,从1998年下半年开始,大量吸纳彩色显像管。正因为如此,当长虹彩电旺季时,各厂家却彩管明显供不应求,甚至出现停产现象,因此,长虹一举奠定了行业霸主地位。
长虹非常有预见性。试想,倘若他的伏军无法卡在“敌人”的必经之道,那它的决策成本将会是怎样的高?实际上,长虹的做法当时确实引起了竞争对手的集体恐慌,他们甚至只能请政府的“有形的手”出面干涉。只可惜,长虹的“釜底抽薪”虽然厉害,而中国彩电行业毕竟也非长虹一家天下,而且技术要求不高,使长虹并没掌握见血封喉的独门暗器。与之相反,彩电行业进一步竞相杀价竞争时,长虹反而要承受着彩管大量库存的痛苦,正是如此,2000年,彩电大鳄长虹首次报亏。
如果想成功地“釜底抽薪”,应该注意以下几点:一、“薪”必须是敌人的重要资源,是其发展的瓶颈。二、自己必须有一定的实力,使自己能将敌人的“薪”抽尽,而自己不会提前垮掉。你必须保证抽出来的这些“薪”能够把自己灶中的火烧得更旺,不然,听任这些“薪”堵塞自己的炉灶,变得只冒烟,不出火,呛坏了自己,才会使自己后悔。
随机应变,巧中取胜
综观曾国藩一生的思想倾向,他是以儒为本,杂以百家。上述各家思想,几乎在他每个时期都有体现。但是,随着形势、处境与地位的变化,各家学说在他思想中体现的强弱程度又有所不同,这正体现出曾国藩善于运用各家学说的“权变”之术。
曾国藩的同乡好友欧阳兆熊以前觉得,曾国藩的思想一生有三变。以前在京城时信奉儒家,治理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时用法家,晚年功成名就后则转向了老庄的道家。这便是曾国藩一生三个时期的重要思想特点。
为官期间打下了扎实的儒学功底。他用程朱理学这块敲门砖敲开了做官的大门之后,并没有把它丢在一边,而是对它进行了深入研究。
在新的环境里,他得到了唐鉴、倭仁等理学大师的点拨,登堂入室,便又走向了一个新的境界。他不仅对理学论证纲常名教和封建统治秩序的一整套伦理哲学,如性、命、理、诚、格物致知等概念,有了深入的认识与理解,而且还进行了理学所重视的身心修养的系统训练。这种身心修养在儒家是一种“内圣”的功夫,通过这种克己的“内圣”功夫,来平定天下。他还发挥了儒家的“外王”之道,主张经世致用。
唐鉴曾对他说,经济,就是经世致用包括在义理之中,曾国藩完全同意,并大大地加以发挥。他非常注重对现实问题的考察,重视研究解决的办法,提出了很多改革措施。曾国藩对儒学,特别是深入探索程朱理学,是他这个时期的重要思想内涵,而对于这一套方法、理论的运用,便贯穿于他的一生。
太平天国时期,曾国藩临危受命,组织湘军镇压农民起义。此时,非常鲜明地体现出他对法家思想的推崇。他提出要“纯用重典”,采取强硬的手段镇压。而且,他还向朝廷表示,就算由此而得残忍严酷之名,他也在所不辞。他也的确是这样做的,他设立审案局,对所捕农民严刑拷打,任意杀戮。他还规定,不完粮者,一经抓获,就地正法。在他看来,儒家的“中庸”之道,是不适用于这个关键时期的。
曾国藩的老庄思想,从始至终都具备。他常表示,在名利方面,须存退让之心。自太平天国败局已定,马上大功告成之时,这种思想日渐加强,一种兔死狗烹的危机感时常萦绕在他心头。他写信给弟弟说,从古至今,权高名重之人没有几个能有善终,要将权位推让几成,才能保持晚节。天京攻陷之后,曾国藩便马上遣散湘军,并做好功成身退的打算,以免除清政府的疑忌。
三个时期不同的思想,说明曾国藩善于在不同的处境中,从诸子百家中吸取养分。容闳说,曾国藩是“旧教育中之特产之物”。的确在曾国藩身上,熔铸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基因,正是这些基因,让曾国藩成了封建社会的“三不朽”人物与最后一个精神偶像。
关于曾国藩处世态度从刚至柔有一个重要的过程。这个过程就发生在1858年。曾国藩初出治军,严刑苛刻,手段非常刻薄,从他杀李金阳事件看得出他的残酷无情,且同将帅多相忤。然自1858年再起,大存放变。这一变化过程有记载说:先是文正(曾国藩)同胡文忠(胡林翼)书,言恪靖(骆秉璋)遇事掣肘,哆口谩骂,有劝效王小二过年再不开口之语。至八年夺情再起援浙,甫到省,有“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属恪靖为书纂联以见意,同以前一样要好,不念旧恶。这次出山后,以柔道行之,以致成功,毫无沾沾自喜之色。尝戏谓予曰:“他日有为吾做墓志者,铭文吾已撰: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告万世。”故予挽联中有“将汗马勋名,问牛相业,都比作秕糠尘垢”数语,自谓道得此老心事出。盖尝言以禹墨为体,以老庄之术之本,可知其所趋向也。
曾国藩如何变得“柔顺”了呢?有人认为罗汝怀的劝勉最有影响。当曾氏丁父忧请假于家时,汝怀寄以书,以尚平实不争权相劝。其书略云:
独识阁下为奇士,所见四方之士无出其右者,为何?天下为平实坚术之人可以干事,军务特别如此。阁下无大僚尊贵的习惯,行履部伍,亲自把接细节。庶几大禹之栉风沐雨,手胼足胝,故能船炮坚利,壁垒坚固。也就是粪厕亦有方隔,所谓道去屎溺,这不是高谈渺论不知而作者所能望见也,乃复温乎其容,抑然自下,慕好贤之雅,循周咨之节,日冀奇士之至于前,然而战胜城弗克,饷弗给,奇士无如何也。我本来就很奇怪,斯不免太奇之病矣。夫救乏自古无奇策,况在今日糈饷之匮。然生财之道,未尝无良法,尤贵有关意。
鄙谚曰:“官出于民,而民出于土地。”其折拨捐抽之法,要在使民无怨,且使官无怨,财源无窒塞之患。使民无怨,阁下所知而以为美谈者也;让官无怨,则阁下所不知而以为口说者也。惟其然也,所以折漕自我,拨漕自我,捐资抽税都欲自我,而不复有人之见存焉。虽军务者阁下之专司,而民者疆吏之职守,各持其是,按一个地方也一样。阁下军政必自己操,大权未尝旁落,而欲兼掌一方土地人民之事,若圣人之设官分职,官事无摄者非乎?
罗汝怀之书,把曾国藩苛求及垄断权力之病,说得入木三分。曾国藩能虚怀而受之,其1858年以后之立身行事也深受其影响。若将1854年因与王鑫不惬而不救其败事,与1864年同左宗棠绝交后仍能助其成大功于西北二事相比,就可见曾国藩之待人接物,前后判若两人。
世谓曾国藩以禹墨为体,老庄为用,其至曾国藩在1858年以前以禹墨为体,申韩为用。1858年以后,开始趋向巽顺。如果将曾国藩的一生处世也按三个阶段来看,此各有其特点,第一阶段,为奋发向上的时期;第二阶段,为规划经营,功德圆满之时;第三阶段,为自主自抑,持盈保泰,不在胜人处求强的和平时期。民国的何贻焜说:
曾公之三个时期来说,则早年生活,如同朝日,气象蓬勃。无论情感意志,学问德行,都有蒸蒸日上之势。及至中年,则如白日中天,盛极一时,无论事业文章,道德学问,都已渐臻成熟,篾以复加。洎乎晚年,好像斜阳晚照,好景无多,虽德量愈醇,让人仰慕,志气事功,也少替矣。
可见曾国藩的处世,不仅是一生三变,甚至可说是一生多变。
有的时候坚持,是不明智之举。谋取胜局者都有一个特点:随机应变,巧中取胜。曾国藩一生经过三次大调整,不停地改变谋略,故终于谋取胜局。
随机应变,是获取成功的关键。曾国藩的处世之道,事实上是一种灵活辩证的处世态度和方法。虽然他处世中勤于功名,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坚守仁义道德,而在做事为人的“形”上却是一生三变。正是这“三变”,包含了人们对他的评价。但,无论如何,没有这适时的“三变”,便不会有他的更大成功与显赫声名。
把握机遇,大局可定
左宗棠的人生关键点是于1861年与太平军的江西鏖战。当时太平军于鄱阳湖一带大败曾国藩,逼得曾国藩差点要自杀,幸亏左宗棠以寡敌众,同太平军死拼,才挽回败局。曾国藩对他格外器重,并向朝廷请功。自此受到清廷重视,打下了通向胜利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