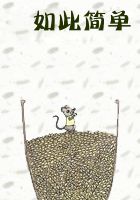为了爱,勇敢向前,哪怕违了自己的特性,威胁到了生命。因为爱,一切都不是障碍,任谁也无法阻拦,即便化成化石,也要迈步。这种勇气,你有没有?刘若英有首歌唱道:请问你敢不敢,像我这样的痴狂?唯有痴狂,爱才得以纯净和永恒。
(人生感悟)
爱是一朵从天飘下来的雪花,还没结果已经枯萎,爱是一滴擦不干烧不完的眼泪,还没凝固已经成灰。谁说爱情一定要有结果呢?缘起缘灭,缘浓缘淡,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我们能做到的,是在因缘际会的时候好好地珍惜那短暂的时光。
总有一片爱情,让人泪流满面
结婚后她一直给他做洋葱吃:洋葱肉丝、洋葱焖鱼、香菇洋葱丝汤、洋葱蛋盒子……因为她第一次去他家,他母亲拉了她的手,和善地告诉她——虽然他从不挑食,但从小最爱吃的是洋葱。
她是图书管理员,有足够的时间去费心思做一款香浓的洋葱配菜,但他却总是淡淡的。母亲为他守寡近20年,他疯狂爱着的女子母亲却不喜欢,他对她的选择与其说是爱,不如说是对自己孝心的成全。
她似乎并没有什么察觉,百合一样安静地操持着家,对他母亲也照顾得妥帖周到。婚后第四年,他们有了一个乖巧可爱的女儿。
平滑的日子一日日复印机一样地掠过,再伤人的折磨也钝了。当初流泪流血的心也一日日结了痂,只是那伤痕还在,隐隐的,有时半夜醒来还在那里突突地跳。
那天他去北京开学术会,与初恋情人小玉相遇,死去的****电石火花般啪啪苏醒。相拥长城,执手故宫,年少的激情重新点燃了一对不再年轻的苦情人。
小玉保养得圆润优雅,比青涩年少更多丰韵,一双手指玉葱般光滑细嫩。在香山脚下他给她买了当年她爱吃的烤地瓜。她娇嗔地让他给剥开喂到她的嘴里,因为她的手怕烫。七天很快过完,他回家,记得她娇艳如花的巧笑,记得她喜欢用银匙子喝咖啡,记得她喜欢吃一道他从没吃过的甜点提拉米苏。
母亲已经故去,他不想太苛待自己了,每年他都以开会或者公差的名义去北京。妻子单位组织旅游的时候,他还甚至让小玉来过自己的家。他的手机中也曾经爆满火热滚烫的情话,甚至他们的合影曾经被他忘在脱下的上衣口袋里,呆了一个多星期……可这一切都幸运地没有被发觉。
平地起风云,妻子突然被查出得了卵巢癌,已经是晚期了。住进医院后,女儿上学需要照顾三餐,成堆的衣服需要清洗,家里乱成一团糟。那次他在家翻找菜谱时,在抽屉里发现了一个带扣的硬壳本子。打开,里面竟然有几根玄红的长发。妻子一向是贴耳短发,自结婚以后。他好奇地看下去,原来这是他和小玉缠绵后留下的,还有那些照片,妻子一直都知道,因为从来没让他的脏衣服过夜。他背着妻子做的一切,妻子都心如明镜,却故作不见。几乎每页纸上都写着这么一句话:相信他心里是爱着我的。后面是大大的几个叹号。
他心里一片空茫地去医院,握住妻子磨粗的手,问她想吃什么。妻子笑着说,你会做什么菜,去给我买一份鸭血粉汤吧。她每天做好了他爱吃的洋葱,熨好了他第二天穿的衬衣,在家等他,20多年了,他却从来不知道在南方长大的她爱吃鸭血粉汤。
妻子走后,他掉魂一样地站在厨房里为自己做一道洋葱肉丝。他遵照她的嘱咐将洋葱放在水里,然后一片片剥开,眼睛还是辣得直流泪。当他准备在案板上切成细丝时眼睛已经睁不开,热泪长流。他从来不知道那样香浓的洋葱汤,做的过程这么艰难苦涩。七千多个日子,妻子就这样忍着辣为自己做一份洋葱丝,只因为他从小就喜欢吃。
而小玉那双保养得珠圆玉润的手,只肯到西餐店拿匙子吃一份提拉米苏。而当年母亲是怎样洞若观火,知道妻子能给予他的安宁和幸福。傍晚时分,一个站在九楼厨房里的男人拿着一瓣洋葱流泪发呆,他终于知道真正的爱情就像洋葱:一片一片剥下去,总会有一片能让你泪流满面……
(人生感悟)
张爱玲说,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两个女人,至少两个。娶了红玫瑰,久而久之,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白的还是“窗前明月光”;娶了白玫瑰,白的便是衣服上的一粒饭渣子,红的却是心口上的一颗朱砂痣。当时间过去,你忘记了自己曾经义无反顾地爱过一个人,忘记了她的温柔,忘记了她为你做的一切。浮躁的内心起伏不定,最后,你终究败给了自己。
狼行成双
他们在风雪中慢慢走着。他和她,他们是两只狼。他的个子很大,很结实,刀条耳,目光炯炯有神,牙齿坚硬有力。她则完全不一样,她个子小巧,鼻头黑黑的,眼睛始终潮润着,有一种小南风般朦胧的雾气,在一潭秋水之上悬浮着似的。他的风格是山的样子,她的风格是水的样子。
刚才因为她故意捣乱,有只兔子在他们的面前眼巴巴地跑掉了。
他是在她还是少年的时候就征服了她的。然后他们在一起相依为命,共同生活了整整9年。这期间,她曾一次次地把他从血气冲天的战场上拖下来,把伤痕累累昏迷不醒的他拖进荒僻的山洞里,用舌头舔他的伤口,舔净他伤口的血迹,把猎枪的砂弹或者凶猛的敌人的骨头渣子清理干净,然后,从高坡上风也似的冲下去,去追捕獐獾,用獐脐和獾油为他涂抹伤口。做完这一切后,她就在他的身边卧下,整日整夜的,一动不动。
但是,更多的时候,是由他来看顾她的。他们得去无休无止地追逐自己的食物,得与同伴拼死拼活地争夺地盘,得提防比自己强大的凶猛的对手的袭击,还得随时警惕来自人类的敌视。这真的很难,有时候他简直累坏了。他总是伤痕累累,疲于应战。而她呢,却像个不安分的惹事包,老是在天敌之外不断地给他增添更多的麻烦。她太好奇而且有着过分的快乐的天性。她甚至以制造那些惊心动魄险象环生的麻烦为乐事。他只得不断地与环境和强大的敌手抗争。他怒气冲天,一次又一次深入绝境,把她从厄运之中拯救出来。他在那个时候简直就像一个威风凛凛的战神,没有任何对手可以扼制住他。
他的成功和荣誉也差不多全是由她创造出来的。没有她的任性,他只会是一只普通的狼。天渐渐地黑下去,他决定尽快地去为她也为自己弄到果腹的食物。
天很黑,风雪又大,他们在这种状况下朝着灯火依稀可辨的村子走去,自然就无法发现那口井了。
井是一口枯井,村子里的人不愿让雪灌了井,将一黄棕旧雪被披在井口,不经心地做成了一个陷井。
他在前面走着,她在后面跟着,中间相隔着十几步。他丝毫也没有预感,待他发觉脚下让人疑心的虚松时,已经来不及了。
她那时正在看着雪地里的一处旋风,旋风中有一枝折断了的松枝,在风的嬉弄下旋转得如同停不下来的舞娘。轰的一声闷响从脚下的什么地方传来。她这才发觉他从她的视线中消失了。她奔到井边。他有一刻是昏厥过去了。但是他很快就醒了过来,并且立刻弄清楚了自己的处境。他发现情况不像想的那么糟糕。他只不过是掉进了一口枯井里,他想着算不得什么。他曾被一个猎人安置的活套套住,还有一次他被夹在两块顺流而下的冰砣当中,整整两天的时间他才得以从冰砣当中解脱出来。另外一次他和一头受了伤的野猪狭路相逢,那一次他的整个身子都被鲜血染红了。他经过的厄运不知道有多少,最终他都闯过来了。
井是那种大肚瓶似的,下畅上束,井壁凿得很光溜,没有可供攀援的地方。
他要她站开一些,以免他跃出井口时撞伤了她。她果然站开了,站到离井口几尺远的地方。除了顽皮的时候,她总是很听他的。她听见井底传出他信心十足的一声深呼吸,然后听见由近及远的两道尖锐的刮挠声,随即是什么东西重重跌落的声音。
他躺在井底,一头一身全是雪和泥土。他刚才那一跃,跃出了两丈来高,这个高度实在是有些了不起,但是离井口还差着老大一截子呢。他的两只利爪将井壁的冻土刮挠出两道很深的印痕,那两道挠痕触目惊心,同时也是一种深深的遗憾。
她爬在井沿上,先啜泣,后来止不住,放声出来。她说,呜呜,都怪我,我不该放走那只兔子。他在井底,反倒笑了。他是被她的眼泪给逗笑的。在天亮之前的那段时间里,她离开了井台,到森林里去了,去寻找食物。她走了很远,终于在一棵又细又长的橡树下,捕捉到一只被冻得有些傻的黑色细嘴松鸡。
他把那只肉味鲜美的松鸡连骨头带肉一点不剩全都嚼了,填进了胃里。他感觉好多了。他可以继续试一试他的逃亡行动了。
这一次她没有离开井台,她不再顾忌他跃上井台时撞伤她。她趴在井台上,不断给他鼓劲儿,呼唤他,鼓励他,一次又一次地催促他跳起。隔着井里那段可恶的距离,她伸出双爪的姿势在渐渐明亮起来的天空的背景中始终是那么地坚定,这让井底的他一直热泪盈眶,有一种高高地跃上去用力拥抱她的强烈欲望。
然而他的所有努力都失败了。
天亮的时候她离开了井台,天黑之后她回来了。她很艰难地来到了井边,她为他带来了一只獾。他在井底,把那只獾一点不剩的全都填进了胃里。然后,开始了他新的尝试。
她有时候离开井台,然后她再折回到井台边来。她总觉得在她离开的这段时间里,奇迹更容易发生。
她在那里张望着,企盼着当她回到井台边的时候,他已经大汗淋漓地站在那里,喘着粗气,傻乎乎地朝她笑了。但是没有。天亮的时候,她再度离开井台,消失在森林里。
天黑的时候,她疲惫不堪地回到了井台边。整整一天时间,她只捉到了一只还没有来得及长大的松鼠。她自己当然是饿着的。但是她看到他还在那里忙碌着,忙得大汗淋漓。他在把井壁上的冻土,一爪一爪地抠下来,把它们收集起来,垫在脚下,把它们踩实。他肯定干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他的十只爪子已经完全劈开了,不断地淌出鲜血来,这使那些被他一爪一爪抠下来的冻土,显得湿漉漉的。她先是愣在那里,但是她很快就明白过来了,他是想要把井底垫高,缩短到井口的距离。他是在创造着拯救自己生命的通道。
她让他先一边歇息着,她来接着干。她在井坎附近,刨开冰雪,把冰雪下面的冻土刨松,再把那些刨松的冻土推下井去。她这么刨一阵,再换他来,把那些刨下井去的冻土收集起来垫好,重新踩实。
他们这样又干了一阵,他发现她在井台上的速度慢了下来。他有点急不可耐了。他不知道她是饿的,也很累,她还有伤。天亮时分,他们停下来。他们对自己的工作很满意。如果事情就像这样发展下去,他们会在下一次太阳升起的时候最终逃离那可恶的枯井,双双朝着森林里奔去。
但是村子里的两个少年发现了他们。
两个少年走到井台边,朝井下看,他们发现了躺在井底心怀憧憬的他。然后他们跑回村子里拿猎枪来,朝井里的他放了一枪。
后来其中一个醒悟过来。他把手中的猎枪举起来。
枪声很闷。子弹钻进了雪地里,溅起一片细碎的雪粉。她像一阵干净的风,消失在森林之中。枪响的时候他在枯井里发出长长的一声嗥叫。他的嗥叫差不多把井台都给震垮了。在整个夜晚,她始终等待在那片最近的森林里,不断地发出悠长的嗥叫,他知道她还活着,他的高兴是显而易见的。他一直警告她,要她别再试图接近他,要她回到森林的深处去。永远不要在走出来。
她仰天长啸着,她的长啸从那片森林里传出来,一直传出了很远。
天亮的时候,两个少年熬不住打了一个盹。与此同时,她接近了井台,她把那只冻得发硬的黄羊拖到井台边上去。她倒着身子,刨飞着一片片雪雾,把那头黄羊,用力推下了枯井。他躺在那里,不能动。那头黄羊就滚到他的身边。他大声地叫骂她。他要她滚开,别再来烦他,否则他会让她好看的。
他头朝一边歪着,看也不看她,好像对她有着多么大的气似的。她爬在井台上,尖声地呜咽着,要他坚持住,只要他还有一口气,她就会把他从这该死的枯井里救出去。
两个少年后来醒了。在接下去的两天时间里,她一直在与他们周旋着。两个少年一共朝她射击了7次,都没能射中她。
在那两天的时间里,他一直在井里嗥叫着,他没有一刻停止过。他的嗓子肯定已经撕裂了,以至于他的嗥叫断断续续,无法延续成声。
但是在第三天的早上,他们的嗥叫声突然停止了。两个少年,探头朝井下看,那头受了伤的公狼已经死在那里了。他是撞死的,头歪在井壁上,头颅粉碎,脑浆四溅。那只冻硬了的黄羊完好无损地躺在他身边。
那两只狼,他们一直在试图重返森林。他们差一点就成功了。
他们后来陷进了一场灾难。先是他,然后是她,其实他们一直是共同的。现在他们当中的一个死去了。他死去了,另一个就不会再出现了,他的死不就是为这个么?
两个少年,回村里拿绳子。但是他们没有走多远就站住了。她站在那里,全身披着银灰色的皮毛,皮毛伤痕累累,满是雪痂。她是精疲力竭、身心俱毁的样子,因为皮毛被风吹动了,仿佛是森林里最具古典性的幽灵。她微微地仰着她的下颌,似乎是轻轻地叹了口气,然后,她朝井台这边轻快地奔来。
两个少年几乎看呆了,直到最后一刻,他们其中的一个才匆匆地举起了枪。子弹从她的后脊梁射进去,从她的左肋穿出。血像一条暗泉似地往外窜,她一下子就跌倒了,再也站不起来。
枪响的时候,停歇了两天两夜的雪又开始飘落起来了。
(人生感悟)
就像蝴蝶飞不过沧海,没有谁忍心责怪。因为只要蝴蝶曾在沧海上飞过,就已足够,结果,永远没有过程重要。两只为爱情坚守的狼最终死去了,或许很多人为此感到失望,但人生又怎能都是心想事成、美满团圆呢?不管结局如何,那份面对生死而表现出的淡定、从容,已足够震撼人心,令人泪流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