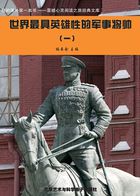黄侃这样牛气,可是认识他的人没有一个非议的,反而有很多人觉得大师就是这样的,谁让人家才学高呢。
黄侃讲课,以天马行空着称,一般学生很难跟上他的思维,但是一旦入了门道,又仿佛置身山阴道上,学问之美让人目不暇接。在北大讲“说文解字”时,他一不带原书,二不带讲稿,引经据典,口若悬河,头头是道。学生对引用的经典论据下课以后去查书,一字不漏,一字不错。黄侃治学强调要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听其讲学,常有新鲜感。
黄侃善于咏诵诗章,带有浓郁黄氏风格的“黄调”一时在北大十分流行。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说:“黄侃善于念书念文章,他讲完一篇文章或一首诗,就高声念一遍,听起来抑扬顿挫,很好听。他念的时候,下面的观众都高声跟着念,当时称为‘黄调’。当时的宿舍里,到晚上各处都可以听到‘黄调’。”
由于黄侃的才学加上他那口令人拍案叫绝的“黄调”,慕名听课者把他的课堂都要挤破。黄侃在金陵大学上课时,该校农学院院长是一位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海龟”,一则看不起黄侃研究的古董学问,二则年轻气盛,准备跟黄侃较量一下,看两个人的课谁的更受学生欢迎。为了吸引大家的眼球,这位院长决定在学校礼堂公开表演“新法阉猪”,海报贴出,全校轰动。当日黄侃上课时,学生们果然纷纷跑去看“新法阉猪”,以至于上课者寥寥。黄侃知道真相后,索性宣布今天不上课了,随后他自己也跟着学生一起去凑个热闹。
到了现场,只见那院长得意扬扬地让人将一头肥猪捆绑在架上,然后开膛剖肚,谁知他弄了半天也未能找到猪的卵巢,这头肥猪经不起折腾一命呜呼了,本想“阉猪”,最后却成了“杀猪”。事后,黄侃写了一首词送给这位院长:大好时光,莘莘学子,结伴来睹。佳讯竞传,海报贴出,明朝院长表演阉猪,农家二畜牵其一,捆缚按倒皆除。瞧院长,卷袖操刀,试试功夫。渺渺卵巢知何处?望左边不见,在右边乎?白刃再下,怎奈它一命呜呼,看起来,这博士,不如生屠。
除了才学之外,黄侃最让学生佩服的是他的治学精神。
黄侃热爱读书是出了名的,他最恨看到别人读书半途而废,称之为“杀书头”。黄侃曾问自己的学生陆宗达:“一个人什么时候最高兴?”陆宗达说了好几个答案,黄侃都摇头。陆宗达无奈,只好反过来问黄侃答案是什么,黄侃笑着说:“是一本书圈点到最后一卷,还剩末一篇儿的时候。”这句话让陆宗达终身受用。
黄侃认为对书要常存有敬畏之心,他读书喜欢随手圈点,往往一本书圈点了很多遍。黄侃自己曾在日记中提起对一些书的圈点情形:“平生手加点识书,如《文选》盖已十过,《汉书》亦三过,《注疏》圈识,丹黄烂然。《新唐书》先读,后以朱点,复以墨点,亦是三过。《说文》、《尔雅》、《广韵》三书,殆不能记遍数。”又有说《清史稿》全书一百册、七百卷,他从头到尾,一卷一卷地评加圈点,绝不跳过。直到临终前,黄侃还一面吐血,一面坚持将《唐文粹补遗》圈点批校完。
有些书光圈点不行,还要背,黄侃有一句名言:“《汉书》都不会背,教什么书呢?”可见黄侃是会背《汉书》的,而平常人完整看一遍《汉书》都不容易,更何况是背。
据说黄侃到了弥留之际,学生来看他,黄侃话已经说不出来了,手却指向架上一书。学生们将书拿来,黄侃翻到其中一页,手一点,似有所指。黄侃去世之后,学生们想起那书,把它翻开一看,顿时觉得雷电之光激荡天地:原来学生们看望黄侃的间歇争论一个问题,黄侃口不能答,但他最后手之所指,正是答案之所在!
黄侃在学问上睥睨当世,然而他却慎于下笔,述而不作,原来他认为着述文章是一项流芳百世的事业,不到水到渠成的成熟之境,不可轻易动笔。黄侃自己不急,他的老师章太炎却急坏了,一再催促,黄侃只好答应他:“年五十当着纸笔矣。”1935年3月23日,黄侃五十岁生日,章太炎特地写了一副对联送给他,上联是“韦编三绝今知命”,下联是“黄绢初裁好着书”。上联用的是孔子读易韦编三绝的典故,“知命”即知天命之年,赞扬黄侃五十年来勤奋读书;下联典出曹娥碑后谜似的评语──“黄绢幼妇,外孙齑臼”,曹操帐下谋士杨修解释为:“黄绢,色丝也,于字为绝;幼妇,少女也,于字为妙;外孙,女子也,于字为好;齑臼,受辛也,于字为辞。所谓‘绝妙好辞’也。”章太炎的用意不言而喻。
谁知此联无意中竟暗含了“绝”、“命”、“黄”,向来迷信的黄侃看到联后大为变色,认为这是“黄侃命绝”,虽然老师没有此意,但未必不是天意。结果还真是一联成谶,当年10月6日,黄侃因饮酒过度导致胃出血,两天后在医院与世长辞,成为学术界的一大损失。在上海的章太炎听说黄侃病逝的消息,号啕大哭,连呼:“天丧我也!天丧我也!”
至情至性
黄侃出生时,其父已经六十七岁。十三岁,黄侃失怙,由生母周太孺人和慈母田太夫人共同含辛茹苦抚养成人。
黄侃是大教授,也是大孝子。少年时为了表达对母亲的孝顺,黄侃特地弄了头驴,每天晚上吃过晚饭后,他让母亲横坐在驴上头,自己牵着驴在自己家的大花园里转着圈遛。直到有一天他母亲实在受不了了,跟他说:“儿呀,你别‘孝顺’我了,你把我‘孝顺’得受不了了。”
1908年,身在日本的黄侃接到生母病危的电报,急忙赶回国内,昼夜服侍汤药。生母去世后,他捶胸顿足,悲伤欲绝,不小心跌坐在火盆上,屁股烧伤都没有发觉。黄侃回到日本后,还特地请老友苏曼殊绘《梦谒母坟图》,自撰了题记,请章太炎作跋。这幅图后来黄侃一直带在身上,直到终老。
黄侃对慈母田太夫人一样视若生母。黄父当年在四川做官时曾自制一口棺材,后又嫌棺材太小,把它留给了田太夫人。黄侃后来四处奔波教书,总会携带这口棺材随行,令人侧目。1922年田太夫人去世后,黄侃在日记中撰写了慈母生平事略。文末云:“孤苦苍天,哀痛苍天!孤黄侃泣血谨述。”其后每逢生母、慈母生日、忌日,黄侃必亲率家人设供祭祀,无论天大的事,从不间断。
就如对母之“孝”一样,黄侃从来不刻意掩饰和压抑自己的天性,生活中的黄侃除了好书之外,还有四好:好酒、好美食、好赌、好色。
黄侃好酒,有酒无类,不管是好酒、烈酒、国酒、洋酒,来者不拒,与友人饮,每饮必醉。黄侃在中央大学时,有一次去拜访已经贵为国民政府司法院长的老乡兼好友居正。结果,衣着邋遢的黄侃不出意外地被居正家的门卫挡在门外,差点上演全武行。幸好居正闻声出来,见状忙对黄侃说:“别上火,我家里有两瓶上好的茅台,正要等你来品尝呢。”黄侃一听,怒气顿消。
黄侃的早逝与他常年酗酒不无关系。1935年的重阳时节,黄侃与友人在北极阁登高,品蟹赏菊,这样的良辰美景黄侃自然是不醉不归,回到家中他吐血半盂,终至不起。不过古人有言:“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以这样的方式死去,倒是为黄侃一生的名士风流作了最好的总结。所以,章太炎后来就此事评价自己的弟子:“断送一生唯有酒,焉知非福。”
黄侃对美食的爱好到了痴的地步,甚至为此常常不惜破坏自己的规矩。黄侃早年热衷革命,加入了同盟会,脾气暴躁的他难免和会中的一些人不相得。有一次,黄侃听说一些同盟会会员在某大酒楼聚会,席上有不少自己没有吃过的佳肴。黄侃一听,食指大动,但是这些人素来跟自己关系不好,这样不请自去岂不是让人笑话?黄侃思来想去,难耐肚中的馋虫,还是决定不请自去。宴会上的诸公看到黄侃后,一开始也是万分惊讶,但想到这人平时如此骄傲,能够屈尊前来,也算给足了自己面子,于是热情地邀他入座。没想到,黄侃就座后,二话不说,专挑好的吃,酒足饭饱之后,嘴巴一抹,抬脚就走,走到门口,突然间回过头来冲着众人说了一句:“好你们一群王八蛋!”说着,加快脚步离开了,留下在座各人目瞪口呆。
1915年,章太炎因为骂袁世凯遭到软禁,但是他的门生故旧还是可以照常去看望他。袁世凯每月给老章五百大洋,让他随意开支,老章吃喝全部都可以“三公消费”,但老章在这方面不是很注重,不懂得揩政府的油。有一次,黄侃去看望老师,章氏留他一起就餐,黄侃吃饭时发现饭菜实在难以入口,于是怂恿老师换个厨子。谁知章家的厨子是由监视章氏的警察假扮的,此人借机贪报伙食费,黄侃这么一来无意间就断了他的财路,于是下次黄侃再来就被撵出去,黄侃一度气得要以绝食来抗议。
对于黄侃的学生来说,吃喝也是门重要的学问。往往,他们在酒桌上可以跟着老师学到很多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黄侃的学生陆宗达因能抽烟喝酒,深得其喜爱,师徒俩常常在酒桌上论道,有时一顿饭要吃好几个小时,陆宗达自认在这当中受益匪浅。
在好赌方面,黄侃的赌兴在教授里面堪称首屈一指,他在日记中自称“日事蒱博而废诵读”,为了打麻将常常连读书都忘了,这对于普通人寻常不过,但对于嗜书如命的黄侃则是极其不正常的。热爱打麻将的梁启超有句名言“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有人说,黄侃的赌兴堪比梁启超。
好赌成性的黄侃也是一个铁杆的“彩迷”,精通《周易》的他运用卜卦的办法演算爻位与彩票的关系,居然还真的因此中了大奖。据刘成禺的《世载堂杂忆》记载,黄侃在中央大学执教时,某日卜得一个“三上上”的卦,他当天以此卦象买了一张券值五元的全张彩票,没想到竟中了头奖。虽然书中没有具体说明中奖金额,但黄侃用这笔钱在南京蓝家庄购买了一处大宅子,并按照自己的设计推倒重建,可见彩金着实不少。
当然,跟以上几点比起来,黄侃一生中最为人诟病的无疑还是好色这一点。
有人说,黄侃一生中结婚达九次之多,这未免有点夸张,但是黄侃一生中有案可查的婚恋史至少好几段。黄侃的结发妻子姓王,双方的出身可以算是门当户对,两人于1903年成婚,只可惜婚后三年黄侃就远赴东洋游学,两人聚少离多,因此缺少共同语言。王氏为黄侃生下一子三女,她一直以相夫教子为己任,直到1916年郁郁而终。
1913年,黄侃在上海创办《民声日报》时,和一个名叫黄绍兰的女孩久别重逢,并上演了一出“诈婚”的戏。黄绍兰小的时候,黄侃曾当过她的家庭教师,只不过那时黄绍兰还是一个小丫头片子,现在已经出落成楚楚动人的大姑娘了。黄侃见了黄绍兰的美貌,不顾师生关系主动追求,单纯的黄绍兰很快防线动摇,但是她知道黄侃是有妻室之人,对两人的结合深感犹豫。
黄侃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他提出要与黄绍兰办理结婚证书,但是又以王氏不肯离婚加上自己不能抛弃发妻为由,说结婚证上自己只能用李某某的假名,以免犯重婚罪。黄绍兰见黄侃如此重情重义,又肯为了自己不顾一切,恋爱中的女人智商容易变低,一感动之下就答应他了。
未承想,不久之后黄侃到北京教书,又与一个叫彭欣缃的女学生好上了。黄绍兰知道后如五雷轰顶,这才醒悟当初中了这厮的奸计了,结婚证上男方用的是假名,现在就是闹上法院也无济于事啊。这个时候,黄绍兰已经怀有身孕了,几个月后她为黄侃生下一女,但这并没能让负心郎浪子回头。更可悲的是,黄绍兰的父亲恨她辱没家风,一怒之下,与她断绝了父女关系。
黄绍兰后来投入章太炎门下,成了章氏唯一的女弟子,黄侃的师妹。章夫人汤国梨很同情黄绍兰的遭遇,曾在笔下痛骂黄侃“有文无行”、“无耻之尤”。黄侃死后12年,黄绍兰终于因精神崩溃自缢而死。
而那位名叫彭欣缃的女学生要比黄绍兰稍微幸运一点,因为那时黄侃的原配王氏已经故去了,所以她跟黄侃结婚时黄侃用的是真名。然而,彭欣缃在为黄侃生下两个儿子后,两人还是走向了离婚的结局。
黄侃最后一段婚恋故事的女主角叫黄菊英。1919年,黄侃在武昌高师任教,同时在湖北女师兼课,他的大女儿黄念春也在女师读书,黄念春的同窗好友黄菊英常来黄家串门。芳龄正当二八年华的黄菊英长得亭亭玉立,这一来又触动了黄侃老牛吃嫩草的心思。黄侃不愧为情场高手,且看他为黄菊英所填的这首《采桑子》:
今生未必重相见,遥计他生,谁信他生?缥缈缠绵一种情。
当时留恋成何济?知有飘零,毕竟飘零,便是飘零也感卿。
那个年代的女孩子不像现在只爱“高帅富”,像黄侃这样才华横溢且懂得浪漫的成熟男人最容易被少女青睐。这样一来二去,黄菊英居然不顾家里“同姓不婚”的强烈反对,坚决跟这个可以当自己爸爸的男人走在一起了。
1923年,黄侃与黄菊英正式对外宣布结婚,消息一出,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祝福者固然有之,但更多的是对黄侃罔视斯文、伤风败俗的非议与谴责。不过,“人言可畏”在黄侃这里可起不了什么作用,他干脆让学生把骂自己的小报收集起来,以供蜜月消遣。
不知道是黄侃老了、累了,还是改邪归正了,这一次婚姻后他居然一改朝三暮四的坏习惯,夫妻两人十分恩爱,而黄菊英也陪伴黄侃走过了人生中的最后十几年。
黄侃常将自己与老师章太炎的关系比作柏拉图与苏格拉底,这不仅体现在学问的传承,还在于两人审美的区别。黄侃认为章氏像苏格拉底一样不是很在乎表面上的美丑,而自己却如柏拉图般追求美,因此总觉得老师无法理解自己的风流韵事。后来有一次,章太炎问黄侃:“妇人身上何处最美?”黄侃反问老师以为何如,章太炎说:“以我观之,妇人之美,实在双目。”黄侃笑道:“都说先生痴,据此来看,先生哪里痴呢!”
事实上,章太炎直到耄耋之年,谈到黄侃时仍然不忘为其辩护:“恐世人忘其闳美而以绳墨格之,则斯人或无以自解也。”章太炎担心世人以俗礼来看待黄侃,过分纠结于其人品,而忽略了他在学术上的宏大与壮美,可谓用心良苦。
革命家与学问家
虽然黄侃在私人问题上有很多让人诟病的地方,但身处那样一个乱世,他始终以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要求自己,并一生保持着崇高的气节,这一点,是任何人都无法否定的。
黄侃的生母是其父的小老婆,庶出的身份加上少年丧父,使得黄侃在人生成长的道路上备受歧视,几乎因此失学。因此,黄侃从小就具备了比常人更强烈的反抗意识和革命精神。
黄侃娶王氏时,有一回去丈人家,对方有人表现出了对他庶出身份的鄙视,黄侃一怒之下蹲到他丈人家的紫檀木椅上,裤子一脱,当场拉了泡屎在上面。后来黄侃去考秀才,看到另外一个考试的人,大概是富二代,连考试都不忘享受,居然在考场里架口锅,弄只鸭子在那里煮起来了。黄侃一见,火冒三丈,等到鸭子煮熟了马上要起锅的时候,他冷不丁过去,飞起一脚,把鸭子连锅给踹翻了,汤水撒了一地。那人急红了眼,揪住黄侃就打,黄侃挨了揍,心里却很开心,他说:“甭管你怎么样,反正今儿这鸭子你是吃不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