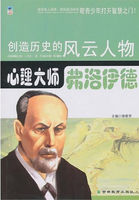维新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期间很快学会了日文,有人说用了半个多月,有说一个星期,甚至有说他在船上一夜便通日文。虽然中国人学日文并不太难,但这个速度也足以让人吃惊了。到了梁氏四十七岁游历欧洲时,还跟丁文江学习英文,丁文江对他进步的神速深感惊异。
不过,相对梁氏的天才,其勤奋更让学生印象深刻。
梁启超生活极有规律,无论冬夏,五点起床,每天工作十个小时,连星期天都不休息。他晚年讲学之余笔耕不辍,学生劝他说:“先生年事已高,应该保重身体,不要过度操劳。”他回答道:“假我十年以读史,可以无大过矣。苟其不然,鞠躬尽瘁而已,亦复何憾!”他经常以“万恶懒为首,百行勤为先”来勉励自己的学生。
直到临终前,梁启超仍然不愿意接受学生的好意停止工作,他对谢国桢和萧龙友等人讲:“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1982年,谢国桢因病住院,仍坚持看书,萧龙友之子萧璋去探望他,劝他放下书本,好好休息,谢国桢道:“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坛,师训不可违!”
梁启超并不是一味讲究勤学苦学的人,他认为读书治学要有方法,这个方法就是“趣味主义”。1922年,梁启超在天津讲演时说:“假如有人问我,你信仰的什么主义?我便答道:我信仰的是趣味主义。有人问我,你的人生观拿什么做根柢?我便答道:拿趣味做根柢。我生平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总是做得津津有味,而且兴会淋漓,什么悲观咧,厌世咧,这种字眼,我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我所做的事常常失败,但我不仅从成功里感到趣味,就是在失败里也感到趣味。”
说到趣味,梁启超最大的乐趣应该是打麻将,梁氏对麻将非常痴迷,他有一句名言:“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有一次,几个朋友约梁启超某天去讲演,他说:“你们定的时间我恰好有四人功课。”原来这一天梁氏恰好有牌局,只好辜负朋友了。
梁启超的厉害之处在于他打麻将不耽误正事,据说他可以一边打麻将,一边让秘书在旁边听他口述文章,时人称他有“五官并用”的功夫——堪比金庸《射雕英雄传》中老顽童周伯通的“分心二用”。另外,梁启超的很多长文都是在他打完麻将之后写成的,他自己笑称这是利用牌局起“腹稿”。梁启超的着名讨袁檄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就是在牌局后写成的,一共九千多字,无一删改。
由于分心的缘故,梁启超打麻将总是输多赢少,但没事,他输得起。以他在清华研究院时为例,月薪400大洋,北洋政府的补助两倍于这个数,加起来已经1200大洋了(相当于现在的十来万人民币了)。梁启超的稿费是当时最高的,商务印书馆给他的标准是每千字20元,其稿费收入肯定不低于从政府领取的薪金。此外,梁启超晚年还卖字,每个大字8元,每月卖字可得两三千,这笔钱用来维持北平松坡图书馆的开支。曾经在北洋政府担任财长的梁启超理财能力也不错,他还投资过股票,收益颇丰。所以梁氏打麻将赚的是心情,其他人可以借机揩油,大家可谓双赢。
而有梁启超这样的老师做榜样,学生读书一定不会觉得无趣。
梁启超的博学总是能让学生大开眼界。有个故事足以证明梁氏的博学,据刘海粟回忆,一次徐志摩请客,梁启超、闻一多、胡适、王梦白等人赴宴。席间,胡适说:“中国古诗很多,诗人都吃肉,就是没有人写过猪。这个牲畜没有入过诗。”他人都沉默,只有梁启超摇头道:“不见得,清朝乾隆就写过‘夕阳芳草见游猪’的句子。”众人听完都感叹梁氏学问无涯,因为乾隆一生诗作无数,但只有数量没有质量,且多枪手之作,极少有人把他的诗当回事。
梁氏尽管博学,却从不以此为傲,相反,他总是教育学生学问要“专精”,他写诗告诫学生“吾学病爱博,用是浅且芜”。当然,梁启超所谓的“专精”是要在具备最基本的人文素养的基础上,否则就会沦为学科的机械工具。梁启超曾给清华大学学生开设国学入门书目,其中把四书五经、诸子、前四史、《资治通鉴》、《文选》以及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白居易等人的集子,凡三十余种作为大学生“最低限度”应读之书,认为这些书“无论学矿、学工程学……皆须一读。若并此未读,真不能认为中国学人矣”。
如果按照梁启超的标准,我敢保证现在的中国没有几个学人。这些“最低限度”的书,就是现在中文系的学生,也没有几个读全(很多人可能一本都没读全),更遑论那些最低限度以外的书。遥想以前的学人,就连华罗庚、钱三强这样纯理工科出身的人,诗词歌赋样样精通,人文素养何其之高,再看看现在,神州人文精神的没落可见一斑了。
课余跟学生在一起时,梁启超总是不乏幽默。1922年,梁启超在北京法政专门学校讲授“先秦政治思想史”,同学给他起了个外号“老博士”,这个“博士”指的是先秦时期明一艺通一经堪称国之大老的人,加一个“老”字以示古今之别。梁启超听说后,问学生:“你们怎么叫我‘老博士’,我觉得自己还年轻。”学生详解“老博士”之意,并说:“如果先生不喜欢‘老博士’,可以换个名称,叫‘先秦博士’,您不是正在给我们上“先秦政治思想史”吗?”梁启超笑道:“‘先秦博士’不敢当,但可以加一个‘准’字,叫我‘准先秦博士’,这样岂不是更好玩?”说完,师生相对大笑。
但是梁启超该严肃的时刻也不马虎。梁氏的爱徒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时,请老师做证婚人,梁氏对徐志摩离婚再娶很不满意,碍于情面才勉强答应。到了婚礼上,梁氏证婚的方式别出一格,把徐志摩劈头盖脸一顿痛骂:“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又用情不专,所以你再婚再娶。以后务必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我送你们一句话,祝你们这是最后一次结婚。”满堂宾客面面相觑,徐志摩不得不求饶:“给学生留点面子吧。”
其实,不管是幽默也好,严肃也好,都是梁启超为人真诚、关爱学生的一个表现,这也是他深受学生爱戴的原因。
多情之人
事实上,据很多学生回忆,梁启超的口才并不好,不能与他的笔才形成正比,最要命的是他那一口广东官话,实在难以听懂。梁启超最大的特点在于他的热情与激情,他自己也说:“我是感情最富的人,我对于我的感情都不肯压抑,听其尽量发展。”梁启超龙卷风一样的情感让身边的人无不卷入其中,被其感染,自然都生机勃勃,成了他笔下的中国少年。
傅斯年曾经劝胡适:“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梁启超一生在政坛几起几落,几次入阁,几组政党,但他一生最大的功绩还在于办报。梁启超办报以1896年《时务报》到1906年《新民丛报》这十年为全盛期,这期间他发表的一系列文章被时人称为“新文体”。梁启超将散文作为宣传变法的工具,他的文章打破了旧有散文的窠臼,亦文亦白,亦庄亦谐,完全凭借感情推动文字奔跑,如飞瀑从天而降,雷霆万钧,汪洋恣肆,一泻千里,令人难以阻挡其冲击,“每一文出,则全国之身目为之一耸”。
梁启超在演讲中称杜甫为“情圣”,让人耳目一新,他认为老杜诗中字字含情,中国文学界写情圣手没有人比得上老杜。其实,若以此而论,梁启超自己也是清末民初一个大情圣,他用自己充满“魔力”的文字打动并激励了一代人,正如梁启超自己所说:“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禅。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当时的青年人,几乎没有不受梁启超影响的。中国人被称为“东亚病夫”,精神之病尤甚于肉体,而梁启超的文章,无异于一剂治病的良药,诵之读之,使人精神焕发,斗志昂扬。青年陈独秀、******、******、胡适都深受梁启超的影响,1912年,还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在日记中写道:“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此二语唯梁氏可以当之无愧。”
而对自己的成就,梁启超也颇为自负,他曾对人说:“没有袁世凯,中国的历史不是如此;没有梁启超,中国的历史也不是如此。”梁氏清华弟子、史学家黎东方对此用四个字评价——“当之无愧”。
梁启超写文章常一气呵成,他写《南海康先生传》,凡二万余言,笔走龙蛇,仅用了四十八分钟就写完。他精力过人,习惯夜间写作,常彻夜不眠,他自述写《戴东原哲学》洋洋数万言,不眠不休连续奋战三十四个小时一口气写完。
有时候,连梁启超自己都无法控制自己的笔端。1918年,梁启超和蒋百里一起游历欧洲。蒋百里回国后写了一本《欧洲文艺复兴史》,请梁启超作序。没想到梁启超下笔后一发不可收,一写就是五万余言,比蒋百里的正文还要长。最后,梁启超自己都不好意思,只好将这篇序言单独成书出版,反过来请蒋百里写序,这就是着名的《清代学术概论》一书。后来,梁启超又将此书扩充为二十五万字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梁启超的多情当然不仅仅在他的文字中,他对于家人、朋友、老师、学生莫不投入了真挚的感情。
梁启超的发妻李蕙仙比他大四岁,完婚后两人始终恩爱如初,琴瑟和谐。李蕙仙出身名门,屈身下嫁,却丝毫没有大小姐的娇气,结婚后相夫教子,安于清贫,在梁启超落难之时不离不弃,慷慨支持丈夫的事业;缺点是性格过于严肃,令人生畏。但梁启超始终爱之、敬之,两人一生竟只吵过一次架。
1924年的初秋,李蕙仙因患乳腺癌去世,梁启超写下了悲痛的《祭梁夫人文》曰:“我德有阙,君实匡之;我生多难,君扶将之;我有疑事,君榷君商;我有赏心,君写君藏;我有幽忧,君噢使康;我劳於外,君煦使忘;我唱君和,我揄君扬;今我失君,只影彷徨。”据杨鸿烈回忆:夫人去世时,梁氏身穿孝服,从回回营步行好几里远路直到宣武城外法源寺回灵,涕泪纵横,可见伉俪情深,老而弥笃。
除了妻子之外,梁启超还有一妾,名唤王桂荃,系李蕙仙带来的陪嫁丫鬟,1903年,王桂荃在李蕙仙主持下成为梁启超的侧室。由于梁启超对外倡导一夫一妻制,自己却享齐人之福,因此王桂荃的身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一个隐秘,直到李蕙仙病逝后方才被扶正。王桂荃性格温顺贤良,为梁氏生了六个子女,梁氏一家都很敬重她。
梁启超的生命中还有一次出名的艳遇。
1899年底,梁启超到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在此他邂逅了保皇会中一位何姓侨商的女儿何惠珍。何小姐芳龄二十,美丽高雅,从小接受西方教育,操一口漂亮流利的英语,她仰慕梁启超的文章人品,曾在报上匿名用英文为梁启超撰文辩护。梁启超在檀香山宣传自己的改良主张的时候,何惠珍在他身边担任翻译,两人配合非常默契,情愫渐长。
受西方教育的何小姐少了几分中国女孩的含蓄,她大胆向梁启超表白自己的爱慕之情,当知道梁启超已经结婚后,甚至表示自己愿意做小,只要能跟梁氏在一起就可以了。梁启超又是幸福又是苦恼,他给自己的妻子写了一封信,把情况告诉她。李蕙仙回信竟然劝梁启超娶何小姐为妾,她也觉得有这样一位精通英文、知书达理的贤内助,对梁启超的事业将会是很大的帮助。
妻子的贤惠让梁启超更感惭愧,他思来想去,最终还是忍痛拒绝了何小姐。他提笔为何惠珍写了一首诗:“一夫一妻世界会,我与浏阳实创之。尊重公权割私爱,须将身做后人师。”数日后,梁启超将自己的小像赠与何惠珍,何惠珍回赠亲手织绣的两把精美小扇,两人含泪而别。梁启超自称活了二十几年,从未对一个女孩如此心动,“几乎不能自持”,这次分别想必对他也是刻骨铭心的。
梁启超共育有五子四女,九个子女个个成才,其中出了三个院士,堪称佳话。梁启超十分疼爱自己的儿女,在他去世前的六年间,他有五个子女在国外求学。梁启超非常想念他们,不断地给他们写信,每封信都充满父亲对子女真挚的爱。在信中梁启超称他们是“大宝贝思顺”,“小宝贝庄庄”,“那两个不甚宝贝的好乖乖”,“对岸一大群孩子们”,“一群大大小小的孩子们”。从这些称呼中,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他对孩子们那种浓烈的父爱。
日常生活中,梁启超能够细致入微地掌握每个孩子的特点,因材施教,引导自己的孩子往自己感兴趣的道路上发展,并为之作出妥善的安排。他很重视培养孩子的实践能力,在孩子面前从来不说教和指责,总是以鼓励的方式让他们战胜挫折。在知识训练之外,梁启超也注意孩子的道德培养,让他们养成艰苦朴素的作风以及热爱生活的乐观精神。
同样的,梁启超对自己的学生也是爱护有加。蔡锷将军是梁启超在长沙时务学堂时的学生,两人感情甚笃。戊戌政变后,蔡锷追随梁启超到日本学习和生活了六年,后来两人又曾一起密谋倒袁。蔡锷英年早逝后,梁启超十分悲痛,他称蔡锷为“再造民国之伟大人物”,在上海为爱徒举办了公祭与私祭,1923年又倡议在京创办了松坡图书馆,自任馆长。在梁氏“饮冰室”书斋的显要位置,也悬挂着他请人绘制的蔡锷戎装油画像。
梁启超入清华国学院时,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大师了,但他跟学生的距离并没有因此拉远,他对青年学子的关怀与照顾让很多人感激涕零。当时清华研究院的学生都是自费上学,梁启超了解到有些学生生活困难,就安排他们去松坡图书馆编目录。王力、刘节等人都做过这项美差,每月可得二三十元,周传儒有个兄弟也在北京读书,费用很大,梁启超让他当总负责人,每月可得五六十元。当然,这笔钱都是从梁启超的私人腰包里出的。
周传儒毕业后到商务印书馆当编辑,月薪80元,已经是中产阶级了,但梁启超仍然觉得弟子工资微薄,于是介绍他到暨南大学当副教授,月薪200元,一年后周又升为教授——暨大校长是梁启超在万木草堂的同学。
在“饮冰室”书斋旁,梁启超自建三层欧式藏书楼一座,内有藏书十余万卷。大多爱书如命的人都不喜欢把自己的藏书轻易给别人看,但是梁启超却允许自己的学生们自由浏览其藏书,就连一些珍本孤本也不介意学生借出。梁启超甚至还把一些价值不菲的珍本送给了自己的得意门生。
谢国桢毕业于清华研究院后,又在梁家跟任公学习了一段时间,兼当梁家的家庭教师。一年后,梁启超推荐谢国桢到南开中学高中部任教。临行前,梁氏以自己珍藏的《宋拓游相本纯化阁帖》相赠,此帖极珍贵,上海书店曾借去影印,梁启超都不舍得。另外一个学生余永梁作了几篇关于甲骨文的考释,梁启超很是欣赏,把自己所藏的《殷墟书契》全套送给了他,勉励他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