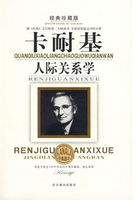金岳霖头一次养的鸡是从北京庙会上买来的一对黑狼山鸡。在老金的精心呵护下,没多久公鸡已经长到了9斤4两,母鸡也超过了9斤。冬天来了,老金担心它们受冻,看到书上说可以喂点鱼肝油御寒,他就用灌墨水笔的管子灌了它们一管子的鱼肝油。结果,这两只宝贝鸡很快就在窝里寿终正寝了。
后来,老金又养了一只云南斗鸡。这只公鸡能把脖子伸上来,和老金在一个桌子吃饭,老金与鸡平等共餐,安之若素。晋朝的阮咸曾经与猪一起喝酒,这又是老金魏晋风度的一个表现。偶尔,金岳霖会带着大公鸡出去溜达,引来很多路人围观,但鸡不在乎,老金也不在乎。
据赵元任的夫人杨步伟回忆,有一次她接到老金的一个紧急电话,让她赶快进城。杨步伟问什么事,老金支支吾吾,只是让她越快越好。当时老金正跟秦丽琳热恋,杨步伟以为是秦丽琳怀孕了,一路忐忑。到了金家,杨步伟才知道这件事跟秦丽琳无关。
原来,金岳霖养了一只母鸡,最近反常地连续三天不下一个蛋。老金担心鸡难产,赶紧请东京帝国大学医科博士毕业的杨步伟过来看一看。杨步伟听了之后又好气又好笑,把鸡抓来一看,原来老金经常给鸡喂鱼肝油,以至于这只鸡营养过剩,鸡蛋卡在屁股眼出不来。杨步伟伸手一掏,问题马上解决。金岳霖一见,欣喜不已,为表感谢,他特地邀请杨步伟一家去吃烤鸭。
贪玩的金岳霖像小孩子一样率性天真,我行我素,因此,也闹了不少笑话。
有一天,梁思成看到金岳霖的厨师外出采购,手捏一张5000余元的人民币活期存折,大为惊讶。在20世纪60年代,5000多块可是一笔巨款。梁思成忙问金岳霖缘由,老金答:“这样方便。”梁思成说:“若不慎遗失,岂不是很冤枉﹖”老金还是说:“这样方便。”梁思成只好跟他建议:“这样吧,存个死期,存个活期,两全其美,而且‘死期’利率高于‘活期’……”谁知金岳霖连连摆手:“使不得的,本无奉献,那样岂不占了国家便宜﹖”梁思成无可奈何,只得详细为他解释储蓄规则,金岳霖这才理解了,满脸笑容,对梁思成说:“你真聪明。”
没想到,到了“改存”之日金岳霖又打起了退堂鼓。原来他预备在自己死后留1000元钱给自己的厨师,他想:“如果将剩余的钱都存了死期,万一某日我突然死了,钱不就取不出了﹖”这下梁思成哭笑不得,只好又将如何把那1000元抽出为厨师另立户头之事细细为他讲了一番。金岳霖听完之后恍然大悟,喜作一团,竖起大拇指对梁思成说:“你真聪明。”据说,梁思成经常从金岳霖的嘴里得到这样的夸奖。
还有一次,三伏天,几位友人到金家串门,一进门,看见老金愁容满面,连连拱手,说:“这个忙大家一定要帮啊。”友人不知何事,但是念及老金一个独身老头儿实在可怜,便个个拍着胸脯做英雄状慷慨允诺。一会儿,老金的厨师为每个人盛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牛奶……原来,金岳霖冬天爱喝牛奶,订了好多瓶,他不懂得变通,以为订牛奶也要“从一而终”,到了夏天他饮量大减,天热又容易变质,于是出现了以上这一幕。
当时牛奶还是奢侈品,也只有老金这种拿着一级教授工资的单身汉才能经常消费,大家揩老金的油,几天后又来喝了一次牛奶。幸有一位好心人知道后,告诉老金牛奶订量可以自己做主,冬天多订,夏天少订。老金听完后大大地佩服,称赞他:“你真聪明!”
老金虽然像孩子一样天真,胸无城府,但是有些事绝对不是单单“天真”两个字可以衡量的。
晚年的老金工资虽然高,但是每个月下来却很难盈余,因为他的钱除去生活费外,还要交党费,寄回老家一些,付保姆、厨师和拉车师傅的工资。最令人惊异的是,老金竟然连厨师和拉车师傅的退休金都预备下了,老金认为自己给这两位师傅终身工资,既可以减轻国家的负担,又可以保证两位老人家晚年的生活。后来,这两位师傅果然领着老金的钱直到去世为止。
这就是金岳霖,身为逻辑学大师,却总是干着不符合逻辑的事情。逻辑是最为理性的学科,而老金却是最为感性的人,感性得让我们感动。
亦师亦友
作为老师,金岳霖给学生留下的深刻印象从第一面就开始了。留学归来的他总是一副英国绅士的派头,他身材高大却永远腰板笔挺,喜欢穿夹克,有时也西装革履,皮鞋擦得油光可鉴,上面绝对不会有灰尘,走路时,一定微仰着头。他夏天穿短裤一定要配上长筒袜,因为在当时看来,绅士穿短裤必须配长袜。不过也许是回来久了,老金的装束也开始走向中西合璧,冬天他会在西装外面套个中式长袍。
在西南联大教书时,金岳霖最引人注目的还是那顶不论冬夏都要戴在头上的遮阳帽,原来老金眼睛怕强光,只好一年四季戴帽子,这也成了联大一怪。据汪曾祺回忆,有一段时间老金还配了一副眼镜,一片镜片是白的,一片是黑的,这就更怪了,后来在美国把眼睛治好了一些,这才没有戴。每当新学年开始,老金在课堂上和新生见面,他的第一句话总是:“我的眼睛有毛病,不能摘帽子,并不是对你们不尊重,请原谅。”
不过,老金上课可比他的穿着随便多了,他的学生任继愈回忆说:“教授没有像他那么随便的。”
金岳霖上课不带书本和讲稿,因为这些早已在心中,他甚至很少写字,粉笔对他基本是多余的。他喜欢在讲坛上走来走去,有时候干脆就坐在教桌上面对着大家,在那里讲课。
老金讲课深入浅出,他最擅长引用生活中的例子来证明自己的观点,那些枯燥的理论经过他的嘴巴就变得生动有趣,令人着迷。比如讲排中律的时候,他在课前闭着眼睛随手一指,问同学们:“这里是桌子,或者不是桌子,你们说对不对?”学生争相回答,课堂气氛就活跃了起来。
在授课时,金岳霖把学生看作和自己同等地位的人。老金的得意弟子王浩,后来成为世界著名的数理逻辑学家,在牛津、哈佛等名校执教过。据汪曾祺回忆,老金曾开设一门选修课“符号逻辑”,对很多人来说,去听课就如去听天书。只有王浩懂得其中的奥妙。老金经常会在上课过程中停下来,问:“王浩,你以为如何?”于是这堂课就成了师生二人的对话。
金岳霖的学生王雨田回忆说:“金先生的讲课是讨论式的,不是填鸭式的,他边讲便提问,师生之间不时展开热烈的争辩。”金岳霖听不清楚发言时,会把右手放在耳边以示自己认真听,听到高兴时,他会从椅子上一下子站起来,大喊一声。老金在课上提问时常常不按章法,有时他一上课就宣布:“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这时所有穿红衣的女同学心里都唱起了《忐忑》,但又有点兴奋。轮到穿蓝毛衣、黄毛衣的女同学亦然。
金岳霖最大的优点是能够鼓励和容纳学生不同的见解。在一次逻辑讨论会上,有人提到了当时享有盛名的哥德尔的一本书,金岳霖很感兴趣,说要买来看看。他的大弟子沈有鼎在旁边对他说:“老实说,你看不懂的。”老金闻言并不生气,神态自然,只说:“那就算了。”金岳霖另外一个弟子,后来去了台湾的大思想家殷海光在一旁听到他们师生二人的对话,大为吃惊:原来师生之间竟可以这样相处!这件事对殷海光的成长触动很大。
据刘培育回忆,20世纪50年代的北京大学哲学系,逻辑教研室开会总是争辩最多的,金岳霖-沈有鼎-周礼全三代师生间经常争得面红耳赤,声音高昂,为此常常遭到同仁抗议他们“声音污染”。不过这并不影响师生之间的关系,他们相信真理愈辩愈明。
事实上,老金从来不把自己当成权威,他自己也不迷信权威,老金早期每堂课必讲休谟,但他并没有因此完全被休谟俘虏,他从学习休谟走上了怀疑休谟之路,进而走上了否定怀疑主义之路,他的大作《论道》就是怀疑休谟的成果。这个比胡适要强,唐德刚在《胡适口述自传》批判胡适虽然一辈子鼓励人家怀疑,但他自己却终生无条件地服膺杜威的学说。
金岳霖对学生的影响不仅仅在课堂内,更在课堂之外。
金岳霖对学问的专注与热爱使他的学生有机会近距离感受榜样的力量。从在清华教书时,金岳霖便养成了习惯,不上课时,他会腾出专门的时间用来做学问。这个时间内,他谢绝一切客人,犹如闭关修炼的高人一样,外面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
后来,金岳霖把这个习惯带到了西南联大,结果差点为此丢了命。1938年9月28日,日本飞机空袭昆明,当时金岳霖住在联大于昆华师范学校租赁的宿舍楼中。敌机来时,正在闭关修炼的老金浑然不觉,好在他福大命大,联大租赁的三座楼,两座楼都直接中弹,只有他居住的中楼安然无恙。当前后两楼被炸的声浪把金岳霖从思考中惊醒后,他跑出来一看,才发现自己不是笛卡儿说的“我思故我在”,而是几乎我思故我不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