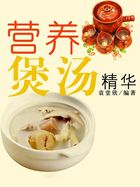屠岸
清晨起身,到户外去呼吸新鲜空气。放眼四眺,只见街心小花园成了白色的塔林,周围是一片银白。寒气凛冽,却没有一丝风。我放慢了脚步,走向了树林。
小树林里有松、柏、槐、杨、柳、核桃、合欢等树。除松柏外,其他各种树木的叶子早已落尽,而枝柯繁密。突然,这些树枝全都成了冰的枝,水晶的柯。而背景则是灰蓝的晴空。一种毛茸茸的冰晶,附着紧裹在每一条树枝上,使整个树林成了一座琼楼玉宇。并没有下雪。这是冰花,水汽花。一位搞气象学的朋友告诉过我,这种奇异的自然现象,是由于气温突降,空中由水汽凝成的雾滴碰到了在零度以下的树枝等纤细的物体时,再次凝结成一种冰晶而形成的。气象上称它为雾凇。也有一种雾凇不经过雾的液态物理过程,直接由气态的水汽凝成固态的冰晶,这一过程叫作凝华。我凝望着这繁密的冰枝所织成的水晶世界,心中问着:这是密度大,附着力强的粒状雾凇即密雾凇呢,还是经过凝华而成的晶状雾凇,又名疏雾凇呢?我对气象学一窍不通。这些名词也是那位朋友告诉我的。
我还不能辨别当前的雾凇属于哪一种。但是,我却喜欢"凝华"这个名词。它是气象上的科学术语,但是它又是多么富有诗意,多么端庄凝重而又闪烁着某种理想光彩的语词啊!我愿意眼前这个奇景就是"凝华"的产物。
我再次凝望着这些玉树琼枝。它们或直指苍昊,或垂顾大地,交叉,横陈,或斜,或挺,或倚,或昂,如织,如射,如伏,如撒,成网,成毂,成突然静止的飞瀑,成死于永恒的火焰。我凝望着它们,凝望着它们。恍惚中,这个雪窟,这个晶殿,似乎在流动,又凝结;在扩散,又聚拢……这是什么?是凝华的过程的再现?是我的幻觉,还是造化赐给我的某种异境?但愿呵,但愿经过凝华,一切灰尘和污垢都会消泯……我想起了另一个凝华。我的思念,徐徐地飞向十一年前的一个冬晨。那时候,夺权,武斗,全国处在****中。我从"牛棚"里走出,奉命打扫院子。我看见院子里的树木,变成了雪枝,冰枝,水晶枝。这世界,似乎变成了一个幻想中的纯洁的世界。我不觉停住了手中的竹扫帚,向着这冰树构成的水晶宫殿发愣。忽然,从冰枝丛中,我见到了一双孩子的眼睛。再仔细一看,哦,是她!一个名叫凝华的小姑娘,那时她八岁。她身穿蓝色棉袄,头上戴着一顶银白色的兔耳大皮帽。
那皮帽的白色线条和冰树枝的白色线条编织在一起,而那一双大眼睛在一片白光中,显得更加乌黑,明亮。尽管,这眼睛又略带惊怕、担忧的神色。她一下子见到了我,眼中现出笑意,但立即迅疾地向我使了一个眼色,把一个纸团塞进了树洞,便悄悄地隐没在树丛深处,不见了。她那向我使眼色的神态,我觉得是超过她年龄的一种神态。这个神态同水晶树枝所构成的白色网连结在一起,永久地刻在我的记忆之中。
那纸团是凝华的母亲给我的一张条子。凝华的父亲原是我的"棚友",但成为"棚友"之前已经是二十几年的朋友了。一个多星期前,他被人们从这里叫去,说是"提审",但始终没有回来。我关心他的命运。我通过一个同情者去向他的爱人打听消息。今天这张字条,就是她的回答。大意是:她的丈夫已经被送到一个地方接受"保护"去了。临去时,他向她表示:严寒只能使他更耐寒,冷酷只能使他更不怕冷。在这污垢遍地的环境里,他将永远保持一个革命者的清白,他相信,一个理想的清白的世界,终将到来。
我当时想,他——一个共产党员,怎么使用起"清白的世界"这样的词儿来了!难道他不要那个红色的世界了吗?他的理想改变了吗?我又想起了当时被当作大毒草来批判的一部电影,它的主题是"认认真真演戏,清清白白做人"。这使我深思。为什么那些人要批这部影片呢?我想了好久,又对照现实,觉得解释只能是:那些高喊"革命"口号的人,其灵魂是龌龊的,是一点也不清白的,因此他们害怕清白。于是我有些明白了,我那位朋友并不是放弃了他的理想。肮脏的手建设不了社会主义,龌龊的灵魂进不了共产主义。不,不仅如此。那些假革命者正在向我们的社会主义大泼污水,要想淹没她!
十一年过去了,我那位朋友早已被落实了政策,不久前被任命为外地某部门的领导人。他离开这里时,我正好出差在外,未能送行,引为憾事。他的女儿凝华已经是十九岁的大姑娘了,在一个街道办的合作社企业里当工人,她爱好文学。一天,我在路上遇见了她,她是那么热情地迎上来,叫我"叔叔"。她那一双乌黑明亮的大眼睛里,闪射着天真热烈的光芒。她的目光使我又想起了十一年前水晶树枝下她向我使眼色的神态。似乎,那时她像个大人,而现在,她倒是个孩子。她说她不久就要和她妈妈离开这里,把户口转到她父亲所在的那个地方去。当我问起她父亲的近况时,她皱起眉来,说:"我爸爸近来特别苦恼。"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她父亲为了整顿党风,要彻查一个走后门搞特殊化的严重事件。
但因为此事牵涉到他那地方上的一位"大人物",因此工作遇到了阻力,暂时进行不下去。在这种情况下,他怎能不苦恼呢?哦,原来如此!我的朋友呵,你不仅要保持一个革命者的清白,而且要用你的手去扫除污垢,打开通向清白世界的道路,但是,这又谈何容易呵!
我,仍然站立在小树林里。我凝望着眼前的奇景——"凝华"的产物。那一边,有好几棵松树,那一簇簇松针,像是一丛丛绽开的银白色的菊花,而菊瓣则是如恣意地辐射着的白光。几株幼松,谦虚地偎在老松的一侧。远远望去,似乎树上开满了怒放着的洁白的梅花,梅瓣则是白璧雕成的晶体。这些松枝,同柏枝、杨枝、柳枝、槐枝、核桃树枝、合欢树枝,交错在一起,连成一片。太阳出来了。阳光照射到树枝上,这些水晶树枝被映衬在朝阳喷出的光流里,如镶上透明的金色光边。纯白幻成七彩,绚丽,跃动,令人炫目。呵,这是谁的大手笔呵,写出了如此晶莹璀璨的大块文章!
我忽有所感,回到屋内,伏案,悄然凝思,提笔疾书,旋又修改多次,最后写成了一首诗:
银梅玉菊出青穹,万树梨花一瞬中。
白璧雕来新世界,水晶琢透旧时空。
寒严苞绽蕊争吐,温降枝繁花更。
清白文章谁写得?
凝华端赖大毫锋!
叫什么题目呢?先写了一个:《树挂》。树挂就是老百姓对雾凇的称呼。但,不满意。几经推敲,改题为《凝华》。于是,又写了一封短信给凝华姑娘。信上说:"我写了一首诗,请你这个文学爱好者看看,提提意见,然后请你把它带交给你的父亲。自从你那天告诉了我你父亲的苦恼之后,我曾想抄一首明代爱国者于谦的《石灰吟》诗赠给他,那诗是这样的:"千锤万击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全不惜,要留清白在人间。"这是一首多么激动人心的诗!今天我看到了自然界的清白世界,有所触发。我想,还得我自己动手来写一首诗,赠给你的父亲。这就是附上的这首诗。也许,这更能表达我作为一个老朋友对你父亲的由衷的敬意和热烈的期待。"我拿着贴好邮票的信,走出屋门,踏着小径,走过街心花园,走过小树林——走在这银白色的环境里,走向邮筒,那戴着一顶闪亮的霜帽的绿色邮筒。
1979年9月
(原载《清明》197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