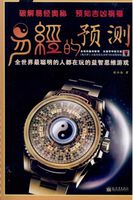你知道的,这世上愿意容忍你干蠢事的人,不多的。
数年前一个阴霾天儿,钢蓝色暮霭黄昏,我趴在江苏路一间写字楼的办公桌上。
手边百合将谢,散发出奇香和奇臭的混合气味来。
打电话给他,“我不想活了呢。”
“为什么呀?”他说。
“很累,每天工作12小时;男朋友完全不明白我的心;还有,我就快缴不出房租了。”
他呵呵笑,“你这就活不下去了?”
“嗯。”
“我能帮忙吗?”
“嫁给你,好吗?”
“好。如果我健康。”
我不知道我的笔是不是能够写出那种感受——特别是我现在这种心情下——获知他已离去——也许认识他的人会看到鼻酸——不认识的朋友会觉得我无病呻吟了些吧——我到底要用多少个破折号——
好吧,简练些。
他叫朱邵华,笔名竹子,是我父母以外,第一个愿意容忍我说蠢话、干蠢事的人。
那会子我刚开始猛写中长篇小说,在榕树下投稿。起初是投着玩,没想到居然有人喜欢我的文字。嗯,我也有那所谓的虚荣心。看人家留言讨论我笔下的人物,是很有趣、很满足虚荣心的事情。
发表《逍遥游》这一篇时,突然有一个读者,这样评价,“没细看,太罗嗦。”
突然又有一个编辑,这样回复。“楼下你有认真看全文吗?这是我难得一见的好文,文字简练故事精彩一气呵成。我们当为现如今还有焱阳这样会讲故事的作家而庆幸。”
这个编辑,就是竹子。
这是他第一次,像溺爱妹妹的哥哥一样,为任何细枝末节、不由分说地为我挡去污泥或是批评。
对于一个写了十多年、从未出版过、以及从未被人正面如此肯定的女生来说——漫漫长夜的笔耕不辍,都不及这一句维护——即便不合理——更能让我鼻酸。
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我们开始在网上聊天。
偶尔聊起音乐,我说,“《龙宽九段》的音乐不错哦。”
他顿一顿,说,“嗯,我没法听。”
我说,“你可以给电脑装一个音箱啊。”
他答,“懒。”
又有一天,我们共同的朋友唐挺(白江)和我聊起他,告诉我,“你知道竹子身患绝症么?”
我……
各种不可置信啊!
赶紧上网找他。
“你不能走路?”
“啊,你知道了?我甚至不能坐呢。”
“那你怎么打字?”
“绑在椅子上,就这样,对着电脑,一个键一个键地敲。你老嫌我慢嘛。”
“那你怎么从不说起?”
“说这个干什么呢。”
“……好吧……”
关掉看似平静的对话框我却没法子平静啊。拜托!鬼才能平静啊!
我一定要去见他,不然怎么能够安然无恙?
“亲爱的乘客,我们的飞机马上就要抵达武夷山机场。预计抵达时间早上7点55分,现在的地面温度是30摄氏度。Ladiesandgentlemen……”
和很多人相反,我把保险带系得更紧了,让自己整个人陷落到椅背里,等待着飞机轮亲吻跑道的那一下轻微而幸福的撞击。
上飞机前的晚上才临时决定要来,所以,只来得及告诉雨巷。对竹子是撒了小谎的,倒不是希望给他一个惊喜(我估计是惊大过喜来着),而是担心又像上次那样,临时出问题来不了,搞得人家小心肝扑通扑通。
刚下飞机,还没分清楚东南西北,一个男人上来问,“小姐要车吗?桑塔纳。”
我记得竹子之前帮我查过从武夷山机场到他家,如果包车的话需要200块钱左右,便试探性地回答,“去晒口。不过,我身上可没有什么钱。”
比较巧合的是,我穿了一条“淑女屋”的黑色裙子,脸上又挂了一个很无辜的笑容。所以司机大哥大概突然想到了他多年未见在外打工的小妹妹,叹口气,“算了,反正这两天还没到旺季,我闲着也是闲着,只收你油费,好吧?180块。”
我二话没说,拎着行李就上车。出门得见这么爽气的贵人,还还什么价?再说天热得紧,再讨价还价我要中暑了。
一路过去,两个人渐渐聊开来。原来司机姓周,也在上海做过生意。提起上海,口气十分唏嘘,“上海滩,好地方,土地矜贵,是武夷山的10倍……”
我说,“周大哥(嘴甜吧),等一下你要空车放回去,真不好意思。”
他说,“没事。”笑一笑,黑黑的脸容很坦诚。
真好。如果一个男人懂得赚钱之余,又懂得什么叫做无所谓,至少可以得到一半以上女性的芳心。
渐渐的山路开始崎岖,但是满眼翠绿,倒叫我惊喜了一把。沿路经过一个个小镇,远远看着,都在崇山峻岭环抱之中。
实在忐忑,打个电话到竹子家揭穿谜底。
“竹子?起床了么?吃早点没?”
“阳阳?巧了,今天我起得特别早,6点多就爬起来了。”
我心想还真是心有灵犀呢。不过我比竹子更早,为了赶早班飞机,5点钟就努力睁大惺忪睡眼刷牙洗脸。
“早点都吃什么啦呀?”
“稀饭,哦,泡饭。”
“有没有剩?”
竹子笑得十分阴险(哼叫你阴险,5秒钟后保证你哭都哭不出来),“连冰箱都洗了,你说有没有剩?”
“啊,那我吃什么呀,我还没吃早点,饿着呢。”
“那怎么办?我空运早点给你?”
“不用空运,我过来吃。”
竹子的笑声戛然而止(我却终于忍不住开始哈哈大笑),忽然非常惊恐的样子,“你现在在哪里?”
我看看窗外,很迷茫地问周大哥,“大哥我们在哪里?”
周大哥也确认一下,“离晒口还有半小时吧。”
于是我回答,“哦,竹子,30分钟以后到你家。”
30分钟以后,我先见到的是竹子的爸爸,老人家怕我找不到,满脸笑容的出来迎接我。
甫进门,又听见的是竹子妈妈满盛笑意的声音,“是阳阳吗?”
真是好人家呀,每一个都笑得这么暖人心。
然后,我终于见到了竹子。
和我想象中一样,清瘦着,简单着,只是脸部表情还未从刚刚的惊恐中恢复过来。
没想到他问我的第一句话居然是,“阳阳,有没有吓一跳?”
神经病。千里相会这么激动人心的时刻,心里还挂着这种微不足道的事情。我大力白他一眼,又拍他一下。幸好打过电话,不然按比例测算,如果我真的突然出现在他面前,竹子会直接昏死过去。
接下来,阿,接下来真是幸福甜蜜。我坐在竹子身边,两个人坏坏的欺负着清绘,搞得好似雌雄双煞。坦白讲,我曾不止一次的想象过竹子会怎样打字,听电话,真正看到了,心里还是好震荡。亲爱的竹子,从这一刻开始,我变了你知道么?
上飞机前的阳阳,是那么别扭那么骄矜的一个人,为了多吃一顿鱼翅而处心积虑,为了买到Burberries贵得离谱的裙子而千金一掷,为了男朋友没在那时那刻给我电话而号啕大哭,为了很多很多小事,耗费无数心力。现在想想,真真无地自容。
整个星期六,我和竹子都在电脑前形影不离。聊天涯的每一个人,聊天涯的每一件事。写帖子,写博客,当然,也毫不掩饰的聊起他的病况。哪怕我只有一点绵薄之力,也希望可以帮到忙。
竹子带我看花园里的花,那么多那么美,他一个一个地介绍,“这个是玫瑰,那个是月季,还有一串红,过去一点花已经谢了但是叶子还在的是芍药,旁边是菖蒲……”
我想起我家里的花。朱顶红,娇贵么娇贵得要死,动不动就歇菜,我都不知换了多少盆了。白白写了《如意》。人啊,为什么不去爱那些简单但是美丽的事物?
竹爸爸很健谈,很爽朗,笑起来声音很大,呵呵呵呵,笑声穿透屋前屋后。我们几个人对景小酌,此情此景,真希望时间就此停顿。
饭后竹子和我说起他的经历,说起那么多那么多的生病与康复。看似轻描淡写的一个个名词从他嘴里迸出来,我也装作处之泰然。实际上心里的泰山早已崩塌。
亦舒曾说,那样辛苦,也安然下来,亦即意味着你是存心来这世上做人的。
竹子竹子,同样的话送给你。
晚上雨巷终于联系上我,说是要坐晚上的车赶过来。要命,如果我早知道她是那种不把别人卖了别人还要烧香拜佛的高手,我才不担心她勒。
可是整个晚上我和竹子真的担心死了。尤其是竹子,坚持要等雨丫头的消息到凌晨。我的天,荷在网上“勒令”我们休息,我看看时间也不对,便对竹子说,“没关系,以丫头的智商,她应该晓得即便午夜两点赶到你家,最多只能像个倩女幽魂,没啥好折腾的了。肯定明天才来。你休息,我回招待所。”
竹子这才瞪着大眼睛,半信半疑地应了。
哎。这雨丫头。
第二天一早,我终于帮竹子把音箱装上。气死了,发了那么多好听的歌给他,原来他一直装聋作哑。奶奶的。蚂蚁,现在可以发你唱的歌给他听了,我在这里代他赔不是。他不是不想听,是真的没有装音箱。懒虫!
就在我们high到一半的时候,丫头的短信又来了。
“阳,我已过顺昌,2个小时后到晒口。告诉我怎么走。”
“你到桥头下车。对了,蛋糕买了吗?”
“没。要不我先到邵武,买了蛋糕再返回来?”
我看看表,娘西皮,已经11点,等她折腾完,我也要赶飞机去了。
于是,“这样,我现在去邵武买回来,你到我住的地方等我,然后我们一起来。”
竹子吵着要看我的手机,我躲开。
“又在玩什么阴谋?”他很心惊肉跳的样子。
哼,小样。我站起身,“我回趟住处,洗个澡换衣服。”
他瞪着我,“你早上还说不换衣服了,怎么又要换?”
我晕。管得还真多。“女人换衣服天经地义,走了。”
然后我以亚光速把蛋糕买回来,见到丫头的时候气喘如狗。
因为雨巷的到来,公公准备了更多的好菜好饭。
我拼命做事情,帮着收拾碗筷,帮着倒酒,帮着搬凳子,帮着夹菜。丫头笑说我好贤惠,我也笑。真实情况是,每次面对离别我就变得好狼狈,只能拼命找事情做来打发离愁。
下午时间一点一点过去,我装作不要去在意时间的样子,其实频频看钟。要走了,要走了,要走了,我不舍得,我不舍得,我不舍得。
吃蛋糕的时候,我溜开了一会儿,在电脑上留了一封信给竹子。
亲爱的竹子:多的话不想说了,我只想告诉你:一定要好好的,一定要好好地努力地坚持下去。哪怕只为了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叫做焱阳的女孩子,这么的这么的喜欢你,这么的这么的希望你好好的生活!我要走了,那么巧,正好在听龙宽九段的歌,《我听这种音乐的时候最爱你》。蛋糕好吃,音乐好听,这世上还有很多很多歌舞升平要和你一同分享。
——阳阳2005年7月3日星期日
不知道该写什么,不知道该说什么。胡乱写,胡乱在心里祝福着亲爱的竹子,什么祝福都用上,只希望好人一生平安。
临走我抱了一下竹子,他很紧张。奶奶的,抱一下还紧张,那就不亲了,怕他一下子害羞到休克。
这样抱一下,希望可以把热力从我身上传递过去,希望可以把此刻天涯社团每个人的祝福送到,希望可以把这美好的世界给他。同样,也希望他那颗天使一样美丽的心灵感染到我。
走了,但我会再来的。
为了武夷山的青山秀水。
为了涤荡自己的心浮气躁。
为了分享竹子身上生生不息的坚强。
为了一切一切美好的愿望。为了天涯共此时。
发上面那篇文章的时候,他说:看哭了呢。
发那篇文章的时候,我没有说的是:他不是懒得装音箱,妈妈哥哥和他罹患同一病症无法行动,父亲伤残,全家根本没有人能够完成哪怕只是装上音箱这么小的事情。
发那篇文章的时候,我刚知道那个父亲,也就是竹爸爸,并非竹子生父,只是为了要照顾他们一家子,勇敢担起重任。
发那篇文章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这会像导火索一样点燃社会对竹子关注的火。如果我有福报,相信这必是苍天感念我的微末功德。
发那篇文章的时候,他还在,我仍能假装轻松快乐。
现在他走了,我不用装了。我悲伤满溢。
几天前我还在一个离他很近的地方,对师兄说,“这里离竹子很近呢。如果时间够的话,我们去看看他吧。”
可是,我食言了,我没有再去——现在时间,再多也不够了。
算算日子,那天是1月2日,我赶回上海,竹子被送进医院。真的是擦肩而过啊。
竹子终因并发症,离开了这个世界。
曾经我也天真地认为,绝症已经忘记他了。
那么巧,又是唐挺告诉我他的死讯。
我抓住听筒,一片茫然。
再打给竹爸时,惭愧,我没有忍住我的眼泪。
反而是竹爸安慰我,“没事啦。也别过来了,竹子的遗体已经按照他生前愿望,捐献给红十字会了。”
是,连走都走得这么光明磊落。
更反衬出我的狷介、拖沓、凉薄与幼稚。
如果悲伤可以用任何一种方式表达,那我就不会这么难过了。
他的故事,一篇文章说不完。我对他的感情,很复杂,首先当然是挚友,其次,我爱他如长兄,再次,我尊敬他,还有,我乐意在他面前撒娇、说丧气话以及骂娘。
这样一个人,世上,少了一个。
再也听不到他笑笑地说“阳阳”了……
再也听不到他笑笑地说“没关系的”了……
再也听不到他笑笑地说“你知道我上厕所很漫长啊,要先挪过去,再挪回来”了……
再也听不到他笑笑地说“你的、地、得用得一塌糊涂啊!改死我了!眼睛都快盲了啊”了……
走好我亲爱的。
如有来世,一定要健康。一定记得还要相逢。一定记得还要相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