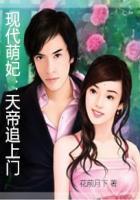荒野萧萧,无尽肃杀意。
落日夕阳,远远挂在天边,在高大险峻、连绵起伏的一道道山脉背后,将残余的温暖洒向西北大地。昏黄的光线落印染着静默,浮雪纷扬,四野沉寂。
寒风呼啸,雪落如麻。驮车窗外映衬在黄昏中的身影屹立,对于始终不曾将这种人生当真的苏景而言,悄无声息的刺杀并不可怕,令他不安的是濒临逝去时的冷静。
车阵中有西厂的探子,七爷早就知道。不过羁旅行商自然不好检查,免得打草惊蛇。只好暗中处处留意,不曾想这探子竟隐藏的如此深,便在方才的冲突中也未现身。
只在这最后时刻,才无声攻袭。时机掌控的端的是如此精妙,若不是苏景拼死将箭射出,现在的情形如何简直难以想象!汪直不死,在场的人自然都难活命。
谁都看的出,方才七爷已经豁出命去,若不是那精确到极致的弩箭,此时便是乾坤倒置。短暂呆滞后,老吴抬头,却见那个悄无声息出手的人正是驮队中的趟子手陈三儿。
未曾细想,此时这个老卒只知他们活命都是承了这个诸生的果断,无论如何也不能叫其陨了性命,*******,只见其臂张似弓,横刀斩落。怒目立须,大喝一声,寒光刀芒迅速掠过。
黯淡的黄昏,深邃的夜色中。粗粝大手捏着冷硬裹着印血棉布的刀柄,顷刻贯彻全身气力,背腹肌肉绷得积累成沟壑,一跃而起,以裂地之势向夜空中斩去。
寒光过处,留影无尽。扑向车厢前的人,尖锐的破空声似狞笑,纵横半生老吴的手从未似这般稳过,锋利的刀刃狠狠斩开了羊皮袍下的上等铠甲,然后长刀斩进温暖的躯体。
骨骼的阻隔对于这冲击力而言,却似半点也无。硕大的身体骤然纵生裂隙,颈骨中有粉碎的声音,目光寒冷,陈三儿甚至连哼都来不及哼一声,身子便被斩做两截。
热血自林间洒下,摔落在焦土枯叶上,半个头颅无声掉落,滚过他的脚边,划在腐叶间留下痕迹,散发气息在墨色中滚了极远,当年在大乾和蒙元的战争中。
老吴率领军阵曾无数次经历过险境,不过无论表现的如何强悍,都不曾有过这种酣畅,此时他横刀立于车厢前,身上狼藉,黄昏中只见那挺立地身形,衣袍猎猎,气度渊亭。
而放弃抵抗的苏景,由于窒息眼前已经浮现幻觉。就在他以为一切都要结束的时候,扼守在颈部的力度,倏然消失,冷粝的空气随着他急促的喘息涌进胸腔。
顿时喉咙深处的灼烧感蔓延至肺部,表情狰狞。视线环顾,嗡鸣的耳际也渐渐有声音浮现,外侧日落月升,只见硕大的银盘穿梭在几缕残云中,寒星寥寥。
机械般转动着的眸子环顾,却见屹立的身影顿时炸开,强劲的刀锋划开他温暖的身躯,溅射的热血叮叮的打在木质车厢上,如急促暴雨。初初恢复的身子,全无半点力气。
苏景那曾射出精湛箭矢的手,现在却连轻便的短弓也持不住了,喘息似从胸腔牵动耳膜,压抑而低沉,视线穿过那布满血污的窗子,落在外侧的战场中。
只见七爷抱着汪直的身子,轻轻一甩。便是将之抛到了两丈外,强自撑着无力的身躯,顷刻掠回燃着火的缓坡旁,迅速拾起宽背砍刀,冷然的目光盯着那已油尽灯枯的大太监。
不过这次他的警惕显然有些多余,给贯穿了耳廓自无多活,瘫软地倚着一株古木,震落枝杈上的雪,将他半边身子都给埋了起来,只留静静呕血的头颅在外。
血脸之上眼瞳衬着夜色默默望着火光里面那躺在车厢内的诸生,喃喃低语。不知为何,苏景似自凝视着自己的汪直表情中看到了释然,火光跃动点缀在他的冷僵的脸上。
渐息的光已经映满了他的双眸,再看时只见汪直摊开双手,唇角带笑,就此消匿。青山岭外沉默许久,七爷盯着他的遗体,双臂开始颤抖,终于有些支撑不住。
前所未有的疲惫和伤痛使他持不住这陪伴自己半生的兵器,刀入雪中。喘息沉闷急促,暗红的血自紧咬的牙关中溢出,茫茫无边黑夜,七爷的身上浸满鲜血。
方才为了攻破车阵,锦衣卫迫不得已用了火油,如今虽燃烧许久却依旧未曾熄灭。但毕竟风大雪疾,况且青山岭外落叶多雪,火势渐渐熄灭,如今只有半点火焰维持。
月色渐渐浓郁,西北荒原上的风向来很硬,火焰拉的老长,随即又被吹灭,冒出一缕缕烟气,伪装成的驮马大多是纵横疆场的战骑组成,经过这场战斗,倒是没跑多远。
此时正不安的嘶鸣着,四下的景物自模糊的轮廓变成清晰的景象,此时苏景混乱的思维也堪堪恢复,趴在车厢里给冻的浑身发麻,瞪着眼睛看着眼前一切。
驮队四周,全是尸体。怕有近百,鲜血溅在焦土草上,凝固就是紫黑的痕迹,人马的尸体横七竖八的堆在那儿,缺胳膊少腿儿却是常有的事儿,平静下来的苏景那里见过如此可怕的景象,顿时间骇的头皮发麻。
驮队内外,到处都是斑驳的烧焦痕迹,还有难闻的味道,一切都在提醒着他们这夜是何等的凶险,即便是七爷,此刻也是乱发横生,身子脱力不由架在车辕边缘休息。
身上破旧的羊皮袍早就烂了,脸上黑一道白一道脏的跟什么似的,颓然间坐倒在地。许久重负看到如此情形,才终于松了一口气。
老吴胸中热血渐冷,寒气平复着情绪,倚靠着车厢休息半刻才勉强有了些力气。不过这里终究不是久留之地。少顷,七爷挪了过来,轻声道:“去看看。”
这件事双方隐秘,以免有什么消息走漏出去,还是谨慎些为好。老吴看着他,也不犹豫。点了点头,提着刀忍住伤口痛楚向战场中走去,不管是哪一方的人。
也无论是死是活,都照样在要害处补上几刀。而七爷也朝着前面几乎变成废墟的驮车行去,掀开沉重的厢木碎石,见此时老者额头有血,却一动不动,只盯着身前已经冷透的钱掌柜的尸体,七爷满脸无奈地叹息,擦去脸上的灰尘。
昂首望天,只见深邃苍穹寒星点点,一轮冷月,数缕残云。合着存余的火星光泽照耀,浑身染血的汉子,持刀挺立在孤独的老者身前,不曾哀伤,只有默默印染的苍凉悲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