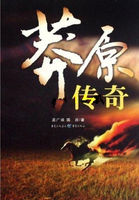随意想了想,总觉得他这话不似寻常关切之话。
我提了提下摆回到:“常在这种地方走,哪有不摔倒的?”
尚书垂了眸子,连连称是。
随行的衙役将上了锁的门打开,而后便伫立在门旁,手搭在腰间那把寒光凛凛的弯刀之上,目如铜铃瞪着牢中其他喊冤的犯人,那些人大多是前朝官员,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些罪状。
这门刚一打开便有一股子霉味迎面袭来,我五脏六腑几经翻涌,强强将那呕吐之意压下。
听见有声响,牢中那人飞快起身,下意识朝门口望。见到来人是我之时,面上有诧异。
他着一身中衣,本是素洁的衣裳现下绽放朵朵鲜红,同白衣相衬之下,难免有些让人发怵。只是这人除去面色因长期不接触日光而有些苍白之外,全然不见受伤后的痛苦之色,即便是稍微抿紧的嘴唇边那抹隐忍也有丝牵强。
我正欲走上前去询问,身旁邢尚书便挡在我身前:“大人,这犯人身上委实污秽,可别脏了大人的衣裳。”
对于他的横加阻拦,我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忍让,但现下这已然上升到了叔可忍婶都忍不了的地步了。
我将方才衙役递过来的帕子摔在他身上:“这事到底是本官办还是你在办?普天之下到底是你大还是皇帝大?”
气愤之下,我声量提高不少,整个牢中半丝声响全无,我回头扫了一圈,众人皆屏气望向我。
尚书年长我不少,见我如此,面上有些挂不住,却因品阶在我之下不得不将怒气咽下。
他虽未还口,但身上愠怒很是明显,冷哼一声便将身子转了过去,但也仅止于此,并无出去之意。
我广袖一挥,带起尘土一片:“本官要审问个犯人还用得着你在旁边指点?”
他勃然大怒,猛然回身盯着我:“这是刑部大牢,下官虽品阶在大人之下,但好歹是一局主官,还望大人注意修辞。”
“既然尚书大人欲同本官谈品阶,那本官便好生说上一说。”我怒极反笑,靠近他两步,瞧见他一双眸子中自己的倒影:“本官身在御史大夫之位,负责监察百官,敢问你邢尚书在不在这百官之列?既在这百官之列那便是本官的职责之内,那本官来你这刑部提审个犯人还要劳你在旁边说三道四?再说这礼节,本官品阶在邢尚书之上,那么邢尚书见到本官时,应当左为手拳,右手为掌,两拳相抱。鞠躬时身子倾斜,口中应道:下官参见大人。那本官又要问上一问,方才你见到本官是如何行礼的?邢尚书任职这些年,官场之道都还给你师父了吗?”
我一口气将话说完,胸口起伏明显,眼见邢尚书一张脸涨成猪肝色,身子不自觉发抖,想必是在极力克制着将我拖下去打一百大板的冲动。
“既然听完了,那便有劳邢尚书在外面候着,本官问过话后自然会离开此处。”
我逐客之意明显,邢尚书又在盛怒之下,闻言不作犹豫便离开牢中。
我吩咐衙役将门关上,这才转身靠近那一直缩在角落中的男子。
他已过不惑之年,面上有复杂的神色,见我过去并未作出旁的举动。
“你可有什么话想说?”我面无表情瞧着他。
他张了张嘴,却未发出一丝声响,不得已之下用手指了指自己的喉咙。
“你哑了?”我心中一紧,扯过他的袖子将声音放低:“可是他们动的手脚?”
男子拼命点头,对我抱了抱拳,后拉过我的手在上面写了几个字,我天生便怕痒,是以忍了许久才算未笑出声。
他一笔一划道:我不想死
我紧迫盯着他,想从他面上找出些蛛丝马迹,但除去希冀外我瞧不出其他任何情绪。
瞧他面相也不是奸恶之人,只是不知如何同刘福山扯上了干系。
见我打量他,他眼中希望之光愈发明显,最后竟是双膝一软在我身前跪下。
平心而论,我对他印象不错,是以见他如此,急忙将他扶起:“我要如何信你?”
他愣怔片刻,希冀之光黯淡下去,想必是说不出教我信服他的理由。
片刻之后,他突然自身上撕下一条布条,咬破手指洋洋洒洒写了几句话,瞧那字体磅礴大气,竟有大家之风范。
他左顾右盼,瞧见周围无人把守之后,飞快将布条塞入我手中,示意我快些瞧完。
我抖开布条,上书:吾乃治粟内史杨奎,家住京郊,现一家妻儿老小皆在刘福山手上,大人不信我无妨,望大人保我妻儿及父母。
我将布条顺手搁进袖口之中,再度拿眼瞧他,心中摇摆不定,只因眸子纯厚便轻信于人这事,怎么瞧都有些冒险。若想查证此事也只得去他府上转上一转,可瞧现下的情形,他分明是被刘福山捏在手中,贸然将他留在此处还不知会遭到何种对待。
我有些为难,未再开口,再三考虑之后还是觉应当先去瞧瞧其他几人。
我出门时,杨奎依旧未作出什么不合礼数的举动。只是透过那极高的窗子眺望一方白云,眼神飘渺。
刘福山亲信四人的牢房相邻,我差衙役将第二扇门打开,里面那人生的肥头大耳,嘴角挂着谄媚的笑,身上着同样的中衣上面有着同样的血花,因着长时间不梳洗,脸上生出一层油脂,即便日光很是微弱,但依旧不耽误他发光发亮,当得起闪闪惹人爱一说。
我有些疑惑,既是行过大刑,怎的还能笑的如此烂漫,瞧他并不像个硬汉,反倒是一脸的奸猾。
邢尚书此时好似忘却了方才的不愉快,又跟在我身后挤了进来,但却是学聪明了些,未再开口,只是下意识的横在我同那男子当间但动作又不十分明显。
见他如此,我也不好再绷着脸,当下朝他扯了扯嘴角,而后趁他不备将那肥可流油的男子衣裳扯下大半。
但见他皮肤白花花一片,哪里有半道伤口。
邢尚书同那男子面色一僵,一同在我身前跪下,老泪纵横道:“大人饶命,下官是不得已而为之,此事若传出去,下官一家老小性命难保啊。”
想必那让他老小性命不保之人又是刘福山,我一脚踹在那男子身上,他躺在地上哼哼个不停。
我转身又去了隔壁牢房,也顾不得礼数,扬手掀开了杨奎的中衣,但见他身上伤疤新旧交替,旧伤还未愈合上面又添了几道新伤,有些还淌着脓水。
这大抵是欲积极配合政府工作后被威胁警告的结果。
我将邢尚书唤了来:“这人我要提走,你放是不放?”
邢尚书全无初始的气度,痛哭流涕道:“大人您这不是为难下官吗?他一走,这势必会传到旁人耳中,下官届时可如何交代啊。”话毕下颔朝门口的衙役指了指,眉峰微挑,表情闪烁,似有难言之隐。
我顺着他的眸光回头瞧了瞧:“他既已知晓了如此多的事,你还准备留着他作甚?陪着你过中元吗?”
邢尚书眼珠转了几圈,低声道:“他是通风报信之人,若他不见了踪影,那事情不就穿帮了?”
我蹙了蹙眉:“此事我自有定夺,你先将他押在牢中顶替杨奎罢,回头我向皇上请旨,你这刑部大牢任何人不准靠近。当然,今日的事邢大人也要守口如瓶才好啊。”
邢尚书忙不迭作揖:“自然自然,方才多有怠慢,还望大人海涵。”
交谈中我瞧门口衙役见情形不对欲脱身,急忙唤人见他拦下,绕至他身后一个手刀将他劈晕,差人扒光了他的衣裳里里外外检查一遍,而后请杨奎同他对换了衣裳,这便带着杨奎往外去。
外头空气着实清新,我不自觉深吸了几口,而后转身对身后杨奎道:“杨大人,这些日子我会将你送至我府中暗牢,直至事情查清后再做定夺。若有怠慢之处还望大人莫要怪罪。”
杨奎点了点头,眼中感激之光闪现。
我府上那暗牢,虽说名义上也称为牢,可实际却是比真正意义上的牢房条件要好上许多,充其量不过是一处闲职的偏房,当然,地理位置偏下。
将杨奎安置妥当后,不过才到午时,我却累的连饭都吃不进去。
草草洗了洗身子,钻入榻上蒙头便睡。
临睡前回想起方才种种,心中这才升起后怕,怪只怪我太易冲动。如此不计后果,倒真是有将自己搭进去的可能。
迷蒙中额上拂过一抹微凉,甚是舒坦,我不自觉朝那凉意贴了贴,蓦然听到一阵轻笑。声量不大,却将我骇的清醒过来。
几乎是下意识抱着被子朝踏里缩了缩,这才瞧见慕容离一身便装倚在我榻前,左臂垫在枕头之上,嘴角还有一抹笑。
我脸一红,方才竟是枕在了他手臂上。
见我转醒,慕容离长臂一挥将我捞了过去:“今日进展如何?”
他一提此事我来了精神,仰头问他:“皇上可认得杨奎?”
他眼神迷茫。
我拍了拍脑门,他平常日理万机,的确没有工夫去记朝中大臣。
“皇上。我想请您下一道圣旨,挑些可信之人严守刑部牢房,教闲杂人等莫靠近刑部牢房,更不能放人进去探望。”
他若有所思,半晌后道了句好。
“今日我还没用膳,你不准备招待下我?”
我起身时,他依旧靠在榻旁,挑眉瞧我。
我探头望了望天色,已日落西山,本是蔚蓝的天际染上了半边橘黄。
腹中也适时唱起了空城计,遂开门教厨子准备了晚膳,再一回头时,慕容离已平躺在榻上睡了过去。
这白日里是做了什么能累成这样。我撇了撇嘴,世人都说没心没肺之人睡眠质量才高,可横瞅竖瞅,慕容离同没心没肺如何也搭不上边啊。
我咂了咂舌,还是过去给他扯了扯被子。但无奈他身量高大,我这薄被是遮住他的肩便遮不住他一双脚,遮了他的脚又将双肩露了出来。
我苦恼之际,他突然伸手将我带进怀中,额前洒下一片温热。
“你你你……你不是睡了吗?”我嘶嘶哎哎问。
他露出一排皓齿,话语间洋洋自得:“我又不是你,自然不会两眼一闭便睡了过去。”他手臂紧了紧:“只是在你这能好好歇一会倒是真的。明日我差人在此处换一张大些的床榻。”
我头皮一紧:“皇上三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