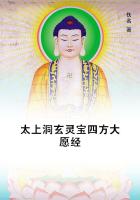当着站长和正在打字的车站,旅客除了眼看一列列火车通过外,竟茫然不知所云,也不知所措。我曾不知多少次经过纽约中央车站,却从未见过那站长。而在这里却实实在在地既见到了车站又见到了站长。要不然我很可能会把他们两个搞混。
梁思成在信的末尾写道:
现在轮到车站了:其主梁因构造不佳而严重倾斜,加以协和医院设计和施工的丑陋的钢铁支架经过七年服务已经严重损耗,从我下面经过的繁忙的战时交通看来已经动摇了我的基础。
十一(一九四六年七月末梁、林全家回到他们思念已久的北京。不久,梁思成受到普林斯顿大学和耶鲁大学的邀请,到美国进行学术访问,其间并受聘为联合国大厦设计委员会委员,参与了大厦的设计工作。一九四七年夏,林徽因病情突然恶化,须作肾切除手术。梁思成匆匆赶回北京。在给费慰梅的信中,林徽因描写了梁思成带给她的礼物。)
在一个庄严的场合,梁先生向我展示了他带回的那些可以彻底拆、拼、装、卸的技术装备。我坐在床上,有可以调整的帆布靠背,前面放着可以调节的读写小桌,外加一台经过插入普通电源的变压器的录音机,一手拿着放大镜,另一手拿着话筒,一副无忧无虑的现代女郎的架式,颇像卓别林借助一台精巧的机器在啃老玉米棒子。
关于那录音机:
我们确实听到了录在磁盘上的各种问候。但是全都不对头了,思成听起来像梅贻琦先生、慰梅像费正清、而费正清近乎保罗·罗伯逊。其中最精彩的是阿兰的,这当然在意料之中。我非常自豪,能收藏一位专业艺术家的“广播”录音。不过迄今我还没有按这机器应有的用途来做什么,只有让孩子们录些闹着玩的谈话。我觉得好像乾隆皇帝在接受进贡的外国钟表。
我敢说他准让嫔妃们好好地玩了一阵子。
致梁思庄
思庄:
来后还没有给你信,旅中并没有多少时间。每写一封到北平,总以为大家可以传观,所以便不另写。连得三爷(指林徽因的三弟林恒,时住梁家),老金等信,给我们的印象总是一切如常,大家都好,用不着****什么心,或是要赶急回去的。但是出来已两周,我总觉得该回去了,什么怪时候,赶什么怪车都愿意,只要能省时候。尤其是这几天在建筑方面非常失望,所谒大寺庙不是全是垃圾,便是已代以清末简陋的不相干房子,还刷着蓝白色的“天下为公”及其他,变成机关或学校。每去一处都是汗流浃背的跋涉,走路工作的时候又总是早八至晚六最热的时间里。这三天来可真真累得不亦乐乎。吃得也不好,天太热也吃不大下。因此种种,我们比上星期的精神差多了。
上星期劳苦功高之外,必到个好去处,不是山明水秀,就是古代遗址眩目惊神,令人忘其所以!青州外表甚雄,城跨山边,河绕城下,石桥横通,气象宽朗,且树木葱郁奇高。晚间到时山风吹过,好像满有希望,结果是一无所得。临淄更惨,古刹大佛有数处。我们冒热出火车,换汽车,洋车(黄包车),好容易走到,仅在大中午我们已经心灰意懒地得见一个北魏石像!庙则统统毁光!
你现在是否已在北屋暂住下,Boo(梁思庄的女儿吴荔明的乳名)住哪里?你请过客没有?如果要什么请你千万别客气,随便叫陈妈预备。思马一(灵色城的五妹思懿的绰号)外套取回来没有?天这样热,Ican’tquiteimagine人穿它!她的衣料拿去做了没有?都是挂念。
匆匆。
二嫂。
整天被跳蚤咬得慌,坐在三等火车中又不好意思伸手在身上各处乱抓,结果浑身是包!
致梁再冰
宝宝:
妈妈不知道要怎样告诉你许多的事,现在我分开来一件一件的讲给你听。
第一,我从六月二十六日离开太原到五台山去,家里给我的信就没有法子接到,所以你同金伯伯(金岳霖)、小弟弟(梁从诫)所写的信我就全没有看见(那些信一直到我到了家,才由太原转来)。
第二,我同爹爹不止接不到信,连报纸在路上也没有法子看见一张,所以日本同中国闹的事情也就一点不知道!
第三,我们路上坐大车同骑骡子,走得顶慢,工作又忙,所以到了七月十二日才走到代县,有报,可以打电报的地方,才算知道一点外面的新闻。那时候,我听说到北平的火车,平汉路同同蒲路已然不通,真不知道多着急!
第四,好在平绥铁路没有断,我同爹爹就慌慌张张绕到大同由平绥路回北平。现在我画张地图你看看,你就可以明白了。
注意万里长城、太原、五台山、代县、雁门关、大同、张家口等地方,及平汉铁路、正太铁路、平绥铁路,你就可以明白一切。
第五(现在你该明白我走的路线了),我要告诉你我在路上就顶记挂你同小弟,可是没法子接信。等到了代县一听见北平方面有一点战事,更急得了不得。好在我们由代县到大同比上太原还近,由大同坐平绥路火车回来也顶方便的(看地图)。可是又有人告诉我们平绥路只通到张家口,这下子可真急死了我们!
第六,后来居然回到西直门车站(不能进前门车站),我真是喜欢得不得了。清早七点钟就到了家,同家里人同吃早饭,真是再高兴没有了。
第六,现在我要告诉你这一次日本人同我们闹什么。你知道他们老要我们的“华北”地方,这一次又是为了点小事就大出兵来打我们!现在两边兵都停住,一边在开会商量“和平解决”,以后还打不打谁也不知道呢。
第七,反正你在北戴河同大姑、姐姐哥哥们一起也很安稳的,我也就不叫你回来。我们这里一时也很平定,你也不用记挂。我们希望不打仗事情就可以完;但是如果日本人要来占北平,我们都愿意打仗,那时候你就跟着大姑姑那边,我们就守在北平,等到打胜了仗再说。我觉得现在我们做中国人应该要顶勇敢,什么都不怕,什么都顶有决心才好。
第八,你做一个小孩,现在顶要紧的是身体要好,读书要好,别的不用管。现在既然在海边,就痛痛快快的玩。你知道你妈妈同爹爹都顶平安的在北平,不怕打仗,更不怕日本。过几天如果事情完全平下来,我再来北戴河看你,如果还不平定,只好等着。大哥、三姑过两天就也来北戴河,你们那里一定很热闹。
第九,请大姐多帮你忙学游水。游水如果能学会了,这趟海边的避暑就更有意思了。
第十,要听大姑姑的话。告诉她爹爹妈妈都顶感谢她照应你,把你“长了磅”。你要的衣服同书就寄来。
妈妈。
致傅斯年
孟真先生:
接到要件一束,大吃一惊,开函拜读,则感与惭并,半天作奇异感!空言不能陈万一,雅不欲循俗进谢,但得书不报,意又未安。踌躇了许久仍是临书木讷,话不知从何说起!
今日里巷之士穷愁疾病,屯蹶颠沛者甚多。固为抗战生活之一部,独思成兄弟年来蒙你老兄种种帮忙,营救护理无所不至,一切医药未曾欠缺,在你方面固然是存天下之义,而无有所私,但在我们方面虽感到lucky终增愧悚,深觉抗战中未有贡献,自身先成朋友及社会上的累赘的可耻。
现在你又以成永兄弟危苦之情上闻介公,丛细之事累及泳霓先生,为拟长文说明工作之优异,侈誉过实,必使动听,深知老兄苦心,但读后惭汗满背矣!
尤其是关于我的地方,一言之誉可使我疚心疾首,夙夜愁痛。日念平白吃了三十多年饭,始终是一张空头支票难得兑现。好容易盼到孩子稍大,可以全力工作几年,偏偏碰上大战,转入井臼柴米的阵地,五年大好光阴又失之交臂。近来更胶着于疾病处残之阶段,体衰智困,学问工作恐已无分,将来终负今日教勉之意,太难为情了。
素来厚惠可以言图报,惟受同情,则感奋之余反而缄默,此情想老兄伉俪皆能体谅,匆匆这几行,自然书不尽意。
思永已知此事否?思成平日谦谦怕见人,得电必苦不知所措。希望泳霓先生会将经过略告知之,俾引见访谢时不至于茫然,此问。
双安。
致金岳霖
老金:
多久多久了,没有用中文写信,有点儿不舒服。
John(费正清)到底回美国来了,我们愈觉到寂寞,远,闷,更盼战事早点结束。
一切都好。近来身体也无问题的复原,至少同在昆明时完全一样。本该到重庆去一次,一半可玩,一半可照X光线等。可惜天已过冷,船甚不便。
思成赶这一次大稿,弄得苦不可言。可是总算了一桩大事,虽然结果还不甚满意,它已经是我们好几年来想写的一种书的起头。我得到的教训是,我做这种事太不行,以后少做为妙,虽然我很爱做。自己过于不efficient,还是不能帮思成多少忙!可是我学到许多东西,很有趣的材料,它们本身于我也还是有益。
已经是半夜,明早六时思成行。
我随便写几行,托John带来,权当晤面而已。
徽寄爱。
致梁思成
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二日。
思成:
我现在正在由以养病为任务的一桩事上考验自己,要求胜利完成这个任务。在胃口方面和睡眠方面都已得到非常好的成绩,胃口可以得到九十分,睡眠八十分,现在最难的是气管,气管影响痰和呼吸又影响心跳甚为复杂,气管能进步一切最有把握,气管一坏,就全功尽废了。
我的工作现实限制在碑建会小组的问题(当时正在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有时是把几个有限的人力在一起组织一下分配一下工作,技术方面讨论如云纹,如碑的顶部;有时是讨论应如何集体向上级反映一些具体意见作一两种重要建议,今天就是刚开了一次会,有阮邱莫吴梁连我六人,前天已开过一次,拟了一信稿呈郑副主任和薛秘书长的,今天阮将所拟稿带来又修正了一次今晚抄出大家签名明天可发出(主要要求立即通知施工组停扎钢筋,美工合组事难定了,尚未开始,所以也趁此时再要求增加技术人员加强设计实力,反映我们对去掉大台认为对设计有利,可能将塑型改善,而减掉复杂性质的陈列室和厕所设备等等使碑的思想性明确单纯许多)。再冰小弟都曾回来,娘也好,一切勿念。信到时可能已过三月廿一日了。
天安门追悼会(斯大林的追悼会)的情形已见报我不详写了。
昨李宗津(清华大学建筑系美术教授,油画家)由广西回来还不知道你到莫斯科呢。
徽因三月十二日写完。
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七日。
思成:
今天是十六日,此刻黄昏六时,电灯没有来,房很黑又不能看书做事,勉强写这封信已快看不见了。十二日发一信后仍然忙于碑的事。今天小吴老莫都到城中开会去,我只能等听他们的传达报告了。讨论内容为何,几方面情绪如何,决议了什么具体办法,现在也无法知道。昨天是星期天,老金不到十点钟就来了,刚进门再冰也回来,接着小弟来了,此外无他人,谈得正好,却又从无线电中传到捷克总统逝世消息,这种消息来在那沉痛的斯大林的殡仪之后,令人发愣发呆,不能相信不幸的事可以这样的连着发生。大家心境又黯然了……
中饭后老金小弟都走了。再冰留到下午六时,她又不在三月结婚了,想改到国庆。理由是于中干(林徽因梁思成长女梁再冰的丈夫)说他希望在广州举行。那边他们两人的熟人多,条件好,再冰可以玩一趟。这次他来,时间不够也没有充分心理准备,六月又太热,我是什么都赞成。反正孩子高兴就好。
我的身体方面吃得那么好,睡得也不错,而不见胖,还是爱气促闹清痰打呼噜出泡声,血脉不好好循环冷热不正常等等,所以疗养还要彻底,病状比从前深点,新陈代谢作用太坏,恢复的现象极不显著,也实在慢,今天我本应该打电话问校医室血沉率和痰化验结果的,今晚便可以报告,但因害怕结果不完满因而不爱去问!
学习方面可以报告的除了报上主要政治文章和理论文章外,我连着看了四本书都是小说式传记。都是英雄的真人真事。
还要和你谈什么呢?又已到了晚饭时候,只好停下来。该吃饭了。(下午一人甚闷时,关肇业来坐一会儿,很好。太闷着看书觉到晕昏。)
(十六日晚写)
十七日续:
我最不放心的是你的健康问题,我想你的工作一定很重,你又容易疲倦,一边吃Rimifon(1)不知是否更易累和困,我的心里总惦着,我希望你停Rimifon吧,已经满两个半月了。苏联冷,千万注意呼吸器官的病。
昨晚老莫回来报告,大约把大台改低是人人同意,至于具体草图什么时候可以画出并决定,是真真伤脑筋的事,尤其是碑顶仍然意见分歧。
徽因匆匆写完三月十七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