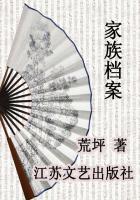他努力把脚放进步幅最大的那串脚印里,这使得他腿上被凝血粘合的伤口又开裂了。热乎乎的血像虫子一样从腿上往下爬行,但他仍然努力迈着大步。微微仰起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一一不知为了什么而开心的笑容,因此显得迷茫的笑容。
枪声。
阴暗的森林深处传来了枪声。也许是因为粗大而密集的树,也许是因为积得厚厚的雪,低沉喑哑的枪声还不如母亲临产的叫声响亮。格拉呆立了一下,然后放开了脚步猛跑起来。沉闷的枪响一声又一声传来。起初还沉着有序,后来就慌乱张皇了。然后,是人一声凄厉而有些愤怒的惨叫在树林中久久回荡。格拉越跑越快,当他感到就要够不上那最大的步子时,那些步子却变小,战战兢兢、犹疑不前了。
格拉也随之慢慢收住了脚步。目艮前不远处,一个巨大的树洞前仰躺着一个蠕动的人,旁边俯卧着一只不动的熊。这几个胆大妄为又没有经验的家伙竟敢对冬眠的熊下手。而另一只熊正拖着一路血迹在雪地上追逐那几个家伙。胃其中两个家伙,竟然一直往下,扑向一块洼地里去了。在机村,即便一次猎都没有打过的女人都知道,猛兽被打伤后,总是带着愤怒往下俯冲,所以,有经验的猎人,都应该往山坡上跑。但这两个吓傻了的小子却一路往下。那是汪钦兄弟俩,高举着不能及时装药填弹的火枪往洼地里跑去。开初,小小的下坡给了他们速度,熊站住了。这只在冬眠中被惊醒、同伴已经被杀害的熊没想到面前的猎手是这样蠢笨。
摆脱了危险的同伴和格拉同时高叫,要他们不要再往下跑了。
汪钦兄弟依然高举着空枪,往积雪深厚的洼地中央飞跑。斜挂在身上的牛角火药筒和鹿皮弹袋在身上飞舞。熊还站在那里,像是对这两个家伙的愚蠢举动感到吃惊,又像是一个狡猾的猎人在老谋深算。
格拉又叫喊起来。
晚了,两人已沖到洼地的底部,深陷到积雪中了。他们扔下了枪,拼命往前爬。
格拉扑到和熊睡在一起的那人跟前,捡起了枪。这是他生平第一次端起枪来,他端着枪的手、他的整个身子都禁不住颤抖起来。他嗅到了四周弥散的硝烟味道和血的味道。在机村,那些有父兄的男孩,很小就模枪,并在成年男人的教导下,学会装弹开枪。格拉这个有娘无爹的孩子,只是带着从母亲那里得来的显得没心没肺的笑容,看着另啲男孩因为亲近了枪而日渐显出男人的气象。现在,他平生第一次端起了枪,往枪腾里灌满火药,从枪口摁进铅弹,再用捅条狠狠地捅进枪膛,压实了火药,然后,扳起枪机,扣上击发的信药,这一切他都飞快完成了。这一切,他早在村里那些成年男子教自己的儿子或兄弟使用猎枪时一遍遍看过,又在梦里一次次温熟了。现在,他镇定下来,像一个猎手一样举起枪来,同时,嗅到了被捣开的熊窝温热腥膻的味道。那熊就站在这种味道的尽头,在雪地映射的惨白光芒中间。血从它身子好几个地方往下淌。
受伤的熊一声嗥叫,从周围树木的梢头,震下一片迷蒙的雪雾。熊往洼地里冲了下去,深深的雪从它沉重的身体两边像水一样分开。
枪在格拉手中跳动一下。
可他没有听到枪声,只感到和自己身子一般高的枪往肩胛上猛击一下。
他甚至看到铅弹在熊身后钻进了积雪,犁开积雪,停在了熊的屁股后面。那几个站在山洼对面的家伙也开枪了。熊中了一弹,重重地跌进了雪窝,在洼地中央沉了下去。但随着一声嗥叫,它又从雪****了出来。它跟汪钦兄弟已近在咫尺了。
格拉扔掉空枪。叫了起来:
“汪!汪汪!”
“汪汪!汪!”
他模仿的猎犬叫声欢快而响亮,充满了整个森林,足以激怒任何觉得自己不可冒犯的动物。如果说,开枪对他来说是第一次的话,那么,学狗叫他可是全村第一。他在很多场合学过狗叫,那都是在人们面前,人们说:格拉,叫一个。他就汪汪地叫起来。听到这逼真的狗叫声,那熊回过身来了。格拉感到它的眼光射到了自己身上。那眼光冰一样冷,还带着很沉的分量。格拉打了一个寒噤。然后,他还听见自己叫了一声:“妈呀!”就转过身子,甩开双腿往来时的路上,往山下拼命奔逃了。
汪汪!格拉感到自己的腿又流血了,迎面扑来的风湿润沁凉,而身后那风却裹挟着血腥的愤怒。他奔跑着,汪汪地狀叫着,高大的树木屏障迎面敞开,雪已经停了,太阳在树梢间不断闪现。不知什么时候,腰间的长刀握在了手上,随着手起手落,眼前刀光闪烁,拦路的树枝刷刷地被斩落地上。很快,格拉和熊就跑出了云杉和油松组成的真正的森林,进入了次生林中。一株株白桦树迎面扑来,光线也骤然明亮起来,太阳照耀着这银装素裹的世界,照着一头熊和一个孩子在林中飞奔。
格拉回头看看熊。那家伙因为伤势严重,已经抬不起头来了,但仍然气咻咻地跟在后面朝山下猛冲。只要灵巧地转个小弯,体积庞大的熊就会回不过身来,被惯性带着冲下山去。带着那么多伤,它不可能再爬上山来。但现在奔跑越来越镇定并看到了这种选择的格拉却不想这样,他甚至想回身迎住熊,他想大家都不要这样身不由己地飞奔了。
现在,从山上往下可以看到村子了。
村子里的人也望着他们,从一个个的房屋平台,从村中的小广场上向山上张望,看着一头熊追赶着格拉往山下猛冲。积雪被他们踢得四处飞扬。猎狗们在村子里四处乱窜。而在格拉眼中,那些狗和奔跑的人并不能破坏雪后村子的美丽与安静。
格拉还看到了母亲,在雪后的美丽与宁静中,脸上汗水闪闪发光,浑身散发着温暖的气息,在火塘边睡着了。睡得像被雪覆盖了的大地一模一样。母亲不再痛苦地呼喊了。那声音飘向四面八方。在中央,留下的是静谱村庄。
格拉突然就决定停下来不跑了,不是跑不动了,而是要阻止这头熊跑进雪后安宁的村子。村子里,有一个可怜的女人在痛苦地生产后正在安静地休息。
那一天,一个雪后的下午,村子中的人们都看到格拉突然返身,迎着下冲的熊挺起了手中的长刀。
格拉刚一转身就感到熊的庞大身躯完全遮蔽了天空,但他还是把刀对准了熊胸前的白点,他感到了刀尖触及皮毛的一刹那,并听到自己和熊的体内发出骨头断裂的咔嚓声。血从熊口中和自己口中喷出来,然后,天地旋转,血腥气变成了有星星点点金光闪耀的黑暗。
格拉掉进了深渊。
在一束光亮的引领下,他又从深渊中浮了上来。
母亲的脸在亮光中渐渐显现。他想动一动。但弄痛了身子,他想笑一笑,却弄痛了脸。他发现躺在火塘一边的母亲凝视着他,自己躺在火塘的另一边。
“我怎么了?”
“你把它杀死了。”
“谁?”
“儿子,你把熊杀死了,它也把你弄伤了。你救了汪钦兄弟的命,还打断了兔嘴齐米的鼻梁。”
母亲一开口,一件又一件的事情就都想起来了,他知道自己和母亲一样流过血,而身体也经历了与母亲一样的痛苦了。屋外,雪后的光线十分明亮,屋里,火塘中的火苗霍霍抖动,温暖的氛围中潇动着儿子和母亲的血的味道。
“熊呢?”
“他们说你把它杀死了,儿子。”母亲有些虚弱地笑了,“他们把它的皮剥了,铺在你身子下,肉在锅里,已经煮上了。”
格拉虚弱地笑了,他想动一动,但不行,胸口和后背都用夹板固定了,母亲小心翼翼地牵了他的手,去摸身下的熊皮。牵了左手摸左边,牵了右手摸右边。他摸到了,它的爪子,它的耳朵,是一头熊被他睡在身子底下。村里的男人们把熊皮绷开钉在地板上,让杀死它的人躺在上面。杀死它的人被撞断了肋骨,熊临死抓了他一把,在他背上留下了深深的爪痕。当然,这人不够高,熊没能吻他一下,给一张将来冷峻漂亮的脸留下伤疤。
“这熊真够大。”母亲说。
“我听见你叫了,你疼吗?”
“很疼,我叫你受不了了?”
“不,阿妈。”
母亲眼中泪光闪烁,俯下身来亲吻他的额头。她浑身都是奶水和血的味道,格拉则浑身都是草药和血的味道。
“以前……”格拉伸出舌头添舔嘴唇,“我,也叫你这么痛?”
“更痛,儿子,可我喜欢。”
格拉咽下一大口睡沫,虽然痛得冒汗,但他努力让自己脸上浮起笑容。用一个自己理解中成年男子应有的低沉而平静的声音问道:
“他呢?”
“谁?”
格拉甚至有些幽默地眨了眨眼,说:“小家伙。”他想父亲们提到小孩子时都是用这种口气的。
母亲笑了,一片红云飞上了她的脸频。她说:“永远不要问我一件事情。”
格拉知道她肯定是指谁是小不点的父亲这个问题。他不会问的。小家伙没有父亲,可以自己来当,自己今天杀死了一头熊,在这个小孩子出生的时候。而自己就只好永远没有父亲了。
桑丹把孩子从一只柳条编成的摇篮里抱出来。孩子正在酣睡,脸上的皮肤是粉红色的,皱着的额头像一个老太太。从血和痛苦中诞生的小家伙浑身散发着奶的气息。
“是你的小妹妹,格拉。”
母亲把小东西放在他身边。小小的她竟然有细细的鼾声。格拉笑了,因为怕牵动伤口。他必须敛着气。这样,笑声变得沙哑。成年男子一样的沙哑笑声在屋里回荡起来。
“给她起名了吗?”格拉问。
母亲摇头。
“那我来起吧。”
母亲点头,脸上又露出了幸福的笑容。
“就叫她戴芭吧。生她时,下雪,名字就叫雪吧。”
“戴芭?雪?”
“对,雪。”
母亲仰起脸来,仿佛在凝望想象中漫天飞舞的轻盈洁净的雪花。
格拉发话了,你也睡下,我要看你和她睡在一起,你们母女两个?
母亲顺从地躺在了女儿旁边,仿佛是听从丈夫的吩咐一样。桑丹闭上了双眼,屋子里立即安静下来。雪光透过窗户和门缝射进屋里,照亮了母亲和妹妹的脸。这两张脸彼此间多么相像啊。都那么美丽,那么天真,那么健康,那么无忧无虑。格拉吐了一口气。妹妹也和自己一样,像了母亲,而不是别的什么人,特别是村里的别一个男人。这是他一直隐隐担忧的事情。
格拉转眼去看窗外的天空。
雪后的天空,一片明净的湛蓝还有彩霞的镶边。
火塘上,烛着熊肉的锅开了。
假装睡着的桑丹笑了,说:“我得起来,肉汤潽在火里,可惜了。”
格拉说:“你一起来,就像我在生娃娃,像是我这个男人生了娃娃。”
母亲笑了,格拉也跟着笑了起来。还是我们机村人常说的那种没心没肺的笑法。
水电站
他们真是些神气的家伙。
特别是在机村孩子们眼中,地质队的这些家伙比工作队还要神气。
工作队也很神气,但是,他们的神气是在眼睛里。他们脸上所有的部分都在笑,但眼睛里却满含着骄傲的神气。他们像军人一样背着背包,来到村子里,开过会后,又一一地分住到贫下中农的家里。他们说:“毛主席教导我们与你们同吃同住同劳动,与你们一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来了。”
但地质队就不一样了。
他们自己带着一队骡子,驮着帆布帐篷,可以折叠的床、桌子和椅子,还有各种各样的尺子与镜子。他们出现了,看见机村这么大一个村庄,但就像没有看见一样。他们赶着驮着各种稀奇东西的骡子队直接就从村子中央穿过去了,对这么大个村庄视而不见。完全是一种见过大世面的样子。每次来的地质队都是这样,径自穿过村庄,一直往河的上游走,一直到转过山弯,把营地扎在比磨坊更远的林边草地上。不要看他们这些人大多都戴着眼镜,但他们什么力气活都会干。从林子里砍伐小树,扎成能撑起帐篷的支架。用铁锨在地上挖坑,转眼之间,里面就烧起火来,埋锅烧饭。有人甚至耐烦用斧子劈出一般高矮厚薄的白桦木拌子,做成漂亮的栅栏,把那几顶帐篷围在中间。这些事情,机村的男人都会,工作队的人是不大会干的,但这些人会。
还有一些就是机村人没有见过的了。他们伐倒粗壮的杉树,用粗壮的树干搭起一个结实的平台,在上面安装上一些机器。有点风尾巴就摇摇晃晃,风稍大点就滴溜溜转个不停的东西是风向标,用这东西是要看出风的大小与方向。他们还在一个箱子里装上一些漂亮的玻璃容器,每天,都有人爬到上面,在一个厚厚的本子上记下瓶子里装了多少雨水或露水。他们还把一把长长的铁尺插在水里,每天记录水涨水消时,贴着水面的尺子上的刻度。
然后,他们就上山下涧了。用锤子在岩石上叮叮当当地敲打,用不同的镜子去照远山、照近水。太阳好的时候,他们就把折叠桌子打开,铺开纸,把记在本子上的数字变成一张张线条上下不定、曲里拐弯的图。
他们就这样忙着他们的事情,对近在眼下的机村不管不顾。偶尔,伙夫会去到村里采购一点蔬菜或牛奶。
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太神气了,在他们眼里机村就像不存在一样,大人们都尽量不到地质队扎营的地方去,也假装出一副视而不见的样子。但我们这些小孩子却是克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的。我们总是偷偷溜到男哩去,停停转转的风向标下面的营地尽是新奇的事情。那些神气家伙,任我们聚在栅栏外面探头探脑。直到有一天,老师突然宣布,地质队邀请机村小学全体学生前去参观,并要为我们组织一个科学主题日。我们头一天得了这个消息,人人都念念有词:科学主题日,科学主题活动日。第二天,这个词在我们嘴里就很顺溜了。但是,老天爷呀,看看我们这群面孔脏污、衣衫破烂、乱发上沾着草屑与尘土的孩子吧,哪里有点能跟科学沾上边的样子啊!
但是,我们去了。老师让我们排成两列纵队,前面打着一面红旗。老师依然吹着他那只哨子,指挥我们迈出整齐的步伐:
一!一!一二一!
一!一!一二一!
他的哨子闪闪发光,哨声也一样闪闪发光。
开始的时候,我们的步伐是整齐的。整齐的步伐使弯曲的村道上扬起了尘土。可是,转过山弯,过了磨坊,看到地质队营地上飘扬着的那些彩色的三角旗后,大家的心立即咚咚乱跳,步伐立即就凌乱了。
地质队把总是半开的栅栏门完全敞开了,把一群小兽一样慌张而又激动的野孩子迎了进去。那天,我们看他们画图,看他们给岩石标本编号建档,学习使用那些不一样的尺子,学习辨识那些收集雨水的瓶子上的刻度。每一处地方,都有一个人出来讲解,但我必须说,光是可以亲手摸摸那些东西,就让我的心跃动不已,至于那些解说,我可—句都没听进去。最后,他们把折叠的桌子排成一溜,请我们坐下,桌子上面摆上了花生与糖果。除了特别馋嘴的人,大多数人都没有勇气把糖果上漂亮的玻璃纸剥开,把那甜蜜的彩蛋融化在嘴里。但是,我们出手的确是太快了。手从宽大的藏袍袖子里像蛇吐信子又收回信子一样,飞快伸出,抓到一颗糖果又飞快地缩回。糖果,像是一颗颗某种秘密的欣喜被藏进了袍子里。
那些人他们笑了,这种很平淡的笑容,让我们紧张激动的心情终于松弛下来。但是,到这个时候,科学主题话动日已经到了结束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