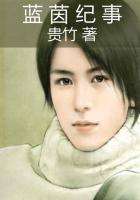赵祁泽讨个没趣,一走,傅好便开始收拾东西,像傅好这样戍卫边塞,要在卫所劳作的人,是不分地的,每年春末,秋末分两次粮食,今年春末的,傅好还没有领,所以厨房的粮食,就剩下几把小黄米,几块番薯,和几条年里腌制储存着的肉干,归一归,用一个小麻袋装了。细软就是几件衣服,一年四季就十来件,来回不过刚刚够换洗而已,穿一套,一套打包,两条被褥,都在年前加过新棉花,还有几件硝制好的毛皮,捆在一起,这么些加一加起来,只有一担重,就是全部家什了。最后把家里的银钱带上,傅好不在吃用上亏待自己,打到猎就吃肉,吃不了再买,得了钱买盐买油的,从不手软心疼,能赚也花得出去,所以,积累至今,靠打猎和马车拉人拉货,只攒了三两银子和五吊铜板,大宗还是穆九百给的聘礼,一个五两重的银锭子,一支二两重的金包银钗头刻了两朵桃花的钗。穆九百也不容易,家里老子,老娘要养着,兄弟姐妹有是有,每一个养到大的,都夭折了,所以,一个帮衬分担的也没有,攒这么不到十两的银子,就是全部的老婆本了。
两三年来,傅好再没戴过金银首饰,去卫所牧羊都是用发绳扎头发,包上头巾,余闲簪的都是木簪,就是自己捡个树枝削一削就能戴了,耳洞插着茶叶梗。这一次出门,傅好换下了姑娘家的发髻,第一次梳上了妇人头,戴上了桃花钗,傅好有了婚契,就算还没有正式抬过门,也是穆家的媳妇了。妆扮好,家里没有铜镜,傅好特意打了盆水,借着月色投在水里的光影,傅好看见了自己久违的容颜,如六月盛开,迎风摇摆的莲花一般,眼神婉转,风情万种,艳丽的眉宇间似乎带着一股蛊惑人心的韵味。傅好愣神着摸着这样的脸,踢翻了水盆笑了,笑容里,充满了魅邪。
傅好其实有几分冷情的心性,不忧聚散,家风巨变,一朝凤凰身落在泥泞里,要是情太多了,整个人早疯魔了。多情空自扰,还是冷掉了血,冰住了情的好。所以傅好连夜把行李装上马车,也没顾念着给周围的人辞行,对住了两三年的安塞县毫无眷恋,悄然的在夜色里驾出了县城,往延安府城里走。
傅好是戍民,朝廷为了防止边地的戍民往内流窜,三令五申戍民不能走出所在府城的范围,所以,傅好没有路引可以出延安府的城门,进西安府的城门,倒是要去甘州,凭和穆九百的婚契可以先过去,不过,之前怎么也要先和穆九百搭头。最好是把穆九百也带上,两人一起回甘州,把亲事办结实了,两口子把日子过上。正像傅好向赵祁泽叫嚣的那样,没有明天的人,管什么将来,人活百年是活,没百年,就活十年,得过且过。
傅好进了延安府,找了一间脚店落脚,再去府衙打探了消息,知道周王府的人还在西安府,便找了一个私人来往于延安府和西安府代传书信物,代递物件为业的伙计,因为穆九百不识字,傅好就让他代传口信过去,让穆九百赶快回来,差事没有办完,请假也要从军中出来。那个伙计自己有马,来回不用一天时间,傅好又是一刻也等不得的,口信就要传过去,和傅好一通议价,收了傅好一两三钱银子才肯上路传话。
傅好从白天等到黑夜,从天黑又回到天明,在脚店守到第三天中午,心里已有数了。这么两天,周王府的人,已经办完在西安府的事,回程经过延安府落脚。傅好接到消息又到府衙等人,穆九百是什长,手下九个兵,凑巧,先碰见了一个穆九百手下的兵卒,终于得到了穆九百的下落。
边地独身的男人多,因此,边城娼馆繁华,边城娼馆的繁华不像京城那样,有才情的名妓,靡费的曲乐,醇香的美酒,雅致的楼宇和精致的菜肴,那样的规格,边城的男人们没几个消费得起。边城娼馆繁华,是另一种繁华,边城娼馆多而杂,许多私娼暗窖,三教九流。边城的娼馆里多是没有什么才情,纯粹陪男人睡觉的明娼暗妓。最好的娼馆也就是几个小院子相互套着,点上粗制的烈酒和大块的肉饼。
傅好穿了一身灰白色短打葛衣,腰上系着马鞭,手持木棍站在门面和普通人家无异的门前,果然进不得门就被一个在门前负责迎来送往的,抹着浓艳的胭脂,带着两朵粉红色大花,年近五十的老鸨拦住,捏着帕子调戏道:“小娘子,我们家里,只接待男客,不接待女客,你要是找人呢,就远远的站外面等着,客官们那什么完事了就出来了,你再逮,你要是……呵呵,以你的模样是玷污了,妈妈我,好好给你留几个财大气粗,年轻力壮的情哥……。”
虽然傅好穿着像个男人,却是没有掩饰女儿身,梳着妇人头呢。老鸨做皮肉生意的,什么官司没见过,一看,就知道是丈夫背着小娘子出来偷腥了,眼前的这位小娘子是漂亮,自己手里的女儿们没一个比得上的,不过,家花没有野花香,男人就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有几个钱,就要尝尝新意儿,房里放着如花似玉的婆娘,就喜欢在外面勾搭,尝回野味的的男人多得是。娼馆门前隔三差五的,就要上演一出抓奸讨债的闹剧,基本都是家里婆娘知道汉子贪嘴了,为了野花满手撒银子肉疼呢,有娘家强势的,邀了娘家人来闹,只是,这么一个年轻娇美的小娘子,一个人不知险恶的敢往这地方闯,也不怕有来无回。老鸨还是片好心着,放荡的,恐吓了几句,把不懂事的小媳妇吓退了,就算积德了。
不过,这次老鸨五十年的人生阅历看走眼了,傅好一鞭子卷住那老鸨的脖子,拉近身来,冷冷道:“开门做生意的,怎么惯得你们挑三练四起来。老娘今天就走一个给你看看。”
傅好的父亲从小被祖父扔在军中,养得一口粗话,傅好小时候,就听了不少父亲爆出的粗口,再近年里耳闻目染,见人说人话,见鬼说给话,什么字眼都能说出口,毫无转换压力。别人犯浑,你得比他更犯浑,才压得了阵仗。
开娼馆的,最容易打架闹事,所以,娼馆里,是常年雇佣着几个身强力壮的打手,防备着,外面的人进来砸场子,也要教训有些爷们儿,吃霸王餐,穿上了裤子不给钱,所以,一听老鸨话说一半,被人卡住了脖子,就知道砸场子的来了,立马从蹲着的门房出来,一个小娘子而已,专业的,一丝怜香惜玉也没有,抡起拳头就上。
“呼……。”只听得一声强劲干脆的棍风,打手的拳头还没有擦在傅好的身上,一根粗木棍子如夹着万钧之力,堪堪停在自己的喉结上,接着对上一双凛冽的眼睛,三月,微凉的春风里,愣是一下逼出了一身冷汗。
打人不打死。娼馆里那些男人下半身引发的斗殴,只捡痛的地方下手,却是不会往死穴里招呼,这是行规。会不会打架,一出手就知道有没有,这位姑娘手太狠,心太黑,又不管道上规矩,一出手就玩命,还有玩死别人命的劲力。打手都是欺软怕硬,赚点钱养家糊口的,犯不着玩命,自知拼不过就认怂了。
傅好用鞭柄拍拍老鸨的肩膀道:“你是要我挨个一间房一间房的搜,把你的生意全搅黄了,还是你给带个路呢,周王府铁骑营卫队的人在哪里?”说到后半句话,傅好不自觉的,就加重了威势。
军营里还有营妓呢,当兵的****不犯军法,只是,军里的营妓是人多肉少,摊不过来,所以,当兵的,放出来,爱那事的,没婆娘的,就野路子凑合了,边地的娼馆,大头都指着当兵的赚钱呢,这个娼馆的姑娘们,在延安府还算有名气,才能拉到周王府铁骑营这单生意。
老鸨是最有眼里劲的,爪牙都拔了,顶什么顶,立马认栽,乖觉的,陪笑道歉,被傅好提着后领走前头带路,沿途看好戏的恩客姑娘们也不知道怕,也不知道躲,娼馆里闹剧见多了,一个和老鸨相熟的恩客还远远打趣道:“老妈妈夜里走多,绊脚了,哪来的,那么标致又凶悍的小娘子呀。”
老鸨早有把握,看傅好穿戴就知道,她有几分本事,没什么来历,有来历的,谁会抛头露面的来这种腌臜地方,因此贱兮兮的吆喝起来:“来找我的女儿,也不会把后面的脚印抹干净,这不,寻着印儿来了,谁家的河东狮呀,打上门来了。”
周围一圈看热闹的,全都是一场哄笑,也不知,哪个男人,有福气,收服了,这么个标致凶悍的娘子,却又没本事,吃了一半,消受不了,跑娼馆河东狮吼来了,哈哈哈!
眼睛嘴巴,长人家身上,傅好管不着,也犯不上生气,一路上,冷着脸到了铁骑营包下的院子,放开老鸨,抬腿一脚把门踢开。
房间里,男男女女歪七倒八,三三两两搂着快活,空气里弥散着,酒味,肉香,就地交欢纵情,散发出来的,腥膻味和口水声。傅好面无表情的掠过一群半裸的男女,把视线停在一个被女人骑着,二十多岁,面庞硬朗,身形魁梧的男人身上。
骑在穆九百身上的女人,并没有和他真正交合在一起,只是一手伸到他的裤裆里挑逗,一手揉着自己的胸脯,半醉微醺的媚样儿,看见外面踢进来的女人,见了这样声色的场面,没有惊慌,没有撒泼打滚,冷傲的盯着自己手下的男人,眼睛深邃,不知深浅,不怒而威,不知觉的,就把手从裤裆里拿出来,又从穆九百的身上滚下去,往外爬了几步。
傅好随手抄起一壶满满的热酒,稳稳的抬手,缓缓的,从穆九百的头顶浇下,穆九百浑浊的双眸渐渐清明,在认出了眼前一双绝美的眼睛后,没有意外,没有懊悔,却是痛苦的,手颤抖着抹了一把脸,合上了自己的眼睛,不敢和那双眼睛对视。
傅好俯下身来,逼到穆九百的脸前,沉重的问道:“你悔了,不敢娶我了,是不是?”
穆九百满脸的酒渍,或许还掺了泪水,口吐酒气,脑袋却是清醒,哽咽的道:“爱慕九娘的,是将军,穆某凭着一身血勇……将来也能做上将军,就是没有这个命,死在了半路上,也是无愧于九娘……可是,爱慕九娘的,是……是天家,上天之子,穆某自知草贱,一辈子,都是趴在地上的人……家中尚有父母……的确是……不敢了!”
“还你的聘礼!”傅好从衣袖里掏出五两的银锭子,又从头上拔下桃花钗,拍在桌案上。
死要死得明白。
只差一天,还是没能逃出去。
世上所有的人,都活着强权之下,又怎么能,苛求,一个男人,仅仅是为了一个女人,压上全家的性命,去抵抗强权。
穆九百摸着钗头两朵并蒂的桃花,这个桃花样,还是傅好自己画的,年前辗转送到甘州来,让自己找人打出来,现在花在人非。穆九百手一用劲,就把钗头的花样抹了,想对转身而去的傅好伸手,手却是有万斤,抬不起来,只好这么着道:“九娘,穆某到底还是无能懦弱的男人,辜负了九娘的深情,九娘你……不是寻常的女子,是我穆某无福,无缘,配不上你。”
傅好扭过头来,无怒无泪,平静的面容有勾魂夺魄般的魅力,是因为……绝决:“你因为顾念了自己的性命,不敢娶我了,其实,傅好爱惜自己的性命,也胜于旁人,你我,是一样的人,没什么配不配得上,是我们这一辈子,缘分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