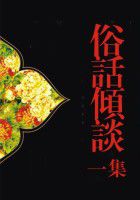对于这次不期而遇的重逢,惊喜的不只是李家人。赵、高二人的惊喜激动甚或苍凉,并不亚于他们。因为他们原本是亲兄弟:哥哥赵明远本名马向方,弟弟高继古本名马向道,出自武学世家,祖上四代都是镖师。其父深知此道凶险,不想让儿子入行,赵明远因而进天津卫当了炉房学徒。高继古虽然也有童子功,但未废读书。后来有人盗掘古墓,发掘出一批金银器皿,想运到天津卫炼化销赃,便找到马镖师,让他解运到长子供职的炉房。镖银余外,愿赠宝剑两口。镖银马镖师并不稀罕,多年走镖,不过是趟正常生意,但那两口剑,他委实喜欢,于是便接镖起运。最终镖也运到了,金银也炼化了,但却被盗掘者的仇家告发。盗掘者早有准备,已经远走高飞,麻烦便落到炉房与马家身上。
盗掘古墓,本为不义之财;徐徐追赃,也算合情合理。然而事到如今,性质完全改变。官府找不盗掘者,便揪住炉房与马家不放。炉房几乎破产,已是师傅的赵明远自然也没了生计。这还是小事,关键是马家因此家破人亡。后来才知道,这是个精心策划的阴谋。他们的目标,就是马镖师的镖局。无奈之下,兄弟俩只能逃往他乡。后来听说父母皆在监中折磨致死,二人便联合父亲的徒弟潜回家乡,手刃仇人全家的男丁,然后亡命天涯。他们俩人手一口剑,化名分开,各自求生。赵明远的谐音是鸣冤,高继古的寓意是记苦。三十年之后,二人都已老去,不期在此地以此种方式重逢。起初他们并无自我解密的打算,然而初见的惊讶、外貌的相似,大家都看在眼里。等对李世登的兴趣的热度退去,他们便成为焦点。问姓惊初见,称名忆旧容。久别重逢的感慨,终于冲破戒备的堤坝。
办几堂红学当然没问题。和盛钱店手指缝并紧点,挡住的碎银子便已够用。不过李世登的要求,并非简单的红学。他要八叔多出点血购买快枪。冷兵器时代正在过去,必须要有新式武器。这一点,李玉亭也不反对。他可不想和盛钱店的银钱,最终要撂到井里保存。大李家的红学虽然创办较早,但快枪很少。他如今后来,理当居上。
就这样,赵明远和高继古便跟着李世登,回到李家寨操办红学。买来枪聚起人,一切走上正轨,李世登却再度远走他乡。他还是要革命,要与组织联系,接受委派。如果说这仅仅因为人们通常都在惯性中生活,李世登也是这样,那显然有辱他的革命情操。事实上他这次的逃离,还是因为麻烦。
李世登回来后不久,全国各地相继出现一本书,是本很薄的小册子,跟当年梁漱溟的文章以及《革命军》差不多厚,名曰《禹县屠城记》。国民二军屠城的详细经过一览无余,种种惨状令人发指。书未署名,以曹部某营书记官的视角,回望惨案,对胡景翼、岳维峻之流大张挞伐。小册子最早出现于郑县开封,但形成全面影响,还是在京沪两地。刚刚继任豫督的岳维峻恼羞成怒,下令严查,随即怀疑上了京汉线的节点信阳。
毫无疑问,此为李世登的手笔。这小子其实根本就没闲着。这让他同时开罪了国共两党的上级组织,以及河南的当权派岳维峻。尽管岳维峻当时尚未锁定目标,但已展开搜查。李世登随即决定,带着手稿以及禹县红会的材料离开信阳。一方面辨明是非,因为禹县屠城,本来也并非死去的憨玉琨所为;二来他要跟上级组织据理力争,以捍卫理想。
然而信阳搜查甚严,尤其是铁路交通。李世登带着手稿材料,那是见证,自然也就是祸端,要带出去多有风险。怎么办呢?李玉亭想起了老朋友李立生。只有教士能免除搜查。
那时李立生已年逾七十,头发斑白。闻听来意,他的本能反应是拒绝。中国国内的各种纷争,他们均无意介入。然而当李世登拿出手稿,详细讲述屠城经过,李立生立即打消疑虑:“我可以帮你。但你必须背会主祷文,学会画十字。”李玉亭道:“你这不是趁火打劫吗?这样能收到真正的信徒?”李立生盯着李玉亭,试图找回在平安夜歌中落泪的那个人,但没有成功。他微微笑道:“你不要误会。这只是为了应付盘查。”
李玉亭一听再无二话,但李世登却不情愿。李立生很奇怪:“你们的一些革命领袖,还有冯焕章将军,不都是基督徒吗?”李世登摇摇头道:“别跟我提冯玉祥!国民二军就打着他的旗号!再说我是国民党员,也是共产党员。我们都是无神论者。”李立生悲天悯人地看看李世登,再看看李玉亭,无奈地耸耸肩:“果真这样,那我爱莫能助。上帝也不喜欢敌对者。”
说来说去,李世登最终只能低头。
教会有个美国牧师,中文名字叫白约翰,也是信义学校的教师。他正好要带着六岁的女儿白宝珠去上海看病,同时购买教学仪器。这些年来,政府对教会学校一直心怀警惕。如今教育部已经通令全国,所有学校都必须教授科学。信义中学没有实验仪器,得去上海置办。经李立生协调,白约翰将手稿放进行李箱,由李世登扮成仆人提着,通过信阳车站上老陕的严密盘查,经汉口顺利抵达上海。
北门外的和盛钱店屡遭劫掠。上次吴佩孚的败兵作乱,店铺几乎被烧成灰烬。修复之后重新营业,生意一直清淡。李立生将之归结为没有得到上帝的祝福,李玉亭听了只是摇头。找来龚先生,他的结论是风水不好。和盛钱店的房址,过去是个火神庙。钱店建在那里,不可能平安。
怎么办呢?简单。另外再建处房子。虽然还在北门外的繁华商业街上,却是龚先生手持罗盘测定的结果。一俟新房盖好,钱店立即搬来重新开业。
那时已是十月。直奉三战已经打响,孙传芳出兵上海,攻击奉军。苏联为此特意拨给孙军两百万发德国型号的子弹。河南局势相对平静,信阳百姓还是一如既往地抽烟打牌。忽一日,有人送来一块精美的木雕山水牌匾,图案是王维的诗意,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旁边刻着八个字:日进斗金,财源广进。泉与钱基本就是兄弟姊妹,这份贺礼因而既雅致又妥帖。谁送的呢?两条红绸子裹在首尾两端,看不出上款与下款,抬匾的两个小伙计也说不知。李玉亭很好奇,正要揭开红绸子探秘,一个戴墨镜穿西服的洋派人士,忽在土耳其项克敏的簇拥下笑着进得门来:“李先生,别来无恙!”
来者正是和盛钱店的债务人,加中将衔的陆军少将袁家骥,头发梳得油光发亮。李玉亭立即抱拳施礼:“哟,袁将军!您老一向可好?请坐请坐!”
袁家骥摘下墨镜,昂首阔步,入室落座:“承蒙你挂念,还算不错。今天路过,闻听贵店换址经营,特来致贺。咱们的账目,也该交代交代。上回走得的确匆忙了点。”
李玉亭以为袁家骥要来结账,赶紧吩咐人去取两栋袁家楼的房契,以便璧还将军:“每次来驻军,长官都要当成司令部。我可是一天都没住过。”袁家骥摆摆手道:“这个暂且不必,你先替我收着。袁某做事向来有始有终,你尽管放心。他们爱住就住,你若愿意也只管住。房子没人住,长时间不沾人气,还爱坏呢。”
袁家骥此行的主要计划,是南下汉口搬兵,以河南乡绅代表的名义向吴佩孚请愿,请大帅出兵河南,吊民伐罪。他代表官绅,请李玉亭代表豫南和商界。李玉亭闻听,本能地抬头看看门外。袁家骥笑道:“别紧张,老陕的主力都在北边。”李玉亭道:“这是军国大事,我一介草民,岂敢多言?”袁家骥道:“你就说吧,我的欠款柜上还收不收?要是想收就跟我走。等大帅打回来,再给我个差遣,马上就能还上。连本带利。”
欠款的确想收回,老陕也的确是太坏。客观而言,虽然吴军的兵变后果最为严重,但那毕竟是特定时期。吴佩孚坐镇洛阳时信阳的局面最为平静。修公路通电话,这才是真正的伟大变化。吴军军费虽也只能摊派给百姓,但从不直接勒索个人。而老陕进入河南后口号像冯玉祥,军纪像张敬尧。
不过话虽如此,其中的水未免深了点,下面是大鱼还是漩涡,难说。而且目前信阳不是已经基本没有老陕了吗?李玉亭有疑虑,袁家骥有下文:“有大帅在,还怕老陕?等河南安定,我可以获得差遣,尽快还你的欠账;你迎驾有功,大帅至少还不得放你个县知事?”李玉亭脱口而出道:“什么县知事,他要给我一个道的责任呢。”袁家骥笑道:“还是啊。就算你南下汉口探看靳二哥,顺带办点事儿呗。”
这话听起来颇能入耳。颐庐旁边的子弟学校已经开办,今秋李世业即将入学。那时国共两党全部进入信阳,各种思潮泛滥,公祭孙中山和声援“五卅运动”时表现得尤为明显。学校师生几乎全部参与,而李玉亭正急于让长子与之绝缘。他很想面谢靳二哥,毕竟那是子弟学校。探看二哥拥戴大帅,两全其美,走吧。
路上袁家骥雄心勃勃地表示,等他东山再起,还要回信阳做生意,开运输公司。信阳向东边几个县份的公路正在修筑,部分县城已经通车。这不就是天赐良机吗?浦信铁路半途而废,正好由汽车沟通秦淮。车轮一动,自有不尽银元滚滚来。
真是英雄所见略同。上一年北京开通电车,已经引起李玉亭的注意。唯一的疑虑,只是资金。袁家骥似乎明白李玉亭的想法:“你别操心钱。我兄弟专门经商,资金雄厚。就我这资历,干个豫南镇守使总归没问题。到时候我们兄弟合股便是。对了,你愿不愿意入股?不行就派你经理!”
李玉亭心里一动。他欠柜上的钱要是能换作股本,倒也不错。如今钱店业务已是夕阳箫鼓江河日下,主要因为货币贬值太快。经营钱店,肯定不如开运输公司。这就像当初的京汉铁路。不过人家终究是将军,提这话伤面子。袁家骥见状哈哈一笑,拍拍李玉亭的肩膀道:“八爷,别老惦记你那些账目。那不过是些数目字,无实际意义。告诉你,我们袁家很快就会起来的。现在最紧要的事情,是赶走老陕。一旦河南局势平定,不就是咱们的天下吗,那时候要啥没有?哈哈。”
吴佩孚的司令部已经组建,但尚未挂牌。这样的请愿者虽然令人欣慰,但他却颇为矜持,只是微微点头欢迎,顺致辛苦:“鸡公山景致不错。我找个夏天,上去避暑。”李玉亭说:“信阳绅商各界,翘首期盼大帅光临。老陕糜烂地方,残害百姓,请大帅义师早日吊民伐罪,救我等于水火。”吴佩孚眼光一闪:“这样的部队,必须驱逐。上次在信阳抢劫的祸首,我已经惩处,你回去替我道个歉。你们一路劳顿,先去用饭吧。”
汪崇屏奉派陪他们吃了顿饭。饭后再见靳云鹗,他却没那么高兴:“八哥,这事儿你怎么能掺和呢?本来我们跟焕章早有盟约,一同讨奉,可大帅始终态度游移,直到现在还叫讨贼联军,不明确目标指向。岳维峻终究属于国民军系统,我们怎么能打他们?直军田维勤、陈文钊和王为蔚三师人马,如今都在岳维峻麾下。原说由我率领他们征鲁,现在大帅这样,岳也改变态度,不让我从河南经过,三个师更不能再提。当此时刻,你们还来请兵北伐,不是添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