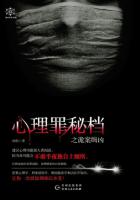凯莉·顾威和同居人马特·塞尔斯面对面坐在小桌子前(“男友”听起来太年轻了,“另一半”听起来太老成了)。他们一起吃青酱羊奶干酪阳光西红柿披萨,还有意大利烟熏五香火腿卷,配上一瓶500美金的一年份美洛红酒。厨房的电视转到纽约第一频道,因为马特想看新闻。对凯莉来说,二十四小时联播的新闻台就是她的情敌。
“对不起。”她又对他道歉。
马特轻扬嘴角,手持着酒杯在空气中慵懒地画圈圈。
“我知道,这不是我的错。但我知道我们都希望能两人单独过周末……”
马特撩起挂在领口的餐巾擦擦嘴:“他经常这样妨碍我们独处,我说的不是扎克。”
凯莉看着第三张没人坐的椅子。不用问,马特当然很期待她儿子这周末出门。他们的抚养权争夺战旷日废时,现在由法院调解,所以扎克这几个周末都会到曼哈顿下城,住在伊费的公寓里。这表示,凯莉可以和马特亲昵地在家吃顿饭,马特对性生活的期待也燃烧着,这点凯莉也很愿意配合,所以她自然会破例比平常多喝几杯酒。
不过,今晚却不行。尽管对马特感到抱歉,但她自己其实是有点高兴的。
“我会好好补偿你。”她说完便眨了眨眼睛。
马特的微笑不掩失落:“你说的哦。”
这就是为什么马特总是让人很安心。经历过伊费暴躁善变的情绪、吹毛求疵的个性、冲动急切的态度后,她需要像马特这样步调较慢的小船。她嫁给伊费的时候太年轻了,做了太多让步——屈就于他的需要、野心、渴望,成就了他的医疗事业。如果要她在任教的皇后区杰克森高地第69公立小学里给班上的四年级女生一点建议,她会说:千万不要嫁给天才,尤其是帅气的天才。和马特在一起时,凯莉觉得很自在,其实还有点享受在感情里略居优势的地位。现在换别人来迁就她了。
白色的小型厨房电视里,所有人都在大肆报道明天的日食。记者试戴各种不同的墨镜,根据保护眼睛的程度来评分,同时又介绍着中央公园里的纪念衫小摊贩。印着“日食之吻,天地见证”的上衣最抢手。主播要观众锁定明天下午的“现场直播”。
“一定很精彩。”马特这么说只是想让她知道,他不会因为失望就毁了一整晚。
“这是天文盛事,”凯莉说,“不过他们报道的好像是另一场暴风雪似的。”
《新闻快报》的画面进来了,通常凯莉看到《新闻快报》就会赶快转台,不过这则新闻的诡异程度引起了她的注意。电视上,记者远远拍摄一架飞机停在肯尼迪国际机场停机坪上的画面,周围有一圈工程照明灯打在整架飞机上,旁边还有好多车辆和小人,不知情的人还以为飞碟降临在皇后区。
“是恐怖分子。”马特说。
肯尼迪国际机场离这里只有十英里。记者说画面中的客机顺利降落后却全机断电,目前无法联络上任何机组人员或乘客。机场已执行预防措施,所有起降全部暂停,原定降落于肯尼迪国际机场的航班都改至纽瓦克机场或拉瓜地亚机场。
她一看到新闻就知道伊费是因为这架飞机才必须带扎克回来。她现在只希望扎克赶快进家门。凯莉是最英勇的战士,而家代表着安全。这是全世界她唯一能掌握的地方。
凯莉站起身走到厨房流理台的窗边,将灯光调暗,抬头看住宅区上方的天空。她看到飞机的灯光盘旋在拉瓜地亚机场的上空,光点一个一个连起来,就像暴风圈一样。她从来没去过美国中部,在那里,你在龙卷风还有几英里远的时候,就能看见它朝自己的方向奔腾逼近。虽然没亲眼目睹过龙卷风,但她觉得现在的感觉一定和那很像。有个她无法撼动的力量朝她袭来了。
伊费把疾管局配给他的福特探险家停在路边。凯莉在这小坡上买了一座小房子,坡道周围都是两层楼的洋房,家家户户门前都有低矮的篱笆、整齐的前院。她走出来到水泥人行道上,怕他进入她的家门,她通常把他当作流感病毒,死命抵抗。
发色更金、身材更纤细的凯莉还是那么迷人,不过她已经不是他认识的那个人了。变化真大。或许在这个家的某个地方(可能是储藏柜深处某个布满灰尘的鞋盒里)还放着他们的结婚照,照片里无忧无虑的年轻新娘掀开头纱,仍笑意盈盈又娇媚地望着盛装的新郎,两个年轻人沉醉在爱河里。
“我本来把整个周末都规划好了,”他比扎克早一步下车,打开低矮的铁门,只为了抢先开口,“但这是紧急事件。”
马特·塞尔斯走出明亮的门口,来到她身后,在第一阶上停下了脚步。他的餐巾还别在领口,遮住了上衣口袋的席尔斯商标。马特是雷歌公园附近购物中心里席尔斯商城的主管。
伊费当作没看见他,继续把注意力放在凯莉和扎克身上,他看着扎克走进前院。凯莉给扎克一抹微笑,而伊费忍不住想:她是不是觉得“看伊费和儿子分开”比“周末和马特独处”有趣?凯莉拥扎克入怀,保护意味浓厚:“小扎,你还好吗?”
扎克点点头。
“我觉得,有点失望吧。”
他又点点头。
她看到他手上的盒子和电线:“这是什么?”
伊费说:“扎克的新电玩。我这个周末借他玩。”伊费看着扎克,他的头抵着妈妈的胸怀,两眼无神看着前方。“小子,如果我能脱身的话,或许明天,希望明天……反正只要有办法,我就会回来找你,我们可以把握剩下的时间玩个痛快,好不好?我会弥补你的,你也知道,对不对?”
扎克点点头,但眼神还是很茫然。
马特在门前阶梯上喊他:“来吧,扎克,我们看这玩意儿要怎么安装上去。”
眼前的马特显得可以依靠、值得信赖,凯莉确实把他训练得很好。伊费看着马特搭着儿子的肩膀走进屋里,扎克回头看伊费最后一眼。
现在就只剩他和凯莉单独站在这小方绿地上了。在她的后方、屋顶上方,等待降落的飞机闪烁着灯光不断盘旋。先别去数有多少行政和执法机构在等他了,至少整个运输网现在都在等这个男人,而他面对着一个说已经不爱他的女人。
“就是那架飞机,对不对?”
伊费点头:“ 机上的每一个人,他们都死了。”
“全部?”凯莉的双眼灼烧着忧虑,“怎么会?是什么原因?”
“我就是要去调查清楚。”
伊费现在感受到这份工作的急迫了。他已经搞砸了和扎克相处的时光,不过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他现在就得离开。他的手伸进口袋里,拿出个印了条纹的信封交给凯莉。“明天下午的球赛,”他说,“要是我不能在明天下午前回来……”
凯莉瞄一眼门票,看到票价时忍不住扬起眉毛,然后又放回信封里。她看他的眼神几近同情:“只要你别忘记下星期要和肯普纳医师见面就好了。”
家庭困扰治疗学家,就是他要决定扎克最后会跟谁。“肯普纳医师,没错。”他说,“我一定会到。”
“还有——凡事小心。”她说。
伊费点点头便驾车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