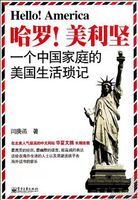原本打算五一出去逛逛,因事改到五二了。天还不错,临时决定去公园转转。
前年来过一回,真真是有了时光如水的感觉,一晃的事,儿子天赐已经初中了。记忆里总是有个小小的身影在我身前身后晃来晃去,都是几多年前儿子成长时留下的影像碎片。公园里他坐过的石头大象还在,却是一些比较大型的游乐设施不见了踪影;小猴拉车和转转椅在那不紧不慢的转着,坐着几个很小的孩子。这些可爱的小东西当年也是天赐的最爱。
人也不多,冷清的公园给人感觉象是要关门的样子,还有工人在往地上摆放着盆栽,那花开得甚好,红的黄的,正是花的花季,就象天赐此时,十几岁,最是饱满,最要绽放。
只是天赐比我当年是要苦的多了,生活上虽还富足,精神上压力却是重如山石,整天有着写不完的作业,能出来玩很是金贵,安排了又安排挤出来一个上午。
园子逛够了,我也给渐渐温热的太阳晒暖,想回家了。儿子说反正不远,我推你走吧。十来里可不近乎,是他不想回家的一个借口罢了,我便不说破,由他一回。往常能由着他的时候不多,作业没完没了,想要这样那样是不得了的事,被老师罚,被老师找,都曾有过,虽然我不赞成现今的教育方式,但胳膊拧不过大腿,老师怎么说咱就怎么做吧,老师也有老师的难处,怪不到他们。
出来的路上,我遇到一个以前的邻居,因为搬迁,我们已经多年没见了。他当时开着一辆灰色奥迪,摇下车窗笑着要我停一下,问我是否还记得他,我想了半天不得不抱歉地摇头。他报了姓名,我这才想起来有朋友曾与我提起过,他早已不是当年的那个二愣子,而是某单位一个受人尊重的总经理了。
我们相互问了一下彼此的境况,说了几句客套话就道了再见。
天赐说这人真不够意思,有车也没说送送我们,我说儿子咱不能这样想,人家现在是单位的领导,事很多,身份跟我们也不一样,能停下来跟我们打个招呼已经很不错了。天赐说你总是替别人说话,我说你不认为妈妈说的是对的吗?可能你还小,慢慢就懂了。是啊,他才十三岁,哪里知道这些呢。我也见过比这个邻居当了更大官的人,并且曾经还是朋友,如今见了跟不认识一样,不再迎接我的微笑。
走到少年宫附近,路出现了叉道,天赐有点发蒙,我让他拐向左侧,他怕我说错了,可又没别的办法,他知道我一向缺少方向感,出门走稍远些就会迷路,但公园实在是来的太多次了,而回家的路也是直线。我让他拐一下只是想避开前面那些塞停的车,过了这道弯看到商场就算到家了。
这时,一个骑着摩托车的男子从我们身后赶上来,放慢速度,偏着头看我们笑,然后加速离去。天赐说这人用异样的眼光看我们呢。我说不是,人家是笑着的,而“异样”是好奇、古怪,很少有笑含在里面。他一定是在想:这个妈妈真幸福,有这样一个好儿子推着逛街。
天赐说是吗?我说是啊,就象你的心思,有时妈妈不懂,妈妈的心思你也不懂一样,咱们不能乱猜这些好心人的心思,我们跟他们无亲无故,他们不会伤害我们或看不起我们的是吗?天赐说哦;他们的行为都是善意的——我继续唠叨——我们要感谢他们的帮助和赞赏,这里面包括帮我们抬抬轮椅呀,让让路啊,问候啊,还有微笑的目光和奇怪的眼神。天赐嗯了一声,不知在他小小的心灵里是否能容纳下这些比较抽象的概念,希望在他成长过程中,那些良好的因素能逐渐扎下根来,做一个心地善良的人。
到家了,天赐打开作业本,我也打开日志,记下了这些流水账。
每一天的不同,都是我们的心智在注入不同的元素,厚重,而又成熟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