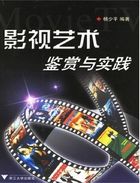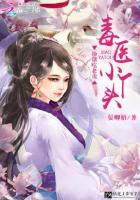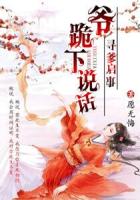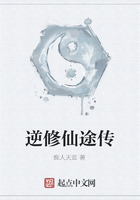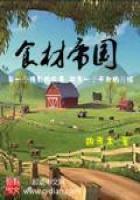1.
我见证过藤井树的青春热血。
那是茫然不安且中度伤感的年代,电影梦如同包裹在每个人头上的氧气袋,支撑着爱电影的鸡血青年在人潮中逆流而行。
2.
我们真正的相识是在可可西里。
这个形迹可疑的上海女记者是突然空降在我们面前的。鲜活得像一只春季的蜥蜴,花花绿绿且毫无节制地变幻着色彩,让那时已经在戈壁滩上待了将近四五个月的我感到一阵晕眩。她嘹亮的欢笑惊醒了整个戈壁滩,扑面而至的热情几乎淹没了整个剧组。
是的,藤井树就是这样的姑娘:质朴而热情。
她热力四射的热诚经常能融化四周的坚冰,令她在人生的征途上不断遭遇友谊的伏击;也能令她如同无人驾驶的蒸汽机车莽撞地冲上枕木已经朽烂的密林铁路,不知归途。
这十年,就这么看着她一路高歌冒着热汽地前行着,手心攥着汗。
3.
那天我们决定放弃在格尔木周边的拍摄景地,直接将剧组拉入可可西里腹地海拔4700米左右的五道梁。
制片主任默默地拿出一罐氧气瓶,把两根导管插入鼻孔,然后深沉地点上一支香烟:“你们上吧,我老了。”在他的身后,是二十箱氧气瓶。
“吸着氧还抽烟?您丫不怕炸死自己?”年代久远,印象中藤井树大致说了类似的一句话,随后从桌子上抄一个苹果拿起背囊,径直走到吉普车旁。
文艺女民兵-在那个瞬间,我默默给她起了这个名字,然后在心中流着热泪给她鼓了两下掌。
车队沿着青藏公路一路盘山而上,路边山谷里熊熊燃烧的卡车,远处的雪山,冰河前孤独的野牦牛,奔驰而过的野驴群都能让这枚只见过自行车群的上海女民兵发出阵阵尖叫;傍晚时分我们的车进入了五道梁地区。4700米的戈壁,开始显示其黑暗的力量。缺氧让车里一片死寂,藤井树牌复读机也开始间歇性断电,并咝咝啦啦发出各种令人担忧的噪音,直至最后陷入永久的沉默。
我回过头,看见她脸色苍白,惊恐万状地举着苹果。她把苹果转过来让我看,在她咬过的地方,一大片血迹。
高原反应,我们都习惯了。
随后在楚玛尔河边上,我们正在勘景,藤井树开始喷射性呕吐,两个副导演都扶不住她,她很快陷入了轻度昏迷,我们迅速把她送到最近的五道梁兵站医务所,在那里她做了一个决定:继续留在五道梁,完成她的采访。
4.
在写这些文字的时候,我隐约还会觉得自己肺部的两个痛点又开始疼痛,一左一右两个看不见的贯穿伤永远烙印在我的胸膛上。在五道梁拍到第二个礼拜的时候,我感觉我的肺部仿佛中了两枪,两个伤口从前胸一直贯通到后背,令人发狂的疼痛彻夜不停地折磨着我。
剧组从一百零八人减员到六十多人,每天都有人一头栽倒,被紧急送下山。留在山上的人都有一个显着的幸福特征,脑袋逐渐变大,肿得跟紫茄子一样。在这样惨烈的局面中,藤井树奇迹般地存活了下来,她不但活了下来,而且越来越健康、吃嘛嘛香。我们不多的口粮碰到这样坚韧的朋友,真是悲剧。她真的是-我们所有人都齐赞-高原的一朵奇葩。
她在现场,白天热火朝天地和各种藏族巡山队的小伙子谈笑,热火朝天地和摄影组的帅哥们聊天;晚上热火朝天地和我们在兵站外小餐馆涮各种白菜、大口喝青稞酒、大声唱歌;深夜陪着剧组病号在救护站打点滴-大声和护士聊天……这不会是假象吧,我猜她不但没好,应该彻底病了。
有一句话是说这种症状的:自从得了精神病,心情开朗多了。不会是高原缺氧让她彻底神经了吧-我暗忖。
她其实一直没有脱离危险,嘴唇已经是黑紫色,脸型也成功地从南瓜子升级做了南瓜。每天晚上兵站医务站都会给她准备一整瓶医用的氧气瓶,钢罐,一人多高,斜支在她的床边,供她很奢侈地整夜使用。我们探视她的时候,都流着口水凝视着她-身边的氧气瓶,心想,丫怎么还不走呢,这氧气瓶就可以-这是五道梁地区唯一的医用氧气瓶。
她是坚持到了最后一刻,坚持到了我们完成了可可西里腹地楚玛尔河地区的全部拍摄结束的那天,她才离开了我们。
她走的那天,剧组所有的小伙子都和她拥抱了,她貌似哭了,惹得很多人都哭了。
当看着她的车在戈壁滩上拉着一条浓烟越走越远的时候,耳边似乎又响起了她高亢嘹亮的笑声,一瞬间很多人突然明白了她这段时间给我们带来的快乐意味着什么。
5.
后来《南京!南京!》的时候,她又出现了,那次她号称是来看圆圆的。
再后来,《王的盛宴》的时候,她又出现了,这次她和秦岚打得火热。
看谁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见证了成长。
藤井树,就如同她的笔名,她的成长,就是一棵小树的成长。她总是用最热诚的心去拥抱友情,拥抱感情,几乎毫不设防,所以行业中形形色色的人都和她成为了朋友。
这本影评是她心灵的文字,我知道是她用心写的。我就不对她的影评进行吹捧了,反正中国电影走到今天这个状况,影评人起了一部分坏作用。很多影评要么是坟头的花圈,要么是鞭尸的刑具,要么就成了被收买的旗手。藤井树的影评让我看到了很多不同。有什么不同,大家自己去看。
其实我更希望这部书能让大家看到一个作者的心,一颗温暖的爱电影的心。我不想说她是伟大的影评人,我知道她心中有这个目标,她在走向那个目标;不过她内心泛滥的仗义和友善,经常会让她混淆对电影的热爱和理性评判的界限;但是她会迅速清醒,因为电影,永远是她心底不变的底线。
她在我心中,代表着永远爱电影的那一群人。她是我的好友,也是我的镜子。
再长的序,也有终结的时刻。
这篇序写到这里,我对自己很失望,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完整描绘出藤井树的十年;我没有描绘出我们的友谊,以及这种友谊见证的我们爱电影的岁月;我突然意识到我甚至不知道藤井树的本名。我曾经听说过一次,非常诡异的感觉,那个名字过于庸常,我想我一定是从我的记忆中刻意地抹去了。她在我心中应该只有一个名字:藤井树。
真正的老友,应该一起扛过枪,也是知道对方受过多少伤;显然我知道不少,且都是硬货。但是她心底的爱和善意,让她能一次次修复和重生;她拥抱生命的双臂从来没有放下来过。这一点,她深深地感染着我。
电影人老了老了的时候,经常会有沦落街头的结局。我设想很多年后,在某个寒风刺骨的冬季,我会在一个桥洞下写上几页回忆录,然后寄给藤井树,让她看着给钱买走。在信的结尾,我会特别用红色的原子笔写上:你丫如果不给钱,我就把这几页手稿出版在某个闹市区的墙壁上。想象着她接到信的样子,让我总是有一种特别踏实、特别开心、特别温暖的感觉。
这就是和藤井树做朋友十年的感觉。
2012年10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