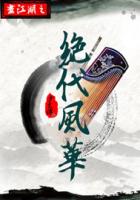洗心斋。
沈言坐在茶楼里,手里端着的茶碗里,仍是南柯一梦。果然人生还是像这茶一样,是一场虚无之梦么。
大约没有人想到,当年那本引出一场腥风血雨的孤兰谱,还留存于世。
江湖人把这本秘籍看作绝世宝物,以为得到孤兰谱练成神功,便可称霸武林,于是趋之若鹜,无数江湖人为此断送性命。沈言后来阅尽百年江湖之史,才知如孤兰谱之灾,每数百年必定重演一回,只因人之贪念,实在可怕之极。
说起来,沈氏收藏天下武功秘籍,明知怀璧其罪,却倚仗有皇家作靠山而有恃无恐,是以一旦失了靠山,立时招来灭门大祸。
当年沈氏本颇得圣宠,却不知为何一夕之间成了天子弃臣,这当中内情隐秘,只怕脱不过皇嗣之争。
沈家出事之时,沈言因自小寄养在云水庵而逃过一劫,待四年之后静安师太拿出沈父临终遗书交予她,除了交代沈氏大宅真正机关所在,只留了一句遗言:我女阿言,爹爹只愿你平安一生,万不要涉入皇族之事。
其时沈言悄悄搬回沈氏废宅,竟就此安然度过六年。江湖纷杂,十载春秋尽可以将一段旧事尘封,而于方岩镇的百姓而言,人生毕竟苦短,十年前的杀戮之气已经淡去,说书先生口中的传说,不过是茶余饭后的娱乐罢了。
手中的茶碗渐渐凉了下去。
沈言放下茶碗,只觉两手发冷,她天生过目不忘,当然不会忘记孤兰谱的开头,写了那样诡异的一段话。
何谓真心人?又何谓伤心人?孔真练成了孤兰谱,他的真心是给了谁人?他又为何成了伤心人?这些她都不懂,但是莫名的,也不想去懂得。
***
太清苑。
太清池的芙蓉,已渐渐露出败意,又一场盛夏将要结束了。
已经是万事俱备,只差动身的时候了呢,倚在太清池边小憩的少女缓缓苏醒,脑中想到的就是这件事。
总算是被我等到了这个时机。少女不无恶意地想道,萧家那帮老头子想拿这种借口阻拦我,未免太天真了。
现下只要能获得父皇的首肯,一切就将沿着那条设定好的路走下去,就算萧氏再怎么圆滑,也无法再明哲保身,自然有人会逼他们做出真正的选择。
想到这里,她莞尔一笑,心中那股恶意的愉悦更深了。
心情突然大好的姚儇伸了伸手臂,方才歪歪斜斜靠着栏杆睡了会,真有些腰酸背痛。她浅眠易醒,午睡时一向不许人打扰,此时太清池周围俱是静谧。
“小白?”她低声唤道。
仿佛凭空而出般,一人在她身侧淡声说道:“非白在此。”
京都的小李公子李丹青在姚儇面前吃钉子,着实也有些冤屈。
姚儇身边的十二暗卫中,有几人姿容出色:英气逼人的穆青、一双桃花眼四处惹风流的石耘……只说一个秦非白,面容清隽如玉,虽常年挂着一张冷面孔,却愈发显得仙人之姿,超然世外。
而朝中的年轻官员中,亦不乏容貌出众者。
看惯了各式美男子的皇朝长公主,自然不会、也不曾把李丹青的“姿色”放在心上了。若单说相貌,恐怕眼前这秦非白比之李丹青,更能入这位公主殿下的青眼。
姚儇默默打量着自己这贴身侍卫,眸光在他玉刻般面容上几多停留,才道:“你可去过幽洲?”
秦非白一愣:“不曾。”
皇朝国土广阔,多为陆地,却有一处岛群,人称十洲,顾名思义乃是由数十岛屿组成,因其方位偏僻,虽是归附了皇朝,却隐隐有些超然的地位。而幽洲城,便是当中最小的一个岛城。
“既如此,三日后便随我去一趟吧。我已吩咐了衣衣准备易容的材料,你这容貌,还是遮一遮的好。”
姚儇看着他,语气有些促狭。
秦非白脸上一阵发红,他生平最忌人谈论自己的容貌,此时由姚儇这样调侃,恼怒交加,却又碍着主仆之别不能发作,一双手紧紧抓住栏杆,几乎要把那块木头捏烂了。
“这可是上好的沉香木,若是弄坏了,再寻上几十载也不一定找得到。”
姚儇淡淡扫了眼秦非白。那双手动了一动,从栏杆上移了开来。
“主子还有吩咐么?”
秦非白此时已恢复镇静。他为人冷静,每每一见姚儇,却极经不起捉弄。世人都知皇朝儇公主尊贵无双,却不知这位公主性情着实有些古怪。
皇朝女子十六及笈,他这主子还有一年才至及笈之龄,可脾性确让人捉摸不透。
皇家子孙历来早熟,锦贵妃的那位晟皇子便是出了名的少年老成,而姚儇既懒散又贪玩,若是个男儿身,只怕便是那纨绔子弟了。
姚儇却在发怔了,不知在想什么。
秦非白见状知趣得告了退,顺路寻妹妹秦衣衣去了。
他们兄妹俩自小孤苦无依,少时即被选入萧氏的暗卫府。秦衣衣擅医术,是以从小即伴在姚儇身边,而他专攻剑术,去年才被调进宫做姚儇的近身侍卫。
兄妹俩多年未见,秦非白虽在旁人面前冷淡,却对自己的妹妹黏得很,姚儇因此又嘲笑过他数次。
秦非白离了太清池,往寝殿走去,却见一个身着黄裳的俏丽少女迎面走来,不由说道:“衣衣,你来得倒巧,我正要去找你呢。”说着面上已经露出了几分笑意。
秦衣衣扑哧一笑,看哥哥面上全是欢喜,娇嗔道:“哥哥,我可不是来寻你的。大皇子来了,在大厅里等着主子呢。”
大皇子姚晟与姚儇同岁,只比姚儇小三个月。
当年萧皇后与当今昭明帝鸾凤和鸣,正当萧皇后怀有身孕之际,锦妃被其父送入宫中,萧皇后是个温婉之人,虽心中恼怒也只是郁而不发,待姚儇出世后不久便含恨而逝。
失去生身母亲的庇护,姚儇被接到太后身边抚养,但太后年岁已高,有心无力,数年后便薨于重病。姚儇孤身一人,无所依凭,只能凭着皇父的爱怜在宫中处处小心谨慎,直长大了些,姚儇正式接管了萧家的暗卫,才算是真正意义上在宫中立了足。
但令昭明帝欣慰的是,姚儇对待姚晟的态度,确凿是毫无恶意,甚而还帮了姚晟不少忙。姚儇与姚晟的手足之情是深刻的,在这一点上,连锦妃也不得不承认。而皇长子姚晟,对皇姐有意或者无意的示好全盘皆收,一直是太清苑的常客。
秦非白知道妹妹对大皇子颇有点倾心,只觉她面上笑容有些刺眼,开口提醒道:“主子将来必然是要继承大统的,你不要与大皇子走得太近。”
“哥哥可不要在主子面前说这样的话。”
秦衣衣正色道:“萧家自然想主子继承大统,但主子一向有自己的主张,萧家既把那暗处的权都交了主子手上,分明是不愿逼迫主子。哥哥怎么糊涂了?我们这些人,早已不是萧家的人,而只是皇朝长公主的人。”
秦非白一直受萧氏教导,不同于秦衣衣陪伴姚儇多年。此时一愣,才想起自己进宫一年有余,却还没有真正把这位公主当成自己的主子。
“哥哥是不是觉得,我们这位主子有些……不可倚靠?”
姚儇平日里的做派,确实不太靠谱,身边的暗卫没有哪一个没被她捉弄甚至调戏过。
秦衣衣见他若有所思,略一斟酌,还是说道:“三年前,大皇子在宫中遇刺一事,面上虽是交由京都侍卫长处理,但那事涉及皇家,多有敏感,真正处理那事的人其实是主子。”
“竟是如此么?”
秦非白大为震惊,面上一阵青白,眼里露出了愧色。
他那时在萧氏受训,也是知晓此事的。整件事处理得干净利落,萧氏得到消息时,已是一月之后,真正是滴水不漏的手段。而姚儇在他面前一直纯良非常,虽说有些怪脾气,俨然是个被惯坏的小女孩模样。
这般说来,是否这位主子对自己,仍然存有几分戒备?
秦非白神情一凛。主子的疑心,于视忠诚为唯一信条的暗卫来说,简直是极大的耻辱。
秦衣衣见哥哥大受打击的模样,正要出言安慰,却是看到秦非白身后,有一人缓缓走来,正是姚儇,忙上前行礼:“主子,大皇子来了,正在前厅等着您呢。”
秦非白几乎是浑身一震,转头一看,正对上姚儇似笑非笑的眼:“小白,你看到本公主怎么吓成这样,莫不是在背后偷说了什么坏话?”
“非白不敢。”
秦非白看向姚儇的目光与往常有些不同,他仿佛如梦初醒,自己这位小主子平素虽没个正经,那份源于骨子里的威仪却不时流露。这样的主子,又怎会无所作为呢?
姚儇又笑了一笑,若有所指地说:“衣衣,你这哥哥可急着找你呢,今日放你大假,你们兄妹两个好好聚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