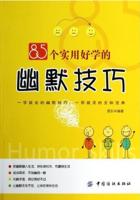当严家人急忙冲上前搀扶严年鹤时,赵继业慌忙低头转身钻出了人群,站在人群外的严丰荣,没有向人群里挤,而是快步溜进了刚才小乞丐们钻进去的那条胡同,向北直追了下去。
小乞丐们在胡同里“嘻嘻哈哈”的向北跑着,没有一个人回头看是否有人追来。严丰荣远远地贴着墙根儿跟在后面,他仔细数了一下,这帮乞丐一共有十三个人,当他们跑到胡同北头时,一帮人站了下来,严丰荣急忙躲到一家住户的门洞里,只听小乞丐们嘁嘁喳喳的争论道:“回去吧,师父一定有赏的!”
“不行,不能就这么回去,不能让他们就这么轻易地走了。”
“对,我还想戏弄一番那个胖头大耳的和尚呢。”
“我还没玩儿够,整天光练功,好不容易出来一次,再玩儿一会儿吧。”
严丰荣从墙角伸出头向北头看着,这时一个个子最高,大约十一二岁的乞丐说话了:“好了,别吵了!师父没让我们干别的,我们不能擅自行动。早晨大家都看到了,风翼大师来家做客,今天肯定不用再练功了,中午还会有好吃的呢,你们几个不是还想请风翼大师教你们飘行术吗?大家听我的,马上回府。”
小乞丐们听他说完,欢呼雀跃地跟着他一直向东跑去。严丰荣疾步来到胡同北头,这里是严家庄的最北边,再往北就是一片丘陵地,没有其他房屋了。他躲闪着跟在了小乞丐们的后面,一直朝东来到庄子的最东头,再仔细看时,严丰荣知道自己已经跟到了赵家院子的北墙外。
接下来的一幕,让严丰荣彻底懵了,自己如同坠入了一场噩梦之中,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只见不远处那群小乞丐站在赵家东院儿墙外,“嘻嘻哈哈”地朝院墙走去,竟然毫无阻挡地走了进去,从严丰荣眼前消失了。
等严丰荣反应过来,大步跑到刚才小乞丐们穿墙而过的地方,把耳朵贴在墙上听着院子里的动静,又小心地伸出双手去触摸眼前的石墙,石墙冰冷坚硬,没有半点儿有人穿过的痕迹。严丰荣又开始仔细查看石墙的每一道缝隙,也没有发现任何机关。他吃惊地看着眼前的石墙,咬了咬牙,向后退了几步,斜着肩膀用力向石墙撞去,冰冷坚硬的石块把他弹了回来,他揉着自己的肩膀,困惑不解,又把自己的手指伸进嘴里狠狠地咬了一下,疼得他龇牙咧嘴。
判断明白自己不是在做梦后,严丰荣绕到了赵家院墙的最低处,轻轻地爬上了墙头。赵家东院儿一片寂静,四周的果树枝桠密密麻麻,有的伸出了墙头,透过这些枝桠,可以看到一垄垄还没有播种的空地,院子的正中央立着一座无碑大坟。严丰荣看到这座大坟,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冷颤,慌忙从墙头跳了下来,接着听到院子里响起一阵狗的狂叫声。
从庄子东头往回走的路上,严丰荣满脑子是刚才那些小乞丐争论的话语,什么师父有赏、整天练功、风翼大师、飘行术……他不相信自己听到、看到的一切。当他走到大街上时,大街上空空荡荡,那些看热闹的人们可能早已经散去了,拉着自己父亲的那辆马车好像也早已经走远了。
他走到自己家大门口,看到大门紧闭,他又看了一眼大门口西侧那棵大槐树,然后快步跨上台阶,抬手扣动门环。门房里的家人答应着:“来了!”轻轻敞开了一条门缝,当看到是严丰荣时,面露惊异之色,严丰荣急忙上下看了自己一遍,又抬头满脸疑问地看着眼前的这个家人。那个家人好像才反应过来,连忙一边打开大门,一边说道:“五少爷,你可回来了,都三天了,可把老夫人急坏了。派人到处找你,也没找到。”
严丰荣听不懂眼前这个家人说的这些话,他抬腿跨进大门,说道:“什么胡话!我不是一直都在家里嘛,刚才我还和你们一起送走的老爷。”
这个家人吃惊地看着他,说:“五少爷,您是说三天前的那个中午吗?”
严丰荣这时才感觉到有些蹊跷了,停住脚步追问道:“什么三天前?你快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家人看他急了,颤颤巍巍地说道:“五少爷,三天前的那个中午,我们大家送走老爷和那两个高僧,回到家里谁也没看到您,直到吃晚饭时,大少爷找您商量什么事,大家这才发现您不见了。开始时,大少爷还以为您跟着三少爷、四少爷去送老爷了呢,可是等到晚上三少爷、四少爷回来时,说您根本就没和他们在一起,大少爷这才急了。老夫人听说后,把家里所有的人都打发出去了,到处寻找您,可整整找了三天,也没有找到您的半点踪迹,您这是去哪了?”
严丰荣被他彻底说糊涂了,自己明明是刚才送走的父亲,又去追赶那帮小乞丐,在赵家大院儿外也没久待,这怎么就过去三天了?他吃惊地盯着眼前这个家人,不知该再说些什么,或再追问些什么。这个家人也不再看他,而是转身冲着大院儿里喊了几声:“五少爷回来了!”
不一会儿,严丰田和几个家人跑到了前院儿,一看果然是严丰荣回来了,严丰田高兴地跑到严丰荣面前,高声说道:“老五,你这三天去哪了?可把我们急坏了,快!快去母亲屋里说一声。”
严丰荣这时才听到母亲屋里的木鱼声一直在“梆梆”的响着,他不解的看着严丰田,问了一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严丰田被他问得一愣,反问了一句:“什么怎么回事?”
“大哥,我可是离开家还不到一个时辰,怎么就变成三天了?你们这是闹什么?”严丰荣有些生气地说道。
严丰田听他这么一说,脸上掠过了一丝不安,他伸手在严丰荣额头上摸了一下,问道:“老五,你没事吧?是不是受了什么惊吓?你二哥走了这么多天没回来,你又不打招呼出去了三天,我们能不急吗?家里出了这么多事,母亲又这么大的年纪,受不了这么折腾了。”
严丰荣张了张嘴,又闭了上来,他不想再解释了,自己也感觉到好像解释不清了。他跟在严丰田身后来到钱老夫人的屋里,老夫人微闭双目,盘腿坐在炕上敲着木鱼,听到两个人的脚步声,眼泪流了下来,头不抬,眼不睁,只说了一句话:“回来就好。”然后继续敲着木鱼。严丰荣这时才将信将疑:自己可能真的离开家已经三天了。
严丰荣从老夫人那里回到自己屋里,他年轻的夫人冯云竹抱着他一岁半的儿子严峰,见他平安无事的回来了,高兴地说着家里这几天如何寻找他,严峰“咿咿呀呀”手舞足蹈着。严丰荣想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但可以肯定自己确实离开家三天了。
严丰登的妻子孙彩兰听说严丰荣从外面回来了,领着自己五岁的小儿子严岭急忙赶了过来,询问严丰荣是否在外面见过严丰登?知不知道严丰登到底去哪了?什么时候回来?严丰荣被问得张口结舌,不知该如何作答。
正当严丰荣和孙彩兰、冯云竹说着话时,五岁的严岭领着一岁半的严峰,戏闹着跑进了严丰荣住的四间屋子的最西面一间。刚跑进去,两个孩子又尖叫着跑了出来,满脸恐惧地站到三个大人面前,大哭起来。严丰荣见此情形,二话没说,快步跨进那间屋子。
这间屋子靠近南窗是一铺土炕,因为没有人住,土炕上胡乱堆放了一些平时不用的东西,土炕下靠西墙安放着一张方桌,方桌左右摆了两把椅子,北侧靠墙处摆了一只五斗柜。
严丰荣仔细看了一遍,没有什么异样,这些东西是一直就摆放在那里的,平时也很少有人去动它,可两个孩子这是被什么吓的?他又竖起耳朵听着屋子里有何响动,仔细寻找着每一个角落,看是否有老鼠之类出没,可还是没有任何发现。
冯云竹和孙彩兰也来到房间门外,伸头向里面看着,两个孩子大哭着远远地躲在后面,不敢再向前半步。
严丰荣站在屋里一动不动,却瞪大眼睛,竖起耳朵,寻找着屋里任何可怕的东西。可结果还是让他失望了,这间屋里连一只苍蝇,或者飞蛾都没有。
严丰荣从这间屋子里出来,看着眼前两个还在大哭的孩子,微笑着蹲下了身子,问严岭:“小岭,告诉五叔,你刚才看到什么了?是老鼠吗?”
严岭哽咽着抬手指着那间屋子说:“白……白胡子老头儿!”
听严岭这么一说,严丰荣脸上的微笑凝固了,他感觉到自己身上的寒毛都立了起来。他盯着眼前的严岭,厉声说道:“别胡说,哪来的白胡子老头儿?我怎么什么也没看到?”
严岭继续哽咽着,一手抹着眼泪,一手指着那间屋子说:“椅子上,椅子上蹲着一个白胡子老头儿。”
严丰荣站起身来,扭头看了看西面这间屋子,伸出右手拉住严岭,小声说道:“小岭,别怕!来,你指给我看,白胡子老头儿在哪儿?”
严岭惊恐地挣脱他的右手,拔腿跑到了屋外,严峰也哭着急忙蹒跚着跟到了屋外。两个女人被孩子的话吓呆了,瞪大了眼睛看着那间屋子,并不断向后退着。
严丰荣壮着胆子再次跨进那间屋子,盯着方桌左右那两把椅子,慢慢靠了过去,两把椅子上还是什么都没有。严丰荣伸出颤抖的右手,先在北面那把椅子上摸了一下,椅子是空的。他接着慢慢挪向南侧那把椅子,离这把椅子还有半步时,他紧咬牙关,把左手也抬了起来,两只手颤抖着摸向这把椅子。摸到一半时,手放在椅子上停了下来,他脑子里有一个声音在不断告诉他:别怕!什么也没有!
然后,严丰荣瞪大双眼迅速把整个椅子摸了一遍,确实什么也没有,他这才赶紧换了一口气,退后一步仔细盯着这两把椅子,椅子上还是什么也没有出现,他清了清嗓子,壮着胆子问道:“何方神圣?光临寒舍,有何指教?为什么不敢现出原形?”
他刚问完,北侧靠墙五斗柜处发出了一个颤巍巍的声音:“哈哈哈哈,犬子离家时也是你这个年纪,四十三载了!哈哈哈……”
“谁?你到底是谁?”严丰荣转向那个五斗柜,可还是什么也没看到,他大声喝问道,“你想干什么?我们一家老小可从来没做过什么亏心事……”
不等他说完,那个“哈哈”的笑声已经在屋子外了,严丰荣转身跑出屋门,惊恐地寻找着那个笑声。站在屋外的严岭吓得把哭声憋了回去,抬手指着前面四间房子的屋顶。严丰荣顺着严岭指的方向看去,还是什么也没看到,两个女人跟了出来,冯云竹不解地看着严丰荣,问道:“你自言自语,装神弄鬼地吓唬我们娘儿几个干什么?”
严丰荣把目光收回来停在两个女人的脸上,问了一句:“你们没听到那个声音?”
孙彩兰和冯云竹疑惑地看着他,然后又摇了摇头。孙彩兰低头看看两个孩子,又抬起头来对严丰荣说:“他五叔,你被两个孩子吓着了吧?我们什么也没看到,什么也没听到啊。”
严丰荣什么话也没说,冲进屋里找出一把铁锁,把那间屋子锁了上来。再回身时,看到二嫂孙彩兰拽着严岭急步走远了。
傍晚时分,严丰贵鬼鬼祟祟的来到严丰荣住的屋里,见冯云竹抱着孩子一直不离左右,就有一句没一句的闲扯着,当看到西面那间屋子锁着时,问了一句:“五弟,你这屋里还藏着什么宝贝吧?”
严丰荣看出他肯定是有事找自己,没接他的话,而是对冯云竹说道:“你带着小峰到母亲那里去看看,我和四哥商量点儿事。”冯云竹很不情愿的抱着严峰离开了。
见冯云竹出去了,严丰贵又把屋子里扫视了一遍,再向屋外看了一眼才回过头来,压低声音对严丰荣说:“五弟,你出去这三天看到了吧,外面兵荒马乱,朝廷又要打仗了。前天在送父亲的路上,那个老和尚若愚还说这场战争不可避免,肯定又要有大批生灵惨遭涂炭。我们家在外的生意也应该早作打算了,如今父亲已经出家皈依佛门,这些生意只由大哥一人掌管,是不是有些不妥?
“五弟,在这个大家庭里,你我的关系最好,你最能理解我的处境,父亲这一出家,我和母亲能否继续在大院儿里住都是个问题,我不得不多为自己考虑。”
说到这里,严丰贵停了下来看着严丰荣,严丰荣低着头,若有所思,见严丰贵不再说了,他抬起头看了看严丰贵,说道:“四哥,你的话我懂。不过,父亲离家只是为了暂时避一下祸端,生意上的事你我都也不懂,家里也没人会赶你出去,一家人住在一起好好的,你想这些干什么?”
“唉!五弟,家里连续发生了这么多的事,老夫人又整天只是吃斋念佛,家里也没人主事,我能不多想吗?”严丰贵摇了摇头说道。
“四哥,正是因为家里出了这么多事,我们兄弟才更应该齐心协力,共度难关。”严丰荣接着说,“现在有好多事还没搞清楚,但我相信我们严家会渡过眼前这一劫的。大哥和宏达掌管家里在外的生意,养活这一大家子老小也不容易,我们就不要再添乱了。”
严丰贵还是摇着头,叹着气,又说道:“五弟,这个家里,只有你能帮我,真有那么一天,那可千万要帮我一把啊。”
两个人正说着,严丰田敲门走了进来,严丰贵显出一些不安和尴尬。严丰田看到严丰贵也在,就说道:“老四,正好你也在,我们有几个事一起商量一下。”
严丰贵却反问了一句:“我在这里不碍你们的事吧?”
严丰田瞪了他一眼,说道:“什么话?家里这么多事,谁也不许撒手不管!——老五,你不说自己去哪了,我也不追问了。你二哥到现在也没回来,我们得立个规矩,从今以后,不管是谁,要离开家,离开严家庄,必须和我打个招呼。再就是你三哥以为前天那声惊雷,就是因为你问若愚法师那句话引起的,我只记得你问东海、南山什么来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严丰荣苦笑了一下,说:“大哥,我说不明白。你还记得我说看到有人从树洞里出来吗?这是千真万确的。还有你们说我离开家三天了,可我就是跟着那帮小乞丐,去了庄子东头赵家大院儿墙外转了一圈儿,回来你们就云里雾里地说我离家三天了。我是有嘴难辩,说不清楚了。”
“那东海和南山又是怎么回事?”严丰田继续追问道。
“大哥,这件事更蹊跷。”严丰荣回答道,“我更说不明白,也不会有人相信我。我以后搞清楚了,一定向你解释明白。”
严丰田不再追问了,他看着严丰贵和严丰荣说:“朝廷又要打仗了,我们家最近又不太安宁,严家在外的生意只靠峻儿这个孩子一人支撑,我有点儿不放心。我前几天给他写了一封信,至今也没有回音,我想带几个人过去看看,又不放心家里。所以,我想听听你们哥儿几个有没有好主意。”
一听严丰田这么说,严丰贵连忙说道:“大哥,这个时候,你可不能离开家啊。外面的生意,你随便安排一个人去就可以了,最好赶紧把生意往回收一下,兵荒马乱的不要再有别的闪失。如果你信得过我,我可以跑一趟,帮着宏达贤侄把生意收回来。”
严丰田看着他没有说话,严丰贵看出来了,严丰田是想让严丰荣跑一趟,而严丰荣却在故意装糊涂,说道:“我看四哥可以,他经常外出,知道如何办事,打起仗来,生意也没法儿做了,就让四哥和宏达把生意先拉回来,等天下太平了再做打算吧。”
严丰贵看着严丰田,等他发话,可严丰田却只是笑了笑,接着把话题岔开了。
这时,一个家人慌慌张张跑了进来,对严丰田说:“大少爷,门外来了三个乞丐,其中一个好像身上还带着伤,正在敲咱家的大门呢。”
一听“乞丐”二字,严丰荣不寒而栗,一下子站了起来,心头涌出了一种不祥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