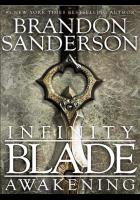那次遇袭过程是这样的:主攻部队B军因连续作战,啃了不少硬骨头,损失较大,需要休整。我师和其它部队及担负后勤的一批民兵便要到附近接管B军的阵地。
当天,我师由三百多辆汽车搭载着人员装备向B军阵地开进。这时前线阵地已被攻克,沿途交通线也有我们的部队警戒。但在前往B军阵地时,我们排和180个民兵,因车辆不足,被留在半途,等待车辆运输。
当晚,民兵们生火做饭,吃了晚饭,然后便休息了。
第二天,来了四辆汽车。我们排和那180名民兵都分别登上汽车,向B军阵地开去。排长带着战士民兵和两挺机枪坐第一辆,我坐在最后一辆。排长乘坐的那辆和第二辆先开出去,后面的这两辆车没走几步竟"没油"了,于是停在了路边等待支援。
坐在我这辆车上的一个民兵营长和我们政治部副主任及一个卫生员,看见车抛锚了,就下车跑步追赶前面的车。但他们不知道,赶上的将是一场大祸……
当天下午4点左右,一个受伤的民兵跌跌撞撞跑回来报告,说开出的车辆在路上遭到敌人伏击,他那辆车上的人员几乎全部牺牲,包括一名政治部副主任和五名放电影的战士及50名民兵,最后只剩下两个民兵,其中一个就是这个跑回来报告的民兵,另一个受了伤还在原地躲藏。
我问他为何没被打死,他说车辆被击中时,他倒在车上装死,敌军最后还是上来踢了他两脚,他仍不动弹。车下的人都被匆忙胡乱复枪,而车上的人本来被炸得很烂,也就没再复枪,他因此得以幸存;另一位民兵则是受伤跳下车后向敌人扔了一颗手榴弹,利用敌人的慌乱和手榴弹爆炸后的硝烟,躲在草丛里才没被发现,现在还在原地等待救援……
我们忙问:"排长呢?"他说:"他冲过去了,但车厢也被炸了,驾驶员没死!"
事实上,据我们事后了解到的情况是这样的:排长在第一辆车上,后面跟了一辆。在路上遇到敌人伏击的时候,车箱上先中了一炮,车上的战士和民兵伤亡惨重,但他们车上的那两挺机枪进行了猛烈还击,向两边拼命扫射,火力很猛,可惜的是,因为看不见敌人在哪里,只是看哪里枪响有烟或火光就向哪里打。排长那辆车加足马力强行先冲了过去,而后面的第二辆车却被打坏在路上。敌人又朝汽车打火箭弹,汽车燃起了大火,没牺牲的战士和民兵跳下车还击,结果又被敌人的弹雨扫倒。
排长的车冲出包围圈5公里多才停下来找人报信,他为此差点受了处分,上级认为他没有必要冲那么远,而应该立即组织力量援救受袭车辆。其实在那样的山地丛林间的一条小公路上遭遇突然又猛烈的袭击,处置起来慌乱一些是可以理解的。
听到这个惨剧,我们都极为震惊:一路上,主要交通沿线都在我重兵把守之下,周围也经过了多次清剿,敌人竟能在路上伏击,而且我们的牺牲如此之大!
事后,留守的部队和我们立即向出事地点奔去。天还没黑,就到了遇袭现场,很惨,牺牲的战士和民兵都被敌人补了枪,或者是被打了很多枪。当时天下着小雨,像是为这些战士和民兵致哀!血水和着雨水流了一地,红红的一大片……
天渐渐暗下来了,我们把烈士们一个个搬到车上,大家的心情异常沉重。
乘着天尚未完全黑,我观察了一下周围的地形,路段并不险峻,按说敌军选择这样的地形打伏击并不是明智之举,离这个地段最多两三公里地就有我们的部队警戒。但就是在这个大家认为比较安全的地段,我们遭受了重大损失。
这次战斗,战友伤亡惨重,但却有两位大难不死的战友成为"钢铁战士"并创造了战争史上的两个奇迹:一位战友头部中弹,子弹从太阳穴部位穿进,然后又从另一边太阳穴穿出,他竟然没有牺牲。弹头在脑子里也没有发生翻滚现象。据卫生员讲,送到医院后纱布竟然能从这头伤口穿进,然后从那一头伤口抽出,说得可能有些夸张,但他头部被子弹穿透没死是千真万确的。另一位战友,也是在第一辆车上被炮弹炸伤的,胸腹部开放性爆裂伤,肠子全都流了出来,但也被救了回来,只是肚皮少了许多皮肉,一直在医院治疗,最后被送到后方某军区的一家医院治疗。回国后,连领导去看望他,说他肚皮上还包着层层叠叠的纱布,直到我那年冬天复员回乡,他都没有回到连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