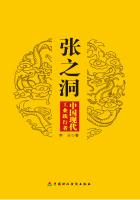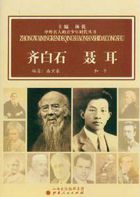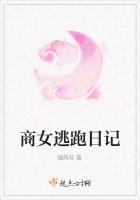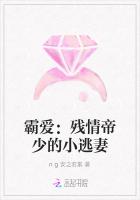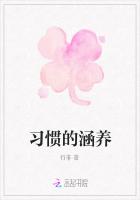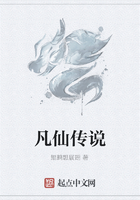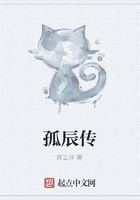我知道,他是病着的,但他说起话来,却比健康的人还起劲,还爽利。他脱下那只大而灰扑的铜盆帽,额上已经冒着细微的汗气了。
“我们息一息吧。”他说。
于是我们就到息一息的地方去,坐下来。我们一共五个人:他和林夫、陈烟桥、白危还有我,围住了一张小茶几。
陈烟桥和白危有一件事情要请求他。是为的什么事情呢,我当时没有听清楚,只仿佛是为了有一个人要他做一篇“序”的样子。但他却摇着头说:
“他吗?他在段祺瑞手里就压迫我的。——我不会做!我不会做!叫他去请别人去,他郑重地说着。
我格外的和他熟识了。我要贪婪地和他交谈:
“那次苏联版画展览会,许先生是和你一起来的,这次许先生没有和你一絲?”
“没有。”
“近来好些吧?还打针?”
“好些了,针已经不打。不过热度有时还要高起来。”
“那末就再打打。”
“也正这样想。”
“前天,你和许先生,鹿地先生,池田先生,一起去看《冰天雪地》的吗?”
“去的。那片子真好!他们到底是和别人不同的!”
“我也去看过了。全戏院就只有三个人。那时,外边还在搬家哩。哈哈!”“嘻。”
“你为什么不搬呢?”我忽然觉得这已经问过他了,就立刻改口道:“你还是到外国去静养吧?”
“我的父亲没有留下遗产给我啊。病也没有法子想。不写文章就不得过。嘻哈。”
“但你毛病没全好,得息息呢?”
“息得太多,也就很无聊。”
“真的,登在《作家》上的那篇《答徐懋庸》……”
“嗯,是啊!不要说他了。他是明明晓得我有病,不能写什么,想来一气气死我的。哈哈,但我那里……我就斜躺着,用一只手搭在茶几上,写了四晚,写成功了。我是不赦他的。我不给他气死……哈哈。”
“但你的《死》也写得太悲哀了!”
“没有什么法子想的,我就只能这样写。”
他太兴奋了,摸出烟来抽。
“那本你告诉我的代替《引玉集》的《拈花集》,什么时候出版呢?”
“啊,恐怕一时还不能吧。钱都差不多印光了:印柯勒惠支的选集,印《海上述林》。柯勒惠支的选集觉得印得怎么样?”
“好极!”
“这都是我亲自衬纸,亲自校阅——多的抽出,少的补上去的。”
“自己有病还……”
“嗯。别人做的不如意呢。而且我拿一本寄给了作者。”
“柯勒惠支能收得到么!”
“不是直接寄给她的,我叫人转去。”
“谁?”
“武者小路实笃的哥哥。他是日本驻德的公使。不知会不会收到?”
“叫官转去,我想总不会有什么毛病的!”我笑着说。
“我也这样想。嘻嘻!”
他又燃着一支纸烟了。我也吸起来。他忽而对我问道:
“你就在新亚教书?”
“是的。”
“那学校——我的侄女儿在那边上过学,要打手心。现在还打吗?”
“还打的。”
“嘻……”但他连忙地摇着头。
“嗯……”我感到很深的内疚,低下了头去。但终于也就又问他:
“你的儿子在哪个学校呢?”
“就在自己的弄堂里。”
“还好吗?,’
“好不来!前几天房东来收租,缴不起,连课都##几乎不能上,哈嘻!”“嘻嘻。”
“我们再来看一看吧。”他立起来说,脸上似乎发亮了。我的身肢也跟着轻起来,只觉得浑身浸在亲切的空气里。我太高兴了。
我们又跟着他看许多的木刻,听着他的对于木刻的细致的批评。他指着画面说,这人的脚骨断了,手太长了,不说这是解剖学的错误;他说这不像中国人,饥民,不说这是轮廓和明暗的错误;他看见刻的是群像,就说,面孔都是一样的;他看见战争,就说,战石不大对,去看看克拉夫兼到”(Kravchenko)的吧。
他是这么具体而微细地批评着的。
看完了,于是乎再坐下来谈。
“觉得怎样?这次的展……”
“自然进步得不少了。但人物总还不会刻。”
“大家的素描工夫都很差。”
“这所以也怪不得的。譬如像柯勒惠支……”
“柯勒惠支的那种基本工夫,实在太深了。尤其对于光线的凝散,布置得非常的有力。”
“是啊!柔石等死了,我写信去请她画一幅被害的图画,作为我们的纪念。但她来信说不能,因为她没有看过真实的情形,而且对于中国的文物,又生疏,没有答应。那种作画的认真的精神,我们应该学学她。”
“真是,她把同样的一幅画,要画上两三遍,我在她的《新集》里面见过的。”
“所以环境不允许作细微的素描时,就要多速写。参考书也要多看。”他严正地说。
“但真真可作参考书的,却很少。”
“这就是我常常赔钱贴工夫,印画册的缘故啊!”
“画册要印得好,方才对于学习的人有用。但成本就要贵。有钱的不要买,没有钱的又买不起——就只好送。哈哈。”
“赔钱赔工夫~你真是一个傻子啊!哈哈!”
“由他去吧。哈嘻。”
我完全把他当作一个“促膝谈心”的朋友看待了。他不是一个平常的人,然而他是一个平常的人;他不像导师,然而他是一个青年们的最好的导师,是领着我们走路的热诚的真真的先导者。
他说要走了。把帽子戴上了,又故意的戴得那样的低,低到帽沿几乎要碰到了鼻子,只能使人看见半个瘦削的苍白的脸庞和一横鼻子下的厚厚的胡须,急急地走了。一面回过头来对我说:
“你不要送!你不要送!”
我也就不送了。看着他的帽子,宽大的袍子,和袍子下面的细瘦的脚肢的移动,我看着一个病人不可能有的他的壮健的背影,在走廊的转角处,很快地消失了。
我在回家的途中,被兴奋所激动,觉得我的周围的东西,都像跳着的,活着的一样。
看了展览会后的第三天,我到鹿地先生那边去了,他说鲁迅先生看了展览会回来之后,又发了热。我为此非常的后悔,我做了饶舌的蟋蟀了。我即刻就给了他一封信。
信发了之后,不见有回信来。十六号的晚上,我又去看鹿地先生了。会讲中国话的鹿地先生的夫人池田先生对我说:
“热倒不发了,他昨天还到我们这里来玩的,但回到家里就喘气!”
“哦!”我不免惊异而且又立刻担心了起来,一面负了很大的内疚。
一夜已过,早晨,我做梦也想不到的接到了他的信,同时还送了一本《述林》给我的朋友陆君。这高兴,对我是不小的;我激动地拆了开来,有两张信笺,那第一段是:
我并不觉得你浅薄和无学。这要看地位和年龄。并非青年,或虽青年而以指导者自居,却所知甚少;这才谓之浅薄或无学。若是还在学习途中的青年,是不当受这苛论的。我说句老实话罢:我所遇见的随便谈谈的青年,我很少失望过,但哗啦哗啦大写口号理论的作家,我却觉得他大抵是呆鸟。
他是这样的宥恕着我,我觉得较为宁贴了。但末一段是:病还不肯离开我,所以信写得这样了,只好收束。
这短短的三句,我把它们反复地读着。读到末一句,他的坚决,但又无可奈何的神情,在我的心上活起来。看看字迹,比先前的潦草了些,那显然是无力,疲惫了的结果。我又即刻看见一个用帽子遮住半张脸的热情老人……
在心绪的不宁中,我又给了他一封回信。但这是十七号的晚上才写成的。
十乂号是星期日,我给他的信,直到下午才能寄出去,因为上半天是无法递寄的。当天的晚上,我又去看鹿地先生了。鹿地先生说道:
“彼7咳夕于、y夕!”
池田先生就即刻翻译给我听:
“他喘气喘得很厉害哩!”
“哦哦!”我更加惊异而且担心,一面负了更大的内疚。然而我自己问着自己说:“可比他五月里的病势危险呢?”
但我也终于别了他们,孤单地踏着无灯的北四川路,悄悄地回家了。而扑面吹过来的是深秋的夜风,很凉,望望天,乌蓝的天上密集着微明的繁星,我清楚地看见一个用帽子遮住半张脸的热情老人……
但只隔了这么短短的一夜——在19日的清早,这老人,就负了现实所给予他的辛苦和恣睢,寂寞和悲哀,停止了他的呼吸,和我们永别了。啊……当我和池田先生,在麻木中奔出校门,麻木地钻进了汽车;在麻木中冲进他的卧室,麻木地立在他的床前的时候,他巳逝世四个钟头了。他已不再能和我“促膝谈心”,也不再能督促,鼓励,指示我们,一同来踏过这丛莽的荆棘道路,而只是和平的,安静地躺在床上了。极度的悲哀蒙住了我,我竟哭不出声音来,眼泪只是向心底流下去,流下去……倒反凝成了愤恨了。
哪里会知道,我们那次在展览会里的相见,竟成了最后的会聚?在十七号收到的那封信里的“只好收束”,竟是他对我的永诀呢?
诺诺,许先生拿在手里的不是我昨天给他的复信么?到现在才接到。为什么不早些送来呢?啊,他没有看到啊……
我毕竟掉下泪来了。
鲁迅先生一死,别人才晓得,我和鲁迅先生的友谊,这就糟啦!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有一种新订的法律,是说:“对于一个自己敬佩的人,万不能和他发生友谊的关系。”而我却对于一个我自己敬佩的鲁迅先生,发生了友谊的关系了。
我又无端地碰在这法律的碑上了,咳!
于是,我不单失去了职业,还得远远的出走。牢狱究竟是屠杀奴隶的刀砧,我自己爬上去干吗?
写到这里,浓重的黑夜把我压住了,真使我难予呼吸。而悲愤的激流又在心中这样的奔腾,我也不再能够写下去了。是的,我把自己所有的说话,还是写在我纪念鲁迅先生的永恒里吧……
我就这样地活下去……
1936年11月1日,深夜。
(1937年,《鲁迅先生纪念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