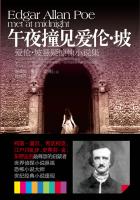刘正一拍桌子,大怒道:“高伟强同志,我看你真是昏了头!什么‘忠孝两全’?你是谁的孝子?谁要你当孝子?自己好好检讨,不要再干这些无聊的事儿,这样才影响内部团结!请你马上出去,出去!”
高伟强走到门口,含着热泪哽咽道:“老刘,我知道您现在心情也不好,您骂俺什么都没关系,我不会计较,今后有事,您……您尽管招呼俺就是了……”
望着高伟强消失的背影,刘正重重地将茶杯砸在桌子上,铿锵的声音在办公室上空回荡了很久。
这天夜里,秦大奎在屋内独自喝酒,唱着志愿军军歌。刘正和我经得谢恒远的同意,走进屋内,静静地看着这位老兵。
秦大奎呆呆地愣着,神情肃穆,气氛悲凉,他没有搭理我们,缓缓地将杯中的酒洒在地上,我感到秦大奎仿佛回到了硝烟纷飞的朝鲜战场上,站在无数牺牲的战友面前,默默地倾述自己的哀思。
半晌,秦大奎迟缓地从怀中掏出一张崭新的照片,准备划动火柴烧掉它。刘正急忙冲了过去,从秦大奎手中一把夺过了照片。
“哎!瑾妹子……”
秦大奎一声长叹,脚一软,头一晕,向前踉跄一步。我上前扶住他,秦大奎甩开我的手,端起酒瓶咕嘟嘟地喝了一大口,他咬紧牙关,猛提一股劲,又朝前走了步。我感到他的脚步轻飘飘地踩不到实处,手到脚不到,脚到腰不到,完全是歪歪倒倒,偏偏扭扭地走,还没等他站稳,就一下子瘫坐在地上了。
“局长!局长!”我连忙将秦大奎扶起来,他虚汗层层涌出,脸色苍白,嘴唇颤抖。秦大奎对我说:“大学生,你不消管我,我自己能走,我能!”我望着秦大奎的模样,心中发酸,禁不住涌出一串热泪。
秦大奎走到刘正身边,凄然地呷了口酒,拿起那张照片细细地端详着。
这是杨瑾生前的照片,照片上的杨瑾身穿一套美丽的学生装,胸前别着闪亮的校徽,手中握着一本厚厚的书。
“这是瑾妹子送我的。”秦大奎说,“莫看她那时是个学生娃儿,可已经有两年党龄了。她和老刘一样,从事地下工作,就在照完这张相片几天后,瑾妹子就被敌人抓走了。监牢里,受尽了各种酷刑,甚至被……了不起啊!
竹签把手指甲敲开了,也没撬开瑾妹子的嘴,她一个字儿都没说。老刘,你说她像个啥?那次对我说了个苏联电影中女娃子的名字。”
“丹娘!”刘正默默地吐出两个字。
“对!丹娘!”秦大奎捶了下桌子,“她就是中国的丹娘,是我秦大奎的丹娘!老刘,我知道她那次拒绝我的原因,她怕配不上我,老是觉得被敌人……哎!日你先人哦!我秦大奎是这种人吗?是吗?……老刘……你说,说!我是这种混账王八蛋吗?呜呜……”说罢,秦大奎哽咽出声,他捏着照片呜呜咽咽伤心不已。
“局长,您要想开点,发生这种事儿谁也想不到啊,人死不能复生。”我劝慰道。
“老秦,你为什么要到车子里去?去干什么?”刘正冰冷地问道。
“你!莫非你也怀疑我?”
“侦查员的纪律你应该知道!证据!事实!只有这些才能说明一切。”
“我去车里是……”秦大奎想了想,鼓足勇气说,“送求婚信给瑾妹子,想给她一个惊喜罢了。吃饭的时候,我和高伟强喝了点酒,他问我为什么还没和瑾妹子结婚,我就给他讲了缘由。老高说,瑾妹子是大学生,喜欢浪漫,不如写封情书说说自己的心里话,让她放宽心。他还告诉我,晚上瑾妹子要用车,可以把信事先藏在车里,给她一个惊喜,说不定事儿就成了。没想到,她会!哎!我他娘的真傻,当时为什么不发动车子呢?把我炸死多好啊!”
啪的一声,秦大奎狠狠地抽了自己一个耳光。他伏在桌上,单手捂脸,花白的头颅一颤抖,肩头一耸一耸,空荡的袖管随风飘荡,潸潸眼泪,顺着指缝流出,叭叭有声。
我茫然地站在一旁,这时,窗外的雨缓缓地落着,静静地滴着。仿佛公安局出现了一些污浊不堪的东西,只有雨水赶来把这些污垢都冲刷掉。
忽然,秦大奎不顾一切地冲出了房间,一溜烟儿下了楼,跑到了大院。
雨中的秦大奎喝尽瓶中的烈酒,砰的一声,将酒瓶砸得粉碎,他向着夜空叫骂开来:“狗特务!你们给老子听着!有本事空投一个团,一个师,一个军下来!老子不怕你们!说话啊!怎么不敢吱声啦?混账东西!有胆子就跳下来,老子和你们单干!来……来……拼刺刀……拼刺刀!老子跟你们拼了……”
秦大奎拎起墙根的一把铁铲,摆出一副刺刀拼杀的架势,四周飘洒的雨珠变为一个个美国兵。“杀啊!杀……”秦大奎左突右刺,在雨中杀得昏天黑地,口中不停地喊着,“扑倒游尔威棚荡!扑倒游尔威棚荡……”
整个公安局的人都知道秦大奎为什么这样做,没有人出来劝阻他,大家默默地站在雨中,热泪盈眶地陪着秦大奎。
不一会儿,秦大奎便撑着身子坐在泥地上,他望着不远处汽车的残骸,显得无比的痛苦和凄凉。我从他的脸上看到一种彻骨痛心的冷,一种万念俱灰的孤独和寂寞。我想,一个男人对烽火硝烟的英雄岁月的回忆,伴随他对一个女人刻骨铭心的爱,此时此刻,已在秦大奎心中冻结,成为他永远的怀念和一道抹不去的伤疤。
缓缓地,秦大奎吐了一口粗气,颓废地躺在泥水中。我和几个同事跑到他身边,将一件棉大衣裹在秦大奎身上,我把这位昏厥的老兵背进房里,他仰躺在床上,紧闭双眼,两行清泪,悠悠晃晃地顺着脸上的伤疤,颤抖着,久久没有滴落下来。泪珠里,饱含着他想要对杨瑾说的话,勾画着他们美好的明天。
夜更深了,雨更大了,刘正一个人坐在窗前,一直注视着那辆被炸毁的汽车。
我到康城县公安局已近一个月,在我脑中积累的印象和思考的问题,比我在省城待了三年的还多。基层公安工作是紧张和危险的,侦查员们游离在生与死的边缘,他们不但要与各种刑事罪犯做斗争,还要与夜空降落的特务和潜伏在内部的“内鬼”斗智斗勇。熬夜,对于每一个侦查员来说是家常便饭。
当会议室自鸣钟敲响时,我看了看手表:凌晨两点,专案组的办公室里依旧灯火通明,案情汇报会开始了。
刘正问韩福祥:“福祥,你了解到什么情况?”
韩福祥说:“事发后,我在四周的居民区调查,找到了一位目击证人。他说当天自己正好下班回家,刚走到距离朱武出事的电线杆不到十米的地方,一辆‘嘎斯’牌军用卡车疾驰而过,溅了他一身泥水。这位同志正要发火,突然,军车在前方停下来了。他以为开车的解放军会下车道歉,没想到车里的人非但没有下车,反倒对着电线杆用大灯一阵猛射,还疯狂地按着喇叭。就在这时,意想不到的场面出现了。”
“什么场面?”凌舒雅显得很紧张,她捧着水杯轻声问。
“电线杆上的朱武在灯光的照射下,发出了惊恐的尖叫,跟着身体不停地抽搐,一不小心,他的手搭在了高压线上,朱武被强大的电流吸了过去,接着变压器发生了爆炸,整个康城的线路就这样瘫痪了。我想,朱武是一个熟练的电工,他的死或许就是一次意外事故罢了。”
“东海,你呢?”刘正问。
“供电所的职工告诉我,上个月初,朱武的手腕不慎被一条狗咬伤了,当时他没有在意。过了十几天,朱武就觉得全身不舒服,还频繁发烧,请了好几天病假。我到县医院问过,朱武到医院看过门诊,医生诊断是感染了狂犬病毒,建议他立即住院治疗,但朱武拒绝了,他说医生瞎乱诊治。我还问过王秋月,她也证实朱武确实被狗咬过,出现过发烧、伤口疼痛、烦躁这些症状。王秋月劝他去医院治疗,却招来朱武的一顿毒打,她就不敢提这事儿了。”
“狗呢?咬伤朱武的是家犬还是野狗?”
“是茂记照相馆养的看门犬‘旺财’,咬伤朱武后就被王茂林叫人打死埋了。”
“王茂林家的?难道……”我和凌舒雅听了后,大吃一惊,难道朱武和王晓兰真的有私情不成?
“被狗咬很正常嘛,但也不至于致命吧。”胡铁柱说。
“疯狗就不同。”刘正缓缓地说,“狂犬病俗称疯狗病或是恐水症,是一种侵害中枢神经系统的急性病毒性传染病,所有温血动物包括人类都可能被感染。它由染病的动物咬人所致。从朱武的症状看,他的确患有狂犬病,而从他的发病时间看,案发当日,正好是狂犬病的兴奋期。”
“兴奋期?”李东海不解地问。
肖克说:“狂犬病患者的病症表现一般分为潜伏期、前驱期、兴奋期和昏迷期。很明显,朱武的潜伏期很短,只有短短的几天,他伤口疼痛和发烧等症状,说明那时朱武正处于前驱期。由于他放弃了治疗,致命的兴奋期就随之而来。”
“致命的兴奋期?”我面带疑惑地问。
肖克解释道:“狂犬病患者进入兴奋期后,会出现精神紧张、全身痉挛、幻觉、谵妄、怕光、怕声、怕水、怕风等症状。因此狂犬病又被称为恐水症,患者常常因为咽喉部的痉挛而窒息身亡。”
“莫非这与朱武的死有关系?”胡铁柱问。
“从常人看来,朱武的死是一次意外事故,不是被人所杀。但是,这里面疑点很多。”刘正说。
“疑点?”凌舒雅不解地说,“不就是王秋月说的,朱武和王晓兰有私情,还有案发当天供电所根本没有人叫朱武去修变压器,莫非朱武有狂犬病也是疑点?当天下雨也是疑点?”
刘正笑了笑:“这些线索单独看,都很平常,但是把它们连接起来,就不一样了。朱武是潜伏的特务,这点毋庸置疑了吧。我们来大胆假设一下,他与陈子白的死有关联,可能导致他身份的暴露,因此有人想杀死朱武,让他永远沉默。首先,凶手让疯狗咬伤朱武,使朱武染上狂犬病毒。接着,他制造了一个意外事故,那就是案发当天晚上,天空下着大雨,有人制造了变压器受损的假象,叫朱武去修理。当朱武在雨中修理变压器时,一辆军车恰好路过,朱武被汽车大灯照射,导致他突然病发,最后被高压电触死。”
“啊!不会吧!这也太巧了吧!”我说。
“对啊!这正是凶手要达到的目的,让所有人都觉得朱武的死不是他杀,而是意外,这样,朱武的特务身份自然被掩盖了,没人去调查他,线索的链条就此掐断了。这个幕后主使是个高手,他掌握一定的医学知识,并知道朱武有狂犬病,从而制造了一场人为的意外事故,将朱武置于死地。”
“福祥,那辆照射朱武的军车找到了吗?”刘正问。
“是咱们局后勤科的车,那天出车的是高伟强。我问过他,他说自己的确在场,开车灯是看见电线杆上有个什么东西,没想到会出这么大的事儿。
事发当天,是高伟强第一时间通知供电所,也是他一直在现场维持秩序。”
刘正又问:“东海,王晓兰这几天有什么异常的情况没有?”
“没有,只不过她好像在谈恋爱,还是和我们自己的同志。”
“谁?”
“高伟强。”
“继续监控王晓兰。”刘正说。
“那高伟强呢?”我问。
“没有确凿证据之前,不要随意怀疑自己的同志。还是那句老话,让证据说话!”刘正说完后,叼着烟斗,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
这时,张福生端着几碗热腾腾的馄饨躬身走了进来。
“五哥,您还没睡?”刘正笑着问。
“年纪大了,睡不着!何况瑾妹子刚走,看着局长这样,我这心……”说着,张福生用袖套抹了抹眼泪,他指着馄饨对我们说,“快!……趁热吃!趁热吃……年纪轻轻就熬夜,身体怎么架得住?政委临走时叮嘱我,要保证你们的后勤供应。”
刘正招呼我们吃馄饨,将两包骆驼牌香烟塞给张福生,笑着说:“五哥,意外收获!”
“呵!正宗美国货。”张福生闻了闻,轻声说,“我在食堂里暖了酒,做了几个凉菜,来一口?”
刘正笑着点了点头:“再杀一盘!”
“行!舍命陪君子!”
说完,两人笑吟吟地走出了办公室。
“喏!奖励你的,大才子!”凌舒雅将碗中的馄饨舀了几个给肖克,有意无意地向我望了望。不知什么缘故,我感到口中无味,心里很乱。
凌舒雅一边吃着宵夜,一边讲述我们那天的战斗经历,大家听到我没拧盖子就扔手榴弹的糗事时,都哈哈大笑起来。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老夫子还当了回干爸爸呢!”凌舒雅说。
“什么干爸爸?”胡铁柱好奇地问,“雪峰连女朋友都没有,哪儿来的孩子啊?”
凌舒雅有声有色地将我拍照时的难堪事儿说完后,问大家:“你们说,是不是当了回干爸爸呢?”
“嗯,对!自古道有爹必有娘,干妈妈呢?莫非是你?”肖克问凌舒雅。
“那孩子是刘惠英妹子接生的,当时就认了惠英当干妈,惠英才是干妈妈,这叫郎才女貌。”
“难怪老刘这么器重你,原来是送上门的乘龙快婿哦。”李东海拍着我的肩头说。
“无聊!吃你们的馄饨吧!这么大碗汤都堵不住你的嘴?”
我扔下没吃完的馄饨,坐在走廊角落吸着香烟,不一会儿,一股沁人心脾的清香由远至近飘了过来。凌舒雅走到我身边,轻声问:“哎哟!男子汉大丈夫像个女孩子一样,还生气啦?我是闹着玩的。”
我瞪了她一眼:“你就喜欢拿我开涮找乐子?欺负老实人。”
“对不起!”凌舒雅用特有的苏北方言对我说,“我不是故意的,别生气了!”
“是啊,咱有什么本事生气啊,没有情调的土包子,从古墓里挖出的老夫子,肖克有魅力啊!馄饨都要多吃几个。”
凌舒雅笑了笑:“其实你这人还挺有意思的。”
“你挖苦我,还是嘲笑我?”
“真的!不然惠英为什么老是向我打听你的事儿?八成她是喜欢上你了。”
“喜欢我?算了吧,我可没这福分。老刘对我够严厉了,老觉得我是一个不合格的侦查员,让他知道我和他女儿有什么,我不死也得脱层皮。”
“雪峰,说实话,我觉得你很像一个人。”
“谁?”
“呵呵,像我的弟弟!傻弟弟!真是个老夫子!”
说完,凌舒雅一阵风似的溜进了办公室,我握着熄灭的烟头发呆,感觉自己对凌舒雅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就像吹口琴时的感觉。她的背影让我想起了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