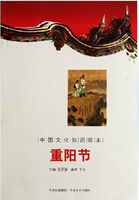在日本,情义和声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个人如果不讲情义,这将是他的污点和罪名,他必须想办法洗刷掉罪名。日本武士尤其视声誉为生命,所以才出现了四十七武士的故事,而且日本人不断地宣扬这个故事包含的复仇与雪耻的意义。在战争中,日本人把失败看做耻辱,所以常以自杀雪耻。
对日本人而言,爱惜自己的名声、使它不受到任何形式的玷污就是在履行自己名声的“情义”。这种“情义”涵盖了许多美德。在西欧人看来可能有些是互相矛盾的,但日本人却认为它们是完全统一的整体。这些美德不是必须要履行的义务,不是对别人施恩的回报,不属于“恩的范畴”。人们在保全自身的名誉时,不需要考虑某个人是否对己有恩。人们要做的只是根据符合身份的礼仪要求办事、在困境中表现出充分的坚毅、在专业技能上维护自己的名声。履行对自己名声的“情义”还意味着消除别人对自己的侮辱和诽谤,诽谤会玷污名誉的清廉,必须洗刷干净,在必要的时候也许还对诽谤者进行报复,或者是自杀,除了这两种极端的方式,还有很多途径可选。但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对诽谤淡然一笑、听之任之。
日本人并没有专门的词语表达我所说的“对名誉的情义”,他们把它描述为报恩范围以外的事情,而这点正是与“报恩”最大的不同:对世界的“情义”是,接受了社会的善意和恩惠有回报的义务;而“对名誉的情义”最显著的一点是它也包括对他人的报复和复仇。西方人一直纳闷为什么这两种“情义”一种表达感激,而另一种表达的却是报复呢?日本人则不以为然,他们说:为什么一种道德观念不能既包括对善意的反应,又包括对他人恶意或污蔑的反应呢?
在日本,人们在做事时也是这样一分为二的。一个正派的人在接受恩惠时,他对恩情是记忆犹新的;而受到侮辱时,那种耻辱也是锥心刺骨的,最后都得有个了结。在对待这两种情义时,日本人不像美国人那样将其区别成“侵犯性”和“非侵犯”两种,在日本人看来,只有“情义范围”外的行为才被称作侵犯,只要在“情义”范围内洗刷掉污名,那就不能说这个人犯了侵犯罪,他不过是清算旧账罢了。只要一天没有对侮辱、诽谤及失败进行报仇雪恨,“世界就一天不会太平”,一个正派的人必须帮助世界恢复到一种平衡的状态。这是人性中善的部分,而不是人性之恶。日本人在理解“情义”时往往掺杂了感激和忠诚。欧洲历史上,这种“对名誉的情义”一直被视为是美德。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情义”曾经盛极一时。在很多方面,它与古典时期西班牙的“西班牙文的勇敢”和德意志的“名誉”有相通之处,某方面甚至像一百多年前欧洲流行的决斗行为。无论在日本,还是在西欧其他国家,主流文化重视雪洗污点,道德价值观的核心就会更注重超越一切物质意义的利益。越是为“名誉”牺牲自己的财产、家庭及个人生活的人,就越会被认为是品德高尚的人。这种做法本身就是和“情义”的定义相符合的,另外它也是这些国家所提倡的“精神价值”的基础。若单从物质角度讲,这种做法会带来巨大损失,可以说“得不偿失”。然而,也正是这一点才使人们“对名誉的情义”与日益充斥着美国人生活的剧烈竞争和公开对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美国某些政治或经济交往中,占有名誉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在物质上谁能获得真正的利益,人们甚至会因此展开一场激烈的战争。至于肯塔基大山中的居民为了名誉习俗而械斗的事件,只不过是一场例外罢了。现在为了“对名誉的情义”而战斗的例子已经越来越少了。
不过,这种文化层面上的“对名分的情义”以及随之产生的敌视心理和伺机报复,绝非亚洲道德观中特有的,不是所谓的东方特质,中国人就没有,暹罗人、印度人也没有。中国人把别人对自己的侮辱和诽谤都看成“小人之举”,认为这些是道德水准低下的人才干的事。而日本人认为,珍视自身的名誉也是高尚品行理想的一部分。在中国的伦理观中,如果一个人因受到侮辱就使用不正当的暴力报复,是大错特错的,这种神经质的行为会让人觉得可笑。同样,也不会用任何善良、伟大的手段来证明这些诽谤是没有根据的,清者自清。在暹罗,人们也不会对此种侮辱如此敏感,他们像中国人一样,受到侮辱时,只是认为诽谤者的行为非常滑稽可笑,而不认为是自己的名誉受到了损害。他们总是自欺欺人地说:“暴露对方卑鄙无耻的最好办法就是容忍和退让。”
只有把“对名分的情义”放到非进攻性的大背景下,人们才可能真正理解这种“情义”的含义。在特定的场合下,复仇只是这种“情义”所要求的手段之一。除此以外人们还需保持冷静和克制。保持忍耐和克制是任何一个自重的日本人对自身“名誉的情义”必须承担的责任。妇女分娩时不能尖声嘶叫,男人面对痛苦和危险不能惊慌失措,洪水来袭时,每个人唯一该做的事情就是赶快收拾几件必需品,然后往高地逃跑,而不能乱了分寸,惊慌失措。秋分前后,狂风暴雨席卷日本本土,他们也是用同样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的。虽然并不是每个日本人最后都能完全做到,但已成为日本人自尊心的一部分。他们认为,美国人的自尊中不太要求自我节制。日本人的自我克制中还具有更深层次的含义,在封建时代,对武士的要求往往比对庶民要求高,虽然这种要求并非强制性的,但却构成了所有阶级的生活准则。在这种要求下,武士必须能忍受非人的肉体折磨,而庶民则在战争中对持刀武士的侵犯表示顺从和容忍。
在日本,有很多著名的讲述武士忍耐力的故事,武士们必须能够战胜饥饿。当然,这事可能太小以至于不值得在这里专门提出来讲了。武士们都饿得快要死了的时候,他们也必须装出刚刚吃饱的样子,并且用牙签剔牙。谚语说:“雏燕长鸣表示它们在寻找食物,武士们口含牙签就表示他们饿了。”在战争中,这句话成了所有士兵的格言,他们不能向痛苦屈服,日本人在这件事上的态度就像那个少年兵回答拿破仑的问题:“受伤了?”“不,报告将军,我被打死了!”即使面临生命危险,武士也不能表现出丝毫痛苦。面对痛苦,他们毫不畏缩。据说,1899年去世的胜伯爵也出身武士家庭,从小家境贫寒,有一次他的****被狗咬伤了,送去医院做手术时,他的父亲用刀戳着他鼻梁警告:“一声都不许哭;哭了就再也不是一名堂堂正正的武士了,将来死了也遭人唾弃。”
“对名誉的情义”还要求人们按与身份相符的方式生活。如果一个人行事不按身份,那他就丧失了自尊的权利。在德川时代,一个自重的人就要按照社会详细的规定来行事,包括穿什么衣服、买什么东西、用什么用品等等。美国人觉得这种按世袭阶级地位而制定的法律特别不可思议。在美国,自尊始终与提高社会地位联系在一起,反对一成不变的法律法规是美国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当得知在日本德川时代某一等级的农民可以给他的孩子买某一种洋娃娃,而另一等级的农民则只能给他的小孩买另一种娃娃时,美国人特别震惊,这几乎无法想象。在美国,虽然办事的规则不一样,但结果往往是一样的。我们理所当然地觉得:工厂主的孩子可以有电动火车,佃农的孩子如果有玉米棒做的娃娃就该心满意足了。我们承认收入的差异,并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美国自尊自重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要不断提高自己的薪金收入。布娃娃的好坏是由薪金的高低决定的,它并不是对我们道德价值观的亵渎。有钱的人理所当然地可以给孩子买高级布娃娃。而在日本,当一个人特有钱时人们就会怀疑他的行为动机,人只有做与自己身份相符的事情才是安全的。即使在今天,不论穷人还是富人,人们只有在遵守等级制规定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建立起自尊,美国人不能理解。早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法国人托克维尔在书中指出了这点。虽然十九世纪的托克维尔对美国的平等制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但他仍对贵族生活情有独钟。他说:“虽然美国有很多特有的美德,但却缺少真正的尊严。所谓真正的尊严就在于搞清自己的身份,不卑不亢。上至王子,下至农夫,皆应如此。”阶级差别本身并非不体面。从这个角度来讲,托克维尔是能够理解日本人的。
今天,人们在对各种文化进行客观研究的时候,发现不同的人对“什么是真正的尊严”有不同的看法,这就像人们定义屈辱一样。有些美国人嚷道:“只有日本也推行美国式的平等观念,日本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尊。”如果真如这些美国人所说,他们确实希望日本是一个自尊的国家,那么首先他们就必须搞清楚什么是日本人自尊的基础。和托克维尔一样,我们也意识到以前那种贵族制度的“真正尊严”正从近代世界中消逝。我相信,另外一种不同的更加优越的尊严正慢慢形成并最终取而代之。今天的日本也将如此,它会依靠自己的力量重建自尊。而且,也只能在自己的基础上,而不是在别人的基础上重建,只有这样,才能获得提升。
“对名分的情义”,除了要求人要搞清楚自己的身份,还要求履行其他的义务。借款人在借钱时可以把自己“对名分的情义”抵押给债主。上辈人在借款时都要向债主表示:“如果还不了债我愿在大庭广众之下受人耻笑”。实际上,即使没还清债务他也不会真的受到公开羞辱,日本人没有当众揭丑的习惯。但是,新年来临之前,借款人必须还清所有债务。否则他只能自杀来“洗刷污名”。至今,仍有一些人会选择在除夕之夜自杀,以此挽回名誉。
所有专业性的工作都涉及“对自身名誉的情义”。特定情况下,当一个人成为众矢之的、备受责难时,日本人的“情义”往往出乎意料之外。如果一个学校失火,学校的主要负责人就会集体引咎自尽,尽管他们对火灾并无直接责任,只是因为火灾使天皇御像受损。还有一些教师为抢救天皇御像,冲入火中被活活烧死。他们的死,证明他们是多么珍视“名誉的情义”、对天皇多么的“忠诚”。还有一些著名的例子,有些人在一些非常庄严的场合,如宣读天皇诏书、或是教育敕语或军人敕谕时,因一时口吃而读错,最后竟要以自杀来洗刷污名。在当今天皇的统治下,也有人曾因一时不慎而误把自己的小孩也起名为“裕仁”,这是当今天皇的御名,必须避讳,最后他只能杀死自己的儿子并自杀,以此谢罪。
在日本,一个专业工作者对其专业名誉的“情义”要求是十分严格的。但这种严格却不一定是美国人所理解的那种要保持技术水平上的先进性。教师会说:“为了保全教师的名誉,我不能对我的学生说不知道。”意思是,即使老师不知道青蛙属于哪类动物,他也必须装作知道。即使一个英语老师他自己本身也只学了几年的基础英语,他也不能容忍别人来订正他的错误。对“教师名誉的情义”指的正是这种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的自我防御性。商人也是这样。对“商人名誉的情义”就是说他不能向任何人透露他公司的资金运转不良,也不能向外界宣布公司的某项计划已经失败。外交家出于“情义”的考虑也不能承认自己某项外交方针的失败。这种在专业工作上对“名誉情义”的尊重实际上是把一个人和他所从事的工作紧紧地联系了起来,任何对某人行为或能力的批评,就自然地变成对他本人的批评。
被人指责专业上失败和无能,日本人的反应在美国也会重复上演。有些人一听到诽谤就气得发狂,但美国人很少会像日本人那样对自己的职业高度防备,一位教师不知道青蛙是属于哪一种属的动物,他会老实承认自己的无知,总比不懂装懂好得多,虽然刚开始他也很想掩饰自己的无知。如果商人们对自己的设计方案不满意,他会考虑采用另一种方案,不会固执地为了保留自尊就坚持自己最初的做法,也不会一旦承认错误,就必须辞职或退休。然而,在日本,这种自我防御却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被普遍接受的礼节,不在太多人面前承认自己的过错是一种智慧。
特别当竞争失败时,他对这件事会特别敏感。比如,面试时录用了其他的应聘者,或者自己在激烈的竞争考试中被淘汰了,这时失败者就会特别在意,觉得自己因此而“蒙受了羞辱”。虽然这种羞耻有时会演变成催人奋进的动力,但更多情况下失败者会非常沮丧。他要么丧失自信、忧郁不振;要么勃然大怒,或者兼而有之。他觉得自己的努力受到了挫败,一切都是没用的。对美国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认识到:竞争在日本并不会发挥像在美国那样的积极作用。在美国,人们都把竞争当成一件好事,对它的作用也深信不疑,心理实验的结果也证明良性竞争可以促使人更出色地完成工作。有压力才有动力,一个人被动地去完成一件工作时,效果当然是没有在竞争的状态下完成得好。然而,在日本,心理测验的结果正好相反。特别是在人们刚告别了少年期,这种结果就更加明显。儿时的日本人大多把竞争看作是一个游戏,并不怎么在意,而对青年和成年人来说,有竞争他们就会有压力,工作效率就会自然地降低。单独工作时,由于很少犯错误,速度也相对较快,工作的进展自然也快。而一旦有了竞争对手,人们就容易分散注意力,也就容易犯错误,工作效率也就下降了。如果对日本人说衡量工作业绩的标准是纵向地与他以前的成绩相比,那么他一定会尽力发挥他的最佳状态;而如果对日本人说衡量的标准是与其他的竞争对手横向对比,他们会慌了阵脚,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几位研究人员对日本人竞争状态下的不良表现的原因作了认真的分析,最后的结论是:如果在做一件事时存在竞争,做事的人就会担心失败,因而精力不能集中,工作业绩自然也受到影响。在竞争状态下,日本人往往对对手异常敏感,认为自己正处于一种被侵犯的状态,所以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如何处理与竞争对手的关系上,不能专心工作。
在接受测验的学生中,大多数人因担心失败可能带来的羞辱而承担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正如教师、商人们重视自己“名分的情义”一样,学生们对他们“名誉的情义”也看得很重。学生组竞赛中输的一队会尽快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来摆脱这种耻辱感。赛艇运动员会扑倒在船上嚎啕大哭;输了的垒球队员也会聚在一起失声痛哭。在美国,我们会说这帮家伙实在太小家子气了,美国人会比较绅士地承认对方更强所以才会取得胜利,然后向胜利者举手致意。虽然谁都不愿意在比赛中输掉,但更看不起因失败而情绪冲动、大哭大闹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