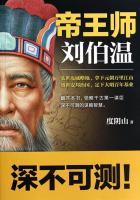一干人离开了“鲨鱼酒吧”,离开了尚东会所。瞿红和丁老板一车,向他们的住所驶去。张朝晖和大猫上了常乐的悍马,尾随着瞿红的法拉利。开过来的时候也是这样,瞿红他们在前面,法拉利尾灯双跳以指示方向。这会儿曲终人散,似乎已经没有那样的必要了。瞿红完全没有等他们的意思,前车的尾灯亮了一会儿就消失在前方的丛林中。黑暗当前,张朝晖的心里犯起了嘀咕:难道说已经就此别过了?就是分手也该打个招呼呀。尤其是经过刚才那不无温柔的一幕,瞿红的体香酒气犹在,一时半会儿他还真的有点接受不了。
好在常乐有GPS定位,加上酒后驾车灵感纷呈,他们并没有走错路,不一会儿就到了城里。
在郊区开车的时候常乐比较沉默,现在他又活跃起来,就像这大城广厦才是他的家一样,或者说常乐是某种趋光动物,一见着满街满市的灯光就不能自已。他看了一眼车上的时间,头也不回地说:“怎么样,咱们再找个地方?”“算了吧,明天我还有事。”这时张朝晖酒已经上头。
“操,谁是闲人啊。”常乐说,“哥们你要学会放松,你来中国不就是放松的吗?否则不就是白来了吗?机不可失。”
“那倒也是。”
“咱们是去洗脚城洗脚,还是去KTV飙歌,要不找个地方让盲人按摩?”
“唱歌,唱歌,我要唱歌!”大猫说。眼瞅着他们就要去唱歌了,就要去卡拉OK,一想到那烟雾弥漫、震耳欲聋的所在,张朝晖就觉得恶心不已。他们好不容易才从那样的地方逃出来,难道又要自投罗网?洗脚、按摩之类的张朝晖就更不敢想象了。你说一个姑娘家的,把你的一双臭脚抱在怀里那是什么滋味?不是你是什么滋味,是她是什么滋味。对方的感觉不好,你又有什么乐趣可言?如果是一个男人那就更不能接受了,不管他是什么滋味,你都会不是滋味。有些东西张朝晖觉得自己是绝对无法消受的。
“我们还是去天安门吧。”他说。那儿天高地阔,正好透气。“天安门?”常乐一愣。
“天安门,现在还开放吗?”“开放开放,二十四小时都开放,就等着你去了。”常乐挖苦道,“张朝晖,你还真把自个儿当成归国华侨了!”“去唱歌嘛,天安门有什么好玩的。”大猫说。常乐不理她。“就天安门。”说着他踩了一下油门,悍马向前直窜出去。在一个十字路口,常乐猛打方向盘,让车掉了一个方向,然后他们就从左边的那条与来路平行的路上直开了下去。车身晃动,继而平稳,这之后常乐再次缄默起来。
他们风驰电掣般地向天安门方向驶去。一上长安街张朝晖这才踏实了,沿途华灯齐放、异常壮观。那路又直又宽又长,就像要通到天上去一样。张朝晖心想:真不愧是世界上最气派的大街呀。上了长安街之后,所有的车辆都像是自动或者是无人驾驶的,一概都在匀速而等距地运动着,悄无声息地向前滑去。路面犹如一条巨大的履带,他甚至怀疑即使自己下去走路也会像坐在车上一样地急速而去,掠过两边的流光溢彩。
其实车速很快,但根本感觉不出来。车厢里嗡嗡地响着低鸣声,并非车况出了问题,而是在报告一切正常。不正常的是张朝晖,这时他感到头晕恶心,肠胃里不禁一阵翻江倒海。
然后,街边很远的地方出现了宫墙,长长的一溜,看上去不高,但显得庄重阴沉。白玉兰般的路灯沿金水河逶迤而去,灯的光亮有限并非用于照明,只是为了指示古老神秘的所在。用于照明的路灯另有一排,靠近车道,灯杆奇高,却白亮犹如太阳。但和玉兰灯比起来是那么轻浮。玉兰灯的白也是胃液的白,是钡餐的那种白——想到这里张朝晖再也忍不住了。
“我,我有点不舒服。”他尽量克制地说。“怎么啦?哪儿不对劲?”常乐看了看后视镜。“肠胃,”张朝晖说,“我好像要,要吐。快找个地方停车。”“你以为这是哪儿,是大王艺术村?想在哪里停就在哪里停?这是长安街,上去就下不来了。”“别开玩笑了,我说的是真话。”“我说的也是真话。”
虽然如此,常乐还是紧张起来。“找找看,车上有没有塑料袋。”张朝晖这时已经不可能去找塑料袋了,他能做的只是拼命地抑制住上涌的呕吐感觉,稍有缓和就向对方告急,“不,不行了,快,快……”好在大猫够机灵,低下头去一阵翻找。她将一只牛皮纸做的购物袋腾了出来,迅速地隔着椅背递过去。张朝晖连忙接过,将袋口张开,然后整个脸都埋了进去。与此同时呕吐物喷涌而出,张朝晖吐了个稀里哗啦。他们的车这时正经过彩灯装饰一新的天安门城楼,广场上的灯光也越发明亮起来,照得车厢里黑白分明,就像打闪一样。窗外壮观的景象张朝晖自然已无法顾及,就是常乐和大猫也无心观赏(他们本来就无此需要)。张朝晖哇哇哇地吐个不停,这边,常乐揿下了所有的车窗,甚至连天顶都全部打开了。大猫小而薄的手掌在鼻子前面扇动着,一面说:“臭死了,臭死了……”
“对不起,I’msorry。”由于脸埋在纸袋里,张朝晖的声音瓮声瓮气的。他总算从纸袋口抬起头来,托着纸袋的手上感觉到一片潮湿。“漏,漏,这袋子是漏的。”张朝晖说:“还有没有袋子?”幸亏大猫此前曾在世贸天阶一通狂购,装衣服的时装袋有六七只之多。此刻她低下头去又是一番倒腾,终于又空出了一只袋子。张朝晖将那只脏手在裤子上擦了擦,不无感激地接过去。他把空袋子套在刚才呕吐过的那只袋子的外面,果然就不漏了。
虽然两只袋子都是纸做的,但后来的那只似乎质量更好,要不就是双层隔离起了作用。当然了,用这样的袋子装水是不行的,好在是呕吐物,足够稠厚。这么一想,那想吐的感觉又涌了上来。但这一次张朝晖不再担心,扒在双层纸袋的口上又是一通狂吐。动作虽然剧烈,张朝晖的心里却异常踏实。最后他已经吐无可吐了。
那只塞满牛肉、羊肉、猪肉、鸡肉、鱼肉、午餐肉、鹌鹑蛋、鸽子蛋、鸡蛋、黄喉、鱼泡、鸡胗、鸭舌、猪血、牛百叶、海参、对虾、凤爪、墨鱼仔、海带、豆腐、冻豆腐、豆芽以及其他各种荤素菜肴和酒精饮料的胃已经转移到了体外,张朝晖托在手上感到沉甸甸的,足有两三公斤重。“今天晚上吃得可真多呀。”他竟然开起玩笑来。
“不是吃多了,是你的美国胃已经不适应中国菜了。”常乐说,“你吐出来的不仅是今天吃的,也包括在美国吃的东西。”
“都有,都有。”张朝晖附和说。“这就叫中西合璧,不堪承受。”“是是是,都搅和到一块儿了。”
在常乐的指示下,大猫递过来一瓶矿泉水。张朝晖拧开盖子喝了一口,他大声地漱着口,然后咕咚一声咽了下去。
“真脏!”大猫说。“我总不能吐到窗外吧?”“你就不能吐在袋子里?”“袋子是纸做的,不够密封。”
一口凉水下肚,张朝晖不由得神清气爽起来。他想起来问:“天安门呢?”
“早过了。”常乐说。“那我们要不要再折回去?”
“罢了,罢了,改天再说。”常乐道,“我还是送你回宾馆睡觉。”张朝晖意犹未尽,“那我们去唱歌吧,去洗脚城洗脚也行,我已经完全没事了。”话一出口连他自己都吓了一跳。“洗什么脚啊,我还要洗车呢。”“你的车没有弄脏。”张朝晖向对方保证,“所有的东西都在这里,都在这只袋子里了。”
常乐的悍马在长城长大酒店门前停住,张朝晖抱着纸袋从车上下来。
常乐向他挥挥手:“哥们,泡个热水澡,好好睡一觉,明天就没事了。”大猫也摆了摆手:“帅哥,拜拜。”
“Bye-bye。”张朝晖说,转身进了酒店的旋转门。那车一声轰鸣,早就窜出去没影子了。
大堂里灯光明亮,由于此刻已是深夜时分客人稀少,就显得更亮了。正对着酒店大门的大堂中央摆放着一只装饰用的巨大的石球,在流水的作用下正旋转不休,水声潺潺,清晰可闻。几名侍者则分别待在若干不同的地点(门边、电梯口、前台一侧),衣冠楚楚,垂手而立。脚下的地毯轻软无声。张朝晖一面走一面四处观望。那几个侍者也只是在他进来的时候看了他一眼,现在已经不看了。而且他们看他的时候并不是他看他们的时候,有一个时间差,张朝晖稍稍放心。他发现,大堂右边的咖啡座那儿灯光已暗,并没有客人,大概营业的时间已经过了。在大堂和咖啡座之间伫立着一只金属垃圾桶,正闪着幽光,张朝晖屏息凝神地向它走了过去。放下纸袋以前张朝晖再次看了看,一切正常,这才提起那只纸袋子往垃圾桶里面塞。然而垃圾桶的口太小了,塞不进饱满的纸袋,但放在上面又过于显眼。张朝晖斟酌了一会儿,最后将纸袋放在了垃圾桶的边上,靠着桶身。之后他便一身轻松地离开了,走向了电梯。
就在他即将跨入电梯的一瞬间,身后响起了一个声音,“先生,请留步。”
音量不大,但清晰分明,而且指向明确(电梯间里此刻只有他一个客人)。张朝晖看见一名侍者提着那只刚刚被自己抛弃的纸袋奔了过来,只得收回了已经迈进电梯里的脚。当然了,他也可以置若罔闻,跨进电梯逃之夭夭,但那样做的确有违他的教养。
于是张朝晖的脸上浮现出一个热情的微笑,故作惊诧地眨巴着眼睛。
侍者及时赶到,“先生,您落东西了。”说着将纸袋递了过来。张朝晖一副如梦初醒的模样,“哦,是是……”他伸手接过袋子,脸上跟着漾起失而复得的欣喜,“是我的,是我的。”自然不可能打开纸袋检查里面的东西。即使不检查张朝晖也知道那袋子里装的是什么,那股子气味已经冒出来了。他将纸袋兜底托起,用双手抱住,以便按紧纸袋的开口。
“谢谢,谢谢。”他说。但侍者并没有马上离开。张朝晖再次醒悟(这回是真的),腾出一只手从衣服里掏出钱包。掏出钱包后又试图从里面取钱。一只手做这一系列的动作毕竟困难了些,侍者再次帮了他,又拿过了纸袋,好让张朝晖两只手动作。
张朝晖终于取出了一张绿色的纸币,十个美元,递给对方。侍者交还纸袋,然后就快步离开了。从背影上看,他似乎是一路掩鼻而行的。也许这只是张朝晖的一个幻觉。
总之张朝晖的感觉十分不好,就像碰见敲诈的了。十美元的小费的确太多了,而且换来的只是一包呕吐物。难道说那股气味对方没有闻见吗?难道,那侍者不是眼瞅着他把纸袋放在垃圾桶旁边的吗?这小子肯定是故意的,利用外国人的教养挣外快,并且干过不止一次两次。
张朝晖一通胡思乱想,气愤不平,身后的电梯门大敞着,都忘记进去了。直到又来了两个住店的客人,走进电梯。电梯门即将关闭的一瞬间张朝晖钻了进去。
他按了所在的楼层。两个客人(似乎是一对)见他进来,唰地就分开了,分别站在电梯的两个角上,意思明显是离张朝晖尽量远一点。张朝晖居中,抱着纸袋,目不斜视一脸正经地看着前面。门缝中光影变化,电梯轻颤着向上升去。
回到房间里,张朝晖终于松弛下来了。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处理纸袋,将里面的呕吐物倒进马桶,冲下去。张朝晖一面倒东西,一面抖着纸袋,同时转过脑袋看卫生间墙上的那面大镜子,看镜子里他的那张脸。经过这一晚上的折腾,这张脸已经难以辨认了,青中带黄,嘴唇犹如一道血线。下午刚刚刮过的面颊上胡楂也冒了出来。张朝晖开始向浴缸里放热水,一来为节约时间(他希望自己马上躺下),二来,弥漫的水蒸气也可以驱散不佳的气味,可以模糊那面镜子,以免张朝晖与自己狼狈相对。
完了是处理倒空的袋子。张朝晖把纸袋撕成碎片,然后装进了酒店提供的垃圾袋。撕纸袋的时候自然沾了一手黏糊糊的东西,张朝晖赶紧洗手。洗完以后又想起需要将垃圾袋的口扎紧,以防气味外逸,于是又弄脏了手,就又去洗。如此折腾了有一刻钟,这才全身脱光了,心满意足地泡进了放满了热水的浴缸里。
洗澡水的上面漂浮着一层云朵似的泡沫,张朝晖不由得深深地呼吸。他什么都不想了,也不想动了。就在这时,房间里的电话响了起来。
张朝晖的第一反应是那个侍者。难道说十美元的小费还嫌不够吗?或者,他又找到了一只纸袋?张朝晖思前想后,自己只有一只纸袋,虽然是两只套在一起的。套在一起的两只纸袋都已经处理掉了,就像毁尸灭迹那样地踪迹全无,无处可觅了。思念至此,他就彻底放下心来,任那电话铃声在房间里响彻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