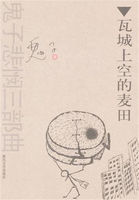故乡月
高桂英
依然是那一方纤尘不染的蓝天,依然是那一轮清辉尽泻的明月,依然是那一片宽阔平坦的土地,此番故地重临,却是别有一般滋味在心头。
二十年了!二十年岁月沧桑,风霜雨雪。人生的舞台上,上演了多少悲欢离合的人间闹剧,导演出多少追逐物欲与虚荣的故事,只有那一轮清如水、明如镜的故乡月心中有知了。
记得二十年前,一只行囊,装进了家乡亲人的殷殷嘱托与牵挂,装进了我格外珍爱和依恋的那轮故乡明月。走上了外出谋生的道路。临行那天,站在坑坑洼洼的小路上,回望养育我十九年的故乡和关心我照料我多年的为我送行的亲友乡邻,一想到父母的遗骨孤寂地静卧在那一扌不黄土之下;一想到吃遍百家饭使我得以成长的那种温情;一想到茅屋陋巷中那关爱我的一张张笑脸,尚未成熟的我,从心底迸发出一种强烈的眷恋,禁不住地潸潸泪下。
以后的日子,不论我走到哪里,不论我遭遇到什么样的坎坷与磨难,有故乡的这一轮明月相依相伴,有故乡人淳朴善良情感的相抚相慰,孤独时不空虚,穷困时不贫乏,痛苦时不沮丧,那样的一份虽苦却甜、虽贫却富的精神的安慰,在我的心头一置就是二十年岁月!
如今,为了孩子的求学,我又重返故乡。岁月流逝,人世纷纭,故乡也沧桑巨变,物是人非。我已寻找不到昔日的朋友,寻找不到低矮的茅檐及那一张张熟悉的笑脸。我的同龄人,有的为名利所惑,迷失了自我,失却了生命的本真;有的苦苦奔波劳碌,换来了超前的衰老;有的似乎“聪明”,想方设法补享着大大小小真真假假的富有,西装化的躯体之中,膨胀着物欲与金钱万能的新价值观念。宽敞明亮的房屋、高墙大院,阻隔了鸡犬的相闻。几家合用一眼水井、两家同享一株枣树、夜不闭户、柴门久开已成为了电影场的道具,成为了人为的景观。鲜活在我记忆之中的那条坑坑洼洼的泥泞的小路,早已成了宽阔平展的柏油大道。
房,宽了。路,阔了。那么,人的心灵呢,也不该日趋地狭窄壅塞了吧?
为了打捞出那已经消逝了的童年的情结,我不止一次地来到田野上。旷野的清风,在我思想的海面上掀起了阵阵的涟漪,扩展、流淌,牵着我纷繁的思绪延伸回童年的疆域,心中生发出一种似曾相识的温暖。方始知,回忆,也是一份难得的享受了!
而今,天,依然蔚蓝,蓝得空洞而深邃;云,依然洁白,白得恬淡而凝重;树,依然翠绿,绿得简明而深奥。而我,经历了几多仕途的跋涉,却亦不复当年那个率真质朴、胸无半点尘迹的少年了!
——惟有永恒不变的,只是故乡这一轮皓净无纤的明月,始终保持着那份清醒、安静、真纯,无瑕、无语、无欲、无求……
母亲的“香椿王”
田樱
春暖花开,推窗可望,自家院子中的那棵“香椿王”,圆滑的、有疤痕的树干,逐渐变绿,然后开始发褐发紫,不久就先拔头筹萌出一爿紫褐色的嫩芽,叶子油亮,脉纹清晰。
母亲喜欢“香椿王”,它留下了岁月痕迹。当年这棵香椿树是母亲的宠物,天旱了,她就浇上几瓢水;天冷了,就用草帘子包上。有一次,父亲说要拔掉这棵香椿树,换上一棵柿子树,母亲说啥也不同意,对父亲说:“香椿树,虽不开花,也不结果;却每年春天都把它那嫩嫩的、香喷喷的嫩芽贡献给大家。”听了母亲的话,父亲只好作罢。岁月如梭,老树旁又发出了小香椿树,过了三五年后,幼树分枝,枝丫上萌出芽儿,母亲还和我一起移走了几棵幼树,围绕老树,形成了一片小香椿林,于是我们把老树称作“香椿王”。
往年,每当春日融融,母亲就领我去掐香椿芽。母亲掐香椿芽,还有一定的门道儿,她说:“掐香椿芽要在初春,香椿芽发紫最嫩,深褐色次之,而且到时候一定要去掐,要不然叶老了,就不好吃了,而且要去掉一些老叶,才能发出新芽。”母亲渍香椿芽,也是很讲究的。她总是按照自己掌握的时间去掐,掐了一小筐之后,便将香椿芽一朵一朵洗净,撒上盐,用手搓到腌浸的水如棕酱色,香味喷鼻时,再用盐压在小缸里;倘水苍绿,芽便老了,因而要择嫩的渍。渍好的香椿芽,或是浇香油拌吃,或炒香椿鸡蛋,做泡饭和面条都用它佐食。
悠悠“香椿王”,好像是母亲生活中的一支歌。母亲当过街道干部,还当过区办工业麻绳厂的车间主任,和邻里、厂里的人都有着密切的来往,而“香椿王”似乎成了交往的媒体。母亲当街道调解委员时,遇到居民家庭不和闹离婚的,或孩子“惹了祸”的,母亲就善解善劝,有时还用塑料袋装了满满的一袋子香椿芽送给他们。哥哥1957年从沈阳一家军工学校毕业后,响应党的号召,到了内蒙古一个偏僻地方的军工厂工作。母亲和父亲都鼓励哥哥到边疆扎根。母亲还专程坐火车,带着自己渍的香椿芽去看哥嫂。哥嫂吃着母亲带去的香椿芽,连声说:“母亲做的香椿芽,真嫩真香真鲜。”唐山大地震时,妹夫在河北清风店部队参加抗震救灾,并荣立了二等功,妹夫探亲回大连时,母亲让妹妹、妹夫来家吃饭,端上了一碟新渍的香椿芽,高兴地说:“俺用香椿芽庆贺你立功。”妹夫吃着香椿芽,连连称赞:“真香,真香!”
母亲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不忘过去苦,她常在“香椿王”下讲传统,讲家史。水仙小学、十二中学的学生都听她讲过。母亲热情健谈,讲起话来有情有感。每当讲到全家人掐香椿芽和榆树叶充饥的苦难日子;我大爷被日本鬼子抓去当劳工“扛豆包”,累病了被活活打死在“红房子”(劳工房);父亲因到金州买米,被当“经济犯”抓去,押进当时“西岗大衙门”灌辣椒水,母亲被抓去陪绑,妹妹无人照顾连饿带吓而死的血泪史,常常催人泪下,激起年轻人对旧社会的深仇大恨。有的中小学生到家里走访时,母亲便一边讲家史,一边做忆苦饭,还拿出自己渍的香椿芽给孩子们吃。母亲晚年患了冠心病,行动不便,且又常住院,可她始终惦记着“香椿王”。后来,母亲住的地方动迁了,要盖新楼了,我按母亲的意愿把“香椿王”移植到我住的小院子里,小院很快也形成了一片小香椿林,这也算了却了母亲的一番心愿。
我拿着自己渍的香椿芽,去探望母亲,母亲吃得也像当年的我那一样有滋有味。母亲以八十二岁的高龄故去了,临终前,她还对我说:“别忘了那棵‘香椿王’。”春天到了,“香椿王”圆滑的、有疤痕的树干,又逐渐变绿,然后开始发褐发紫,不久便拔头筹萌出了一爿紫褐色的嫩芽……
长明灯
辛蓝
每晚临睡前都要去阳台小屋关窗,防止夜里突然降临的风雨淋湿家什,刮碎玻璃。望望外边,宿舍区一片漆黑,都瞌上了沉沉的睡眼,惟见一个阳台的窗口,高高地悬着一盏风雨灯。
那是一盏五六十年代常用的小马灯,黑铁皮镶的护框、提手,椭圆形的玻璃灯罩。灯光如豆,火苗轻闪,在酽酽的夜幕上就像天边的一颗启明星,像夜航船高高的桅杆灯,也像神神秘秘的一团天火。听人说,挂这样的灯常和迷信与宗教有关。于是神神鬼鬼的传说,冥冥上界的缥缈,命运祸福的无常就一齐向眼底袭来,心便有些悚然。从此努力不再看那灯,却又神使鬼差下意识地要瞅上一眼。我看见天黑前那窗前绝没有挂灯,第二天清早刚有曙色那阳台也空空荡荡。那灯是主人临睡前挂上去,
第二天清早即取下来,每日如是。这就很需要一番精力和耐心的。
为这事我特意问过母亲,乡间长大,略知民间习俗和巫术之类。不料母亲却一笑,脸上放着庄严而又圣洁的光。
她说那是一盏长明灯,或许是家人生病,或许是家人远出,家中老人为祈祷平安,悄悄许下心愿而点的。有的点一个月,有的点三个月。
此后便更加注意了那盏灯,却发现它并不止点一个月,也不止点三个月,而是长年亮着。我们虽同住一个地方,但不是一个单位,和那户人家打交道很少。由读灯我还从那阳台读出了四季的变换:时而是一盆米兰,时而是一筛杨梅干,时而又是一筛花生。到冬季了,那东西就多了,挂满了串串熏得焦黄的腊肉、火焰鱼,隔这么远都似乎闻到了那香味。
终于有一天,阳台上出现了一个老太太,她低着头,细心地划拉着筛子里的花生米。她一直低着头,我看不见她的脸,无法揣摸她的形象和神情。我只看见她穿着的半截老式斜襟黑布衫,后脑上绾个巴巴结,她花白的头顶正对着我的目光,使我骤然想起以油画《父亲》轰动全国的川中画家罗立中的另一幅油画《茧》。《茧》中的那位母亲也在低着头剥筛子里的蚕茧,头顶的白发悚然入目,宛如一颗大茧。于是,一切都在了不言中。后来听人说,窗对面那位老太太虽然旧式简朴,却是很有福气的。她的儿女们一个个都在外地谋职,且都是工程师、学者,一个孩子还去了大洋彼岸。那么那些晒着的土特产一定就是为这些走天下的儿女准备的。大概去年,女儿从南方回来了,说是得了一种大医院都诊不好的病,死神几次逼近。这是大悲事,可老太太没有咋咋呼呼,也没有悲悲切切,只是什么时候在阳台默默地挂起了这盏灯,灯光中透出一股不信春风唤不回的执着。
前不久,儿子又来信,说是要去留学,远涉重洋而去了,这是大喜事,却也没见她家有什么动静。儿子走后,阳台上又默默地出现了这盏灯。闪动的火苗就像伫立岸边的老母送帆影远去的幽幽目光。
我终于窥见了这位母亲的心底。这是爱的祈祷,是牵挂的意念,是深深的祝福。在这片爱意中,死神望而却步,游子走到天边,也始终牵着慈母的心之线!我被深深地感动了,拥有这片爱真好!唯愿这片爱跨越时空,无限拓展,之于我,之于世界,能有很多很多。
长明灯,心之灯,那是母亲的眼。
美国印象
王秀杰
美国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葱郁和辽阔。美国的面积与中国相差无几,但人口却只是中国的1/6,所以,一进入美国,你会觉得格外辽阔。从飞机上往下看,只见树林,不见城市。连拥有八百万人口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都看不到与其他国家城市相似的成片的中心市区,原来它所辖的人口分布在七十几个小城市中。美国人的住宅观念和中国有很大的不同,一是他们喜欢独门独院的平房,并视之为上乘;二是喜欢住到幽雅安静的郊区,不愿大家挤在一座高层楼房里,更不愿意所有楼房凑在一起排成一条一条的街。美国最早最大的城市纽约倒有个市中心区叫曼哈顿,但那里的高层住宅里,住的大多是穷人。即使是市中心所谓的高层建筑也都在十层以下,中间也都有很宽的绿化带填充着。美国的城市建筑隐蔽在树林里,消融在草木中。
美国的绿化有统一的法规要求,住宅院落之外的事由国家统一安排,院落之内的绿化有硬性规定,除了甬路硬化之外,其余空地都要绿化,种养草坪和花卉,而且,不能随主人意愿随便改变,并且要安装好自动喷灌系统,及时管理,保证成活。
由此,造就了一个辽阔的绿色美国。
美国给我的第二印象是交通的便利和发达。
美国的汽车真是多极了,的确是一个汽车王国。在美国的城市中穿行,你几乎看不到步行者。
高速公路一般的四条单行车道都挤得满满的。据统计,平均不到两人有一辆车,从十五岁到七十岁,凡得到驾驶资格的人都能有一部车。有着世界影都之称的好莱坞所在地洛杉矶,地理位置优越,开发建设较早,旅游业十分发达,但其市区却很分散,呈不规则形状向外扩展,城市之间有高速公路互相贯通。因而,它在美国拥有的汽车是第一多的,八百万人口一千万辆车,平均每人拥有一辆还多。在洛杉矾你便会看到汽车之奇观。在洛杉矶访问的一个傍晚,我们从宾馆步行了好长一段时间,走到了位于洛市中心点的立交桥上,下面的高速公路两边各有八个单行车道,每边都流淌着宽宽的汽车之河。
天渐渐黑了,车道、车辆模糊起来,眼前的河也变了样。迎面驶来的汽车那白亮的前灯流成了珍珠河,顺向驶去的汽车那红色的尾灯流成了玛瑙河。
那是我所看到的最宽敞最漂亮的高速公路。
洛杉矶还有美国(甚至可以说是世界范围)最大的停车场。那就是位于洛杉矶迪斯尼乐园的停车场。那个停车场一眼望不到边,足有几十个足球场大,能停放近万辆汽车。每个车位都像电影院座席那样编了号,乐园不时地用敞篷车将找车人送到各自的车位上去。
车多,停车场就多,停车场甚至是美国人衡量生活是否方便的一个标志。选择到一处如意的停车场是颇费周折和时间的。在洛杉矶,仅道路和停车场的占地面积就占了市区总面积的1/3。
那么多的汽车行驶起来却很少堵车,是因为有许多能够满足需要的高速公路。美国政府从三四十年代就开始修建高速公路,到六七十年代则开始大规模修建。纵横交错的高速公路构成了美国交通的大动脉,十几条横贯东西、纵穿南北的高速公路,把美国本土上的四十八个州紧紧地连在一起,每个州又连接每个市,每个市又连接每个市区。如今,全封闭全立交的高速公路遍布美国。从任何一个家庭开出的汽车,均可畅通无阻地到达美国的任何一个地方。车子能够畅通,除了公路多,在行驶上还有许多规定。在美国的高速公路上行驶,限制最高时速的同时,也限制最低时速,高者110公里,低者72公里,太快不行,太慢也是要受处罚的。有的路在特定时间内还规定车内所载人数,如小轿车内必须有二人以上,如满载则优先通过。有的按车型优先,如乘坐多人的大巴士可优先通过。
高速公路为汽车拥有者创造了便利的条件,自己开车既经济,又方便。只要时间允许,无论多远的路,美国人都愿意开自己的车去。而铁路就被美国人彻底地冷落了。据说,当年为建高速公路,就已拆除了几万英里的铁路,在其基础上,改建成高速公路。就连货运也是以公路为主,铁路的货运量不及公路货运量的一半。人们出门旅行短途开汽车,长途乘飞机。火车票又比飞机票高出几倍,乘火车就是一种超级享受了。火车的旅行者多为年老退休的富有者。
除了高速公路,美国便利的交通还有一个重要的构成,即中远途所乘用的飞机。美国是第一个发明飞机的国家,也是当今飞机制造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美国拥有的飞机是世界上最多的。美国已注册的飞机总数超过三万架,机场就有一万多个。
从东方飞往美国一般都在地处美国西海岸的洛杉矶降落,偌大个机场上摆满了飞机,廊桥边上各航空公司的飞机正在上下乘客,滑行道上等待起飞的飞机排了长串,起飞线上每隔三分钟就有一架飞机冲向云天。私人小型飞机停放坪如同停车场一样摆放着各式各样数不清的飞机。
在美国乘飞机如同中国乘公共汽车,开机前几分钟到达就可上机,没有繁琐的交费和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