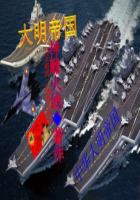《庄子》的字句,非常不好懂;而庄子之意,又公认不可从字句中求之。郭庆藩的《庄子集释》,是传统庄学集大成的着作。但王先谦为之作序,说庄子若见到这本书,只怕倒会说:“此犹吾之糟粕。”
(引子)
有历史责任感的人,往往可以不大计较眼前的得失,而专注于世界本质永恒价值感的人,也容易对繁琐的历史没什么兴趣。
佛教关心成住坏空的轮回,以四十四亿年为一劫,然后动辄千劫亿万劫无量劫。舌头一翻,多少个地球都没了。视野这么大,则释迦牟尼在世的年月误差个几百年,也就是小焉者也,可以忽略不计了。
亚里士多德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开创了诸多学科,但却没给历史学留一席之地。毕竟,人家的第一个身份是哲学家。从哲学的高度往下看,文学挨得比较近,因为“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写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这是在玩演绎法,就有些哲学意味。相反,一板一眼地记录历史事实,像是卖把子笨力气,他老人家不免觉得是通人烦恶,壮夫不为的。
中国也一样,讲究对历史负责的儒家,比较重视记录事实。照一些学者的观点,六部大经典其实全是史书。而据说“哲学上高出诸子”的道家,要么纯说理,要么讲故事,但事实与否,他们是真没上心。
也不妨套孔夫子的名言,仁者乐山而智者乐水。一般印象,当然是儒家重仁,山势地貌比较稳定,难得有个“高岸为谷,深谷为陵”是惊天动地的事,所以忠实记录很有意义;道家人物更聪明,虽然他们经常反智,但水无常形,记不记就无所谓了。
六道之外议庄子
关于春秋战国时期各位大家的生平,是模糊不清的。老子何许人?云山雾罩。庄子的行迹要清楚一些,但也好不到哪里去。
《庄子》书里,以庄子为主角的故事讲了很多,但主要只能作为了解庄子思想和性格的材料看。当事实,则往往假得太明显。
司马迁为庄子写了篇两百多字的传,流沙河先生分析了一下,刨去评论和不可靠的寓言,就剩下来五句话。但就这么几句,分量还是很重的。
庄子者,蒙人也,名周。
蒙是地名,不是说庄子特别会蒙人——虽然《庄子》这书后来确实成了蒙人利器。
蒙在今天的河南商丘附近,当时属宋国。宋国被认为是出蠢人的地方,大家都爱拿宋国人开涮。但守株待兔的故事也好,宋襄之仁的史实也好,这种蠢是透着认死理的固执,耍诈弄奸而老是穿帮的那种蠢,则和宋国人是无缘的。
庄子耍滑头的言论有很多,似乎和宋国的国民性正相反。
周尝为蒙漆园吏。
漆园是地名还是漆树园子,无定论,两种理解都可通。拿官职称呼人,是中国坚定不移的老传统,过去书上经常说“漆园”如何如何,就是在说庄子。
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
庄子和梁惠王、齐宣王同时,自然也就是和孟子同时。奇怪的是,这二位却谁也没提过谁。这引起了很多猜疑。有人说,其实他们彼此眼中还是有对方的。孟子骂杨朱,是指桑骂槐冲着庄周去的;而庄子虚构过一个叫“孟子反”的人物,就是要和孟子反着来。作为考证,这番见解可说证据相当薄弱,但它确实反映了这样一种心理:并世两大高手竟然没过过招,这可实在太遗憾了。
当时宋国的国君是宋康王。这也是个传奇人物,他是宋国第一位称王的国君,也是宋国最后一位国君。在他的指挥下,弱小的宋国嗑了药似的,把身边的魏、楚、齐三雄挨个给揍了,但最终结局是身死国灭。《史记》说,宋康王是个神经病一样的暴君,把自己老祖宗纣王(宋是殷商王室的后裔)的暴行,全套复演了一遍;韩非子则说,宋康王是好人啊,推行仁义啊,但在战国中后期搞仁义不是找死嘛,所以他完了。
这样截然相反的评价,让历史学家感到很困惑。但对庄子来说,这倒完全不成问题,反正不管仁君暴君,他都不喜欢。
其学无所不窥。
庄子学问很大,啥书都看。这句话还反映了一个重要信息,就是庄子并不是很穷,至少在他的青少年时期,生活条件应该还不错。那年头没纸,没印刷术,书之竹帛成本很高,一部书的流传范围也不会很广。能接触到这么多知识,需要钱,更需要一定的身份地位和社会关系。
颜世安先生有一个分析我觉得特别有道理,生在中下层知识分子出头机会大把抓的时代,绝望得那么彻底,从头到尾一点努力的兴致都没有,没落贵族家庭出生的人可能性大一点。换成苏秦、李斯那样的苦孩子,才没工夫这么矫情呢。①
庄子如果想富贵,他的生活条件一定可以大大超过他实际拥有的,这个判断我举双手双脚赞同。但说他有多穷,倒也不至于。忙于操心一日三餐的人,未必有工夫写那么多不解决任何实际问题的文章。庄子打打鸟,钓钓鱼,是生活方式,但不见得是谋生方式。兴致一来就把钓到的鱼都倒掉,真饿着肚子的人,很难做出这个举动。
他有时很缺钱,也许是急不是穷。比如下面这件事——庄子找监河侯(掌管一段黄河水道的官员)借钱。监河侯说,没问题,等我把税收上来,借三百斤金子给你。庄子怒了,就讲了着名的“涸辙之鲋”的段子:小水洼里的鱼,需要一盆水救命,你不能跟它说到吴越去引西江水给它。同理,你跟我扯三百金有意思吗?
历来的分析,都是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来揣测监河侯的心理。但似乎也不能排除下面这个可能:监河侯确实想给庄子一大笔钱,赞助文化人说起来也是很有脸面的事情,太少了也确实拿不出手——对比一下,稷下学士是列大夫的待遇,孟轲老师收黄金,也是整百整百的收——他是真没想到庄子急需用钱到这地步了。
另外,文人喜欢在文章里夸张自己的穷困程度,这个毛病根深蒂固,我们不能断言庄子就一点没沾上。庄子见梁惠王,穿补丁衣服,上台阶时衣带、鞋带挣断。咱们不说他是刻意耍酷,但当相国的老朋友惠施就在身边,如果庄子同意换身好点的衣服,一定也不难置办。
在《列御寇篇》里,还说到过庄子的学生想厚葬庄子,庄子没接受。如果这段不是寓言,那倒也说明厚葬的经济条件是有的。
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
司马迁说,庄子学说是对老子的发挥。司马迁的爹司马谈最推崇黄老道家,认为老子综合了一切学说的长处,理所当然会这么认为。儿子受爹的影响,如此写也很正常。老庄是一家,也符合大多数人的印象。
但庄子自己不承认。《天下篇》里,他把关尹、老子算一派,自己算另一派。章太炎给作了解释:
其术似与老子相同,其心乃于老子绝异。故《天下篇》历叙诸家,己与关尹、老聃裂分为二。其褒之以“至极”,尊之以“博大真人”者,以其自然之说,为己所取法也。其裂分为二者,不欲以老子之权术自污也。(《诸子学略说》)
意思是,庄子的理论似乎和老子相同,但用心则和老子完全不同。庄子对老子赞誉有加,是因为老子“道法自然”之类的观念是自己所取法的;不愿意跟老子待一块儿是因为老子阴谋诡计的东西很多,庄子嫌脏。
其着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
这牵涉到《庄子》这部书的作者和版本问题。
今天的《庄子》,六万五千多字,没有“十余万言”。全书分内篇、外篇、杂篇三个部分,总计三十三篇;《汉书·艺文志》里提到,《庄子》共五十二篇,可见现在是不全了。
司马迁说《庄子》是庄周的个人创作,这个观点今天大多数学者已经不认同。但哪些是门人弟子的作品则不好说。全书观点不一致,文风不统一的地方有很多。①比如说,看《庄子》的大多数篇章,你会认同前面章太炎的观点。但有些地方,因为讲得细,脏得比老子还油腻。如果说,老子的阴谋像冲人脸上泼污水,庄子这些阴谋则像往人眼睛里糊油泥。有些热爱庄子而勇猛精进的学者,碰到这种地方往往会认定这不是庄子的思想而主张直接删去①。
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
得说太史公不愧是太史公,“洸洋自恣以适己”七个字,实在概括得好,创作立场和文风气势,都说在里头了。
庄子这种态度,很难得。咱们的先秦诸子越细看越精彩纷呈。但站在庐山之外打量,则很容易发觉,他们关心的问题其实挺狭隘,就是当前的社会问题尤其是政治问题。庄子对这个问题当然也说了话,但主要是在爽自己的,时代主题面前,他是跑题者。
所谓“王公大人不能器之”,得从两个角度理解。一个是王公大人瞧不上庄子,因为庄子没法当统治工具用。西汉初推崇道家,讲的是黄老之学,没有老庄这一说;一个是庄子也不愿意被王公大人瞧得上,被你当伙计使,有意思吗?
彼此干净利落地无视对方,省了不必要的对话,其实也是良好的状态。这是另一层意义上的相忘于江湖。
世界是用来调戏的(上)
这一节的内容,说得严肃一点,可以叫“游世思想”。
庄子说,“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客观标准是没有的。基本上,普通人推崇的东西,庄子都开过涮。
荣华富贵不重要。
《庄子》书里,讲了不少庄子本人有机会当官的故事。
庄子在濮水边钓鱼,楚王派了两个大夫来请他去做官(《史记》中说是相国)。庄子拿着钓鱼竿头也不回:“我听说楚国有一神龟,死了三千年了,你们大王把乌龟壳当个宝供着。请问从这乌龟的角度说,是喜欢死了享受这种待遇呢,还是宁可活着在烂泥潭里甩尾巴玩?”二位大夫说:“应该还是宁可在烂泥潭里吧,好歹活着。”于是庄子说:
“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
庄子的老乡兼老朋友惠施做了魏国的相国。庄子去找他。惠施误以为庄子是来谋夺自己的相位,在魏国首都大梁城中搜捕庄子三天三夜。结果庄子主动走到惠施面前,说南方有种鸟,名字叫鹓鶵①,从南海飞到北海去,那么远的距离,一路上再累,不是梧桐树绝不停下来;再饿,不是竹米绝对不吃;再渴,不是特甘甜的泉水绝对不喝。这时候,猫头鹰抓到一只死老鼠,看见鹓鶵了,心里很紧张,于是对鹓鶵发出威胁的咆哮声。
这都是有名的段子。故事里称庄子而不是庄周,大概是学生记录老师的轶事。是不是事实不一定,但确实表明了一个态度。
还有一种套路化的情节:一个隐士在家待着,忽然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来的正是当今天子——无非是黄帝、尧之类的人物;这个大人物说:“我挺有自知之明的,我不如您,要不我这活儿,您来干得了。”
隐士们一听,都觉得受到了很大的侮辱,这种东西你也给我。极端点的还要跑到河边洗耳朵。
说实话,个人对这类故事说不上喜欢。需要通过拒绝当官当天子,才能证明自己隐居是清高而不是无能,真是挺可悲的。
但庄子为什么那么讨厌当官?
第一从政有危险。庄子跟惠施说,你们这些当官的就像“狸狌”,也就是狸猫、黄鼠狼之类。
子独不见狸狌乎?卑身而伏,以候敖者,东西跳梁,不避高下,中于机辟,死于罔罟。
不管白猫黑猫,玩到最后都是死猫。
实际上,当官的风险性,庄子肯定是夸大了的。选择夸大,恐怕是他厌恶官场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所以这条理由相对不重要。
第二是官场很肮脏。
把相国的尊位比作死老鼠,听说别人要把天下让给自己就去洗耳朵,这些行为都是在形容政治脏。
庄子眼中政治到底有多脏?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下面这个。一个叫曹商的宋国人,游说秦王很成功,秦王赏赐了他一百辆车。曹商就来跟庄子炫耀:“要说人活着就该困在贫民窟,打草鞋糊口,脖子像枯枝,脸色像病危,那兄弟我的确无能;不过要说一番言辞让大国的国君接受,弄支车队显摆下,兄弟倒还有一技之长。”
庄子说:“听说秦王生病,能给背痈开刀排脓的,赏车一辆;能给肛痔吮脓舔血的,赏车五辆。原则是疗法越下作,赏车就越多。你得在痔疮上反复舔吧,不然车子怎么多到这地步?”
庄子看起来很无所谓,但在对官场的态度上,我觉得庄子有洁癖。很多学者都提过这个问题,学者不愿意当官不难理解;难理解的是,为什么庄子连稷下都不去?待遇好,说话比较自由,也没有丝竹乱耳,案牍劳形。有人说,这就是知识分子的天堂啊。
其实,稷下虽是学术圈,但和政府挨得那么近,事实也是按照行政级别定待遇,衙门化是不可避免的。在这里,你可以从事比较纯粹的研究工作,但官面儿上你至少也得大体敷衍得过去。举个例子,稷下黄老之学最盛,谈老子算是情有可原,怎么把黄帝也扯了进来?因为黄帝据说是田姓齐王的老祖宗,“黄老”这种齐国国家级的科研项目,自然是要往篡位者脸上贴点金的。
如果你的性格只是比较有原则、比较高洁,这种程度的妥协也没啥不可接受的。但事实就是,庄子没接受。
第三是当官不自由,约束非常多。
有个故事说是宋国有个旅馆老板,有两个小老婆。一个漂亮一个丑,但这老板就喜欢那丑的。别人问为什么?他说:
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恶者自恶,吾不知其恶也。
漂亮的自以为漂亮(所以嚣张),我就不觉得漂亮;难看的自知难看(所以谦卑),我就不觉得难看。
这个故事,理解的角度很多。可以认为是在讲男人怎么管媳妇。对漂亮的,就得打压,借助一个丑的来打压漂亮的,更是妙法。甚至于,可以由此引申出帝王术,君主整治臣子的手段也是如此①——要知道,古代文人,自来喜欢拿男女关系比喻君臣关系,屈原作楚辞,一写到楚怀王,自己就发出了女人腔。
从女人(臣子)的角度看,这个故事是教导人要低调,别因为自己漂亮(有本事),就自以为了不起。要记住,讨主子欢心,多磕头少说话,低调是王道。
但我要是就不喜欢低调怎么办?
庄子其实不低调,所以他会写大鹏鸟,写任公子钓鱼,写秋水时至的黄河和万川归之的大海。骨子里,他喜欢的是激越恢弘的意象。惠施骂他,也是说他“大而无用”,跟领导没法处。
再说,何止是被人管很烦,其实管人也很烦。到了魏晋时,庄子有一条大粉丝,叫嵇康,他写《与山巨源绝交书》,其中说到如果当官,自己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甚不可”是说风险性,“必不堪”是说不自由,其中既说了怕见领导,也说了怕带下属,总之,把自己放到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就很烦。
所以在《至乐》篇里面,庄子描述极致的欢乐,不但要“无君于上”,而且要“无臣于下”,然后才能“从然以天地为春秋”。
【段子为证】
自来有很多人愿意相信庄子虽然没当官,但对许多国家的政府有巨大的影响力。《史记·越世家》里,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范蠡离开越国后,做生意发了财。后来他的二儿子在楚国犯了事,要被斩首,范蠡就让小儿子去通关系。这时大儿子挺身而出,说我是家里的顶梁柱,救弟弟这么重要的事情,不让我去,我就自杀。范蠡无奈,就让他去找自己的老熟人“庄生”,说具体该怎么做,你完全听他的。
大儿子找到住在贫民窟的庄生,奉上千金,拜他说项。庄生一口答应,钱收下了,但其实是打算事成之后还的,之所以先收着,是让范蠡的儿子放心,表示自己会尽力。这个行为不算难理解,我们今天有时也会听到外科医生因为不收红包,所以被患者家属认为开刀马虎,然后被劈了的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