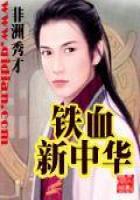战国中期,史料渐多,历史轮廓渐渐清晰。诸子们的活动,虽然不是史书关心的重点,但数得出名号的人物,还是可以排出一大串。这个景象,和之前大不相同。我们知道,孔老师很寂寞,见见官僚,教教学生,但很少有学者出来做他的对手;墨巨侠也只是拍拍儒家的小虾米。高手对决的景象,直到这个年代才多起来。战国中期的思想界,真真是俊采星驰、流光溢彩,是黄金时代中的黄金时代。
(引子)
要让战国时期各位大家一个算一家,也就是所谓“诸子百家”。但要把观点相似的人归置起来算一家,该怎么处理,难度就大了。庄子、荀子、韩非都尝试过分类,但对后世最有影响的分类法,还是汉朝人搞的。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有一篇《论六家要旨》,所谓六家是:
(1)阴阳家;(2)儒家;(3)墨家;(4)名家;(5)法家;(6)道德家。
这篇文章纵论六家的长短,推道德家(也叫道家,但似乎不含庄子)为最高,兼具各家之长而没有各家之短。不过他没说各家都有些什么人物。
《汉书·艺文志》里,推出了一种更着名的分类法:
(1)儒家;(2)道家;(3)阴阳家;(4)法家;(5)名家;(6)墨家;(7)纵横家;(8)杂家;(9)农家;(10)小说家。①
除了司马谈的六家之外,又增添了四家,凑成了整数。这里面,小说家档次最低,不入流,所谓“可观者九家而已”。这入流的九家,也就是后世所谓的“九流”。
《艺文志》相当于是汉朝皇家图书馆的藏书目录,所以在每一家下面都罗列了着作和作者。我们今天说,某某是道家,某某是法家,主要就是依据这篇“志”。
但实际上,这样的分类问题很复杂,因为各位“子”之间互动性很强,思想经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些过渡人物就更难定位。尤其是诸子中的某些大腕儿。原因很简单,越是高手,就越不喜欢被人分类贴标签。比如你如果去跟庄子说,你跟老子,都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庄先生多半会跟你翻白眼。第一,啥叫道家?我没听说过诶!第二,凭啥说我和老子是一派的?区别大了好吧!
但高手们不乐意也没用。因为要便于大众记忆,最好的办法就是分类贴标签。
其实,还有个最大而化之的分类法。孟子谈到当时思想界的状况,说道: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意思当今之世,除了他们儒家之外,就是杨朱和墨翟两大“禽兽派”。
墨家生存之道
和孔门不一样,墨家有个鲜明的特点,就是有严密的组织。这一点,可以从学生的言行中窥见一二。
墨子的顶门大弟子禽滑厘对老师的态度是这样:
禽滑厘子事子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役身给使,不敢问欲。(《备梯》)
这样看来,墨子的学习基本和奴隶没什么区别,连心里想什么,都不敢问老师。想想孔子和学生都是怎么相处的,真是对比鲜明。子路不爽,可以逼得老师赌咒发誓;子贡听到人家说孔子的坏话,则会屁颠屁颠地传话:“老师,人家说你像丧家狗诶!”
和孔子一样,墨子也会帮学生找官做。这样的事例,在墨子书里可以找到很多。有意思的,是学生做官后和师门的关系。
墨子把耕柱子推荐到楚国做官。后来几个墨家弟子去拜访师兄,耕柱子对他们的款待很一般。弟子们不爽,跟墨子说:“耕柱子处楚无益矣!”
墨子说:“未可知也。”意思是等着瞧。
不久,耕柱子送了十斤金子到墨子面前,说:“后生不敢死,有十金于此,愿夫子之用也。”
墨子于是对学生们说:“果未可知也。”意思是,你们看如何?
墨子又有个学生胜绰,墨子把他推荐给齐国将军项子牛。项子牛多次发动侵略战争,胜绰当了帮凶。墨子于是召回了胜绰,因为胜同学这么做,违背了墨家“非攻”的原则。另一个学生高石子就比较自觉,当官而不能实践师门的理想,就自己辞职回家了。
看了这些例子,回头再看那句“耕柱子处楚无益矣”,包含的意思就显得不仅是抱怨:第一,做官的弟子,被认为是有照顾同门的义务的;第二,这些弟子是在请求墨子把耕柱子也从官位上弄下来吧。
总之,墨家的逻辑就是,师门的原则大于官场的规矩。今天要是有个民间组织,可以这样操纵官员的任免,大家觉得会被怎样定性?
孔子若地下有知,发现有人可以当老师而强悍到这个地步,心态大概很难平和。他未必认同这是合理的,但只怕不可避免地也多少会有点羡慕。
学生当了官,然后作风让孔子不爽的事,实在也是有的。冉有就是典型,他帮季氏搜刮钱财,孔子发怒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这家伙不是我的弟子了,同学们敲起鼓来讨伐他去!
处罚是开除学籍,并发动同学去讨伐。讨伐似乎没下文,冉有后来也还是当着自己的官。对比墨巨侠的遥控自如,孔老师的手段显得如此的苍白无力。
墨家的掌门人叫巨子或钜子,有学者认为,墨子当然就是第一任巨子。但另一些学者认为,这个观点“没有文本上的依据”。恰恰是因为墨子去世,伟大导师没了,为了保持组织的凝聚力而塑造新权威,才出现了巨子制度。
即使是采后一说,也还是说明了墨家的组织化程度之高。前面提到过,儒家也曾想立个孔子的继承人,结果就没搞成。
《淮南子》夸墨子,说他门下有追随者一百八十人,皆可为其赴汤蹈火,死不旋踵。这个汉朝人的说法,可能只是推测。但后来有位墨家巨子,确实是做到这一点的。
楚肃王要清洗楚国的贵族,这些贵族不甘心束手待毙又无力抵抗,就纷纷流亡。其中有一位,叫阳城君。
墨子晚年,是阳城君的座上客;墨子去世,墨家巨子孟胜仍然受到阳城君的厚待。所以,当楚军临近之时阳城君便把自己的封地鲁阳托付给了孟胜。
而孟胜决定死守。
有墨家弟子对这个选择表示难以理解,因为实力太过悬殊,与楚军作战无异于以卵击石。何况,阳城君本人也已经逃走,死守毫无意义。
但是孟胜坚持,他认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也绝不退缩的道德勇气,才能真正使“墨者之义”焕发出璀璨的光芒。
最终城破,殉难的墨家弟子一百八十五人。和希腊人“斯巴达三百勇士”的传说一样,其中也有两个人本来有足够正当的理由离开绝地,但他们仍然坚决地选择了死亡。
《吕氏春秋》的作者感叹道,“严罚厚赏,不足以致此”。值得注意的是,当孟胜说明为什么要选择死亡的时候,没有向弟子们提过一句超自然的力量。这大概说明,墨家已经不再需要天志、明鬼之类的教训。对组织的热爱与信仰,本身就足以惊天地、泣鬼神。
《吕氏春秋》还讲过另外一个墨家巨子的故事。
巨子腹,居住在秦国,他的儿子杀了人。秦惠文王怜惜腹年老只有这个独子,因此予以特赦。但腹坚持说:“墨者之法规定‘杀人者死,伤人者刑。’虽然大王为我儿子颁布了特赦,但我还是要依照墨家之法处死他。”
这个故事收在《去私篇》中,强调的是腹道德高尚。这当然没问题。但它也提供了这样一个信息:墨家是一个有自己法律的组织,巨子依照这套法律,对内部成员,有生杀予夺之权。
这样的民间组织,今天又会被怎样定性?
反过来看,领袖太有权威,组织太过严密,也可能成为软肋。
巨子有如此惊人的影响力,从人之常情说,怕是不少墨者都会觊觎这个位置。如果不是刚好有个超逸绝伦大伙都服气的候选人,抢班夺权的事情,就免不了会发生。而一旦发生,这个充满道德激情的组织,大概很难懂得妥协,那时,内耗、分裂就不可避免。
分裂确实发生了。
韩非子提到,墨者分裂成了三派。庄子还说,这些支派都想当巨子的继承人,互相指责别人不是正宗,也就是“别墨”。考虑到《墨子》书里,“别”往往作为兼爱的“兼”的反义词使用,所以这个词的贬损意味,可能相当严厉。
对墨家这样的党团来说,分裂造成的创伤比本来就松散的孔门自然大得多。何况,内患之外还有外忧。
古籍中有很多蛛丝马迹表明,孟胜之后,墨家组织的重心就到了秦国。作为工程技术人才,责任感又如此之强,墨者自然为各国君主所乐于引进甚至礼敬。战国初期,迫切需要改变其边缘化处境的秦国青睐墨家,是毫不奇怪的事情。①
如前文就引了一段墨家巨子腹和秦惠文王的对话。
秦惠文王是什么人?他是秦孝公的儿子,即位后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诛杀变法的商鞅。
其实,他对商鞅制定的法律,不但没什么意见,甚至终身奉行。他所不能容忍的,是“今秦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
君主的权力,是断断不容分享的。绝对君权之外,不可以有任何强大的官场或民间势力存在。
腹不接受秦惠文王的特赦,实际也就是隐然以“墨者之法”与“大王之法”分庭抗礼。这样一位雄猜的君王,嘴上或许会赞誉巨子的大公无私,心里到底会怎么想?
秦惠文王有没有用什么手段对付墨者,不得而知。但秦墨确实飞快地发生了变化。到了这位秦王的晚年,腹想必早已去世,出现在惠文王身边的,是另一个叫唐姑果的墨者。
东方之墨者谢子将西见秦惠王。惠王问秦之墨者唐姑果。唐姑果恐王之亲谢子贤于己也,对曰:“谢子,东方之辩士也,其为人甚险,将奋于说以取少主也。”王因藏怒以待之。(《吕氏春秋·去宥》)
东方的墨者谢子要来见秦惠王,秦惠王向唐姑果咨询。唐姑果害怕谢子威胁到自己的地位,于是说,这个谢子是一个奸诈的辩士,他来,一定会搬出大套说辞,来骗取您儿子的信任。于是,秦惠王见谢子之前,就已经憋着火,当然,谢子的游说也就没成功。
依附权力,然后进谗、邀宠、诬陷……这是自居奴才的人,才会去做的事,唐姑果做起来却是如此地轻车熟路。你再也无法把这个形象,和当年在秦王面前凛然谈论天下之义、墨者之法的巨子联系起来。
墨子、禽滑厘、孟胜、腹的灵魂在云端里看到这一幕,大概也只能一声叹息:“他好像一条狗诶!”
墨家十大主张,谁是头条
如果唐姑果式的人物最终成了秦墨的代表,墨者,大概就只能作为秦军中的一个特种兵团而存在了。
不过,相比墨者集团的命运,墨家思想的影响无疑要重要得多。
而当时人最关注的墨家主张,却和后世不大一样。
十大主张里,尚贤、尚同、明鬼、天志这几条,很少有人提,提了话也不多。
不提尚贤,大概是因为这个主张到了战国中期,就已经近乎普世价值,各派人物都认可,既然是共识,也就没啥可讨论的了。
至于尚同,别派倒是不大会赞成。不过根据尚同原则,主张天子、国君都搞选拔,游说诸侯的时候未必经常当面直说;又主张用严刑峻法收拾老百姓,则发动群众的时候也不大好说。所以,这个最高纲领有可能主要就在墨家内部讲讲,革命成功之前不宜大肆宣传。不传之秘谈不上,却也并不普及,就好像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似的。所以也就不会为它吵架了。
鬼神是真有的,这本来是墨子最注重的观点之一,而别派高手多半不赞同,荀子尤其痛批过。但荀子在大谈“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时候,却并没有点墨家的名。这大概是因为墨家的后学,自己也不信鬼了。前面提到,孟胜决死前的动员演说,就只字未提鬼神;又如《号令》篇里说,要把巫师监控在特定的地方,严禁散布不利言论,只能按照上面的指示跟老百姓说点好听的。这就显然只是利用它们忽悠无知的士兵,并不真信。而神道设教,荀子也以为是好办法。这事没吵起来,应该是墨家发生转变了的缘故。
兼爱、非攻,大家提得确实比较多,但不是最多。所有人必谈的,是墨家的苦行。
这也好理解。节用、节葬这样的主张成为舆论焦点,完全符合传播学规律,什么接近性、反常性、显着性、冲突性和人情味之类的新闻要素,它占齐了。
试想在那个穷奢极欲的时代,有机会升官发财的人却坚决主张过苦日子,实在非常有个性。白白胖胖的王公大人队伍里,出现一个黑黑的乞丐似的人,不想看见也难。而且,这个主张如果得到推广,三公经费省下来大家花,好处来得也很直接。不像兼爱,回报率有多大,回报周期有多长,都是充满悬念的事。
最关键的是,这个话题通俗易懂。儒家和墨家一个主张仁爱,一个主张兼爱,视为原则问题,相互间砸得不亦乐乎,称得上谈玄析理,议论精微,但二者区别到底在哪里,广大人民群众多半听得一头雾水。《吕氏春秋》曾说,墨子提倡的是仁义,《庄子·天道》又云,孔子是主张兼爱的。这算是充分反映了围观群众对这种语词之争不求甚解的欢乐态度。
至于“别墨”们“坚白同异”之类的辩论,更是小众得令人发指。外行看热闹,这是连热闹也不给看。
节用、节葬就不同了。艰苦朴素光荣,铺张浪费可耻,这个道理大家都懂。庄子、荀子们在这个问题上拍墨子的砖,大家当然会觉得其实还是我们劳动人民对此最有发言权嘛。全民大辩论的声势很容易整起来。
当然,辩论太热闹,结果就是立场更加趋于极端,把问题进一步简单化。且看下一个故事。
有个叫许行的楚国人,到一个叫滕国的小国住下,一边干农活,打草鞋,一边鼓吹自己的政治主张。这个许行,据说可能就是墨子的嫡派再传弟子许犯。就算不是,他鼓吹神农之道,属于“九流十家”中的农家,而农家是墨家旁支,这个是学者们大抵公认的。
许行的宣讲效果很不错,有两个儒家弟子,陈相和陈辛兄弟,对许行的理论入了迷,结果就变了节,拜许行为师。众所周知,叛徒反噬本门,出手往往比较狠。所以也许是许行授意,也许是自作主张,陈相去找当时正在滕国的一位儒家前辈踢馆去了。
这位前辈,就是孟轲孟老师。
陈相开门见山,先说对滕国国君滕文公的基本评价:
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仓廪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孟子·滕文公》)
大意是,滕君确实是一位好国君,但治国的大道理,他是没听说过的。贤君要和民众一块儿下地干活,一块儿田埂上吃饭,边做饭边治理国家。可看看现在的滕国,粮仓金库一样不少,这分明就是损害人民的利益来奉养自己,这怎么能叫贤君呢?
要知道,滕文公是孟老师的大粉丝,孟老师的教导,他听了一套又一套,说他“未闻道也”,等于说孟老师的主张都不上台面,这就是大耳刮子呼扇上去了。
为了破这一招,孟老师说了他生平最大的一句反动名言:“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
但要注意,孟老师并不是实在无计可施了,才眼一闭牙一咬心一横,说了句这么自绝于人民的话。实际上,他状态放松得很。本来嘛!他的意思不过是说,社会是要有分工的,用你的管理技能和别人交换粮食吃,和用你生产的手工业产品和别人交换粮食吃,性质上是一样的。所以,有人从事脑力劳动,有人从事体力劳动。从事脑力劳动的进行管理,从事体力劳动的接受安排。这不是最简单、最实在的道理吗?
当时的情况是,陈相同学也觉得孟老师的这番议论无法辩驳,所以他赶紧招数一变,又高调抛出许行的经济主张: